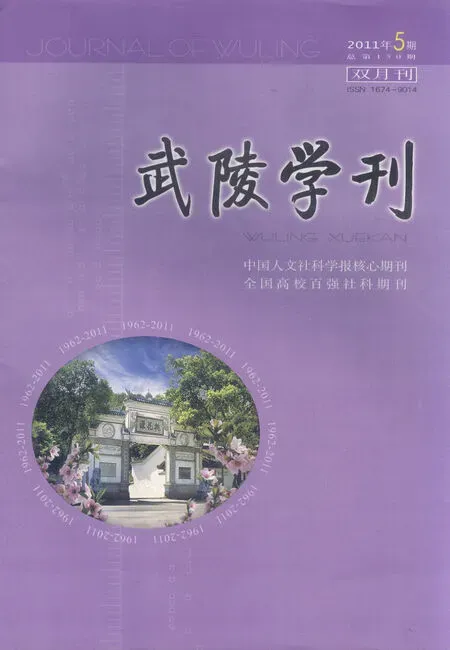论选举权利平等
袁达毅
(北京行政学院 政治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论选举权利平等
袁达毅
(北京行政学院 政治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
选举权利;平等;政治平等;政治文明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它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选举权利平等问题,对于加强我国选举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拟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 选举权利平等及其逻辑和现实起点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常常把选举权利称之为选举权。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很多学者把“选举权利平等”称之为“选举权平等”。对于选举权平等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平等选举权与普选相联系”,“选举权除了合理的积极资格要件(如具有本国国籍、一定年龄及相当的居住时间等)和消极要件外①,不得设定其他不合理的资格限制。这就是‘普遍选举’范畴的平等选举权”[1]。二是认为“选举平等原则是指每个选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不允许任何选民有任何特权,也不允许任何选民受到任何歧视”,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即 “资格平等”和“分量平等”②。三是认为“选举权平等是指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在实现权利的效力方面和当选后的权利受到平等对待”。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选举权平等具体表现在参选权平等、投票权平等、代表名额分配平等、选区划分平等、竞选权平等和当选后的权利义务平等六个方面[2]。四是认为选举平等“是指每个选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在投票上‘一人、一票、一值’,每个选民的投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力完全相同”[3]。这些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上述看法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混淆了“选举权利”和“选举权”这两个概念,把“选举权利”称为“选举权”,这是不科学的;二是仅从直接选举(或者普选)的角度考察选举权利平等问题,其实,间接选举同样存在选举权利平等问题;三是从直接选举考察选举权利平等问题时,以“选民”作为问题的起点,而不是以“公民”作为问题的起点,忽视了“选民”之外的其他公民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四是以“选民”作为讨论选举权利平等问题的起点,实际上是以公民的国籍条件、行为能力条件和政治条件为选举权利平等的逻辑和现实起点,忽视了这些条件之外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因此,上述界定都不能完全反映出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内涵。
那么,什么是选举权利平等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要对选举权利平等这一概念作一界定的话,笔者认为,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选举权利平等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资格平等,即在合理的法律规定(即对资格要件的合理规定)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凡是具有合理资格要件的公民,都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例如,在分配代表名额时,具有相同户籍(或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公民,在计算人口数时具有相同权利。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有相同的选民资格。也就是说,在参加选举活动、被他人选举和当选为人大代表时,享有相同的权利。
二是价值平等,亦称“分量平等”③,是指每位公民或选民在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相同对待。例如,在分配代表名额计算人口数时,所有公民的价值相等,也不得在异地重复计算;在依法确定提名的有效性时,所有选民依法联名的价值相等;在投票选举时,每位选民的投票权相等,即只有一个投票权;在确定选举结果时,每张选票的价值相等,效力相同。概括地说,就是“一地参选,一人一票,一票一值”。
这一界定的最大特点是,将“公民”作为讨论选举权利平等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之所以将“公民”作为讨论选举权利平等问题的逻辑和现实起点,是基于事实经验方面的考虑。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主要依据也是人口。这里所讲的人口,是指具有国籍和地区户籍(或在地区内居住)的自然人,也就是居住在某一地区内的“公民”(或“国民”)。在进行代表名额分配时,除了国籍条件和户籍条件(或居住条件)限制外,没有其他任何条件限制。凡是具有地区户籍(或在地区内居住)的公民,不管其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行为能力如何,也不管其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都是被计算在人口数之内的。也就是说,在进行代表名额分配时,所有公民都享有相同的权利。
从选举权利平等的角度看,就是相同的人口数,应当有相同的选举权利。从代表权的角度看,也就是相同的人口数,应当有相同的代表权。这实质上是从整体情况而不是从个体情况出发,对待公民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是一种整体上的平等。近几年来,我国关于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问题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从整体上讨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2010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构成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从整体上解决城乡人口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选举权利平等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是“公民”而不是“选民”。只有将“公民”作为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才能准确把握“选举权利平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使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较强的解释力。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选举法中关于公民选举权利的规定是不够严密的。一方面规定按人口分配代表名额和划分选区,承认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利;另一方面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标准作了限定。很明显,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严密的规定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参加选举活动和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的选举权利,但只有部分公民才享有全部选举权利。
二 选举权利平等的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总是相对的,绝对的平等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选举权利平等也是一样,是一种相对的平等。选举权利平等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
从选举过程看,选举权利主要由以下五个层次的权利构成。
一是在分配议员或代表名额时所享有的权利。凡是具有本国国籍和选举地户籍(或在选举地居住)的人,都享有的这种权利。凡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都是该国公民,在议员或代表名额分配中,都享有权利。但是,并不是在本国的任何地方都享有这种权利,只能在本国的户籍地或者居住地享有这种权利。也就是说,在进行议员或者代表名额分配时,只能计算在户籍地或者居住地的人口数中,而不能计算在其他地方的人口数之中。
二是公民参加选举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除了要求具备国籍条件和户籍条件外,还需要具备年龄条件、身体条件、政治条件、性别条件、教育条件和财产条件等。只有通过这些条件审查的公民,才能取得选民资格,参加选举活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些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除了年龄条件、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外,没有其它条件限制。具体地说,就是凡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影响参加选举活动的精神病,都可以取得选民资格,都有参加选举活动的权利。
三是被选举的权利。公民参加选举活动的权利和被选举的权利是否一致,因选举目的而定。在一些选举中,两者是一致的,例如,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和居民委员会选举中,这两种权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凡是有权参加选举活动的人,都享有被选举的权利。而在另一些选举中,两者是不一致的。例如,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有年满45周岁的公民才享有被选举的权利。
四是当选的权利。公民拥有被选举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就拥有当选的权利。但实现这种权利,是有条件的。对于当选的条件,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选举,或者同一选举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尽相同。在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当选的要求是:过半数选民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选举结果时,进行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不足应选名额时,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1/3。
五是受救济的权利。当公民的选举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享有受救济的权利。在选举过程中,当公民认为自己的选举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政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选举机构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受理公民投诉和控告的机关经调查核实确认公民选举权利受到侵害的,应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由上可知,随着选举过程的推进,选举权利配置呈“阶梯”状,“阶梯”之间存在一定的“级差”(即“条件”)。这种“级差”是由法律制度规定的,如果“级差”的设置是合理的,法律制度就是合理的(下文还将继续论述这个问题)。根据合理的法律制度配置的选举权利就是合理的,也是平等的。否则,就是不合理和不平等的,例如,把性别、财产、种族和教育程度作为配置选举权利的条件,就是不合理的条件,确认这些不合理条件的法律制度,就是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根据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配置的选举权利,就不是合理和不平等的。
从选举过程看,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平等。条件不同的人,享有的选举权利不同。任何人要享有任何一个层次的选举权利,都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权利“阶梯”的各个层级上,条件相同的人,享有的选举权利也是相同的。
(二)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存在“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
从选举过程看,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平等。那么,从这个“阶梯”中的每一层级的情况看,选举权利是否是绝对平等的呢?回答是否定的。
“平等并非无差别,平等也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追求绝对的结果的平等。……在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平等意味着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应有差别。但在条件不相同或不类似的情况下,区别对待恰恰反映了平等的原则、理念和精神。因此,在平等的原则和理念中,就包含了差别对待的精神。”但是,这种差别是一种合理差别,即“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4]。选举权利平等也是一样。即使是从同一层级的情况看,也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下面,以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为例加以说明。
根据现行选举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数、地区基数和民族情况分配到下一级行政区。
从人口数看,各行政区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不可能完全相等。因为下一级行政区的代表名额,是由下一级行政区的人口数除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平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得出的。被整除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出现余数是正常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根据余数的大小,确定是否再增加一个名额。当余数接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时,一般会增加一个代表名额,当余数少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的人口数的半数时,一般不再增加代表名额。这种由余数造成的差别,就是“合理差别”。
从地区基数来看,所有的下一级行政区的地区基数是相同的。因为各行政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不管其区域大小、人口多少和民族构成情况如何,应当有相同的代表权。这里,区域大小、人口多少和民族构成情况,则是分配地区基数中存在的“合理差别”。
从民族情况来看,对少数民族给予照顾,保证少数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量的代表,是保障民族平等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中,境内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少于总人口数30%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这种因照顾民族平等而存在的差别,也是一种“合理差别”。
根据以上因素确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各地区,再由各地区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各地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会存在不程度的差别。而这种不同程度的差别,就是“合理差别”。从选举权利或代表权看,不是绝对平等的。
选区划分的情况也是一样。从制度规定看,选举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规定大体相等而不是完全相等,就是允许合理差别存在,这是选举权利相对平等的体现,是符合实际的。而按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完全相等划分选区,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选举权利平等的相对性,还取决于认识上的相对性。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对“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的判断,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方面,“依据”即使是客观的,但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即使“依据”是合理的,但根据“合理依据”确定的“差别程度”的合理性,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根据“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 确定的“合理差别”,也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因此,对“合理差别”的认识也不能例外,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下面,以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少数民族人口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依据)。那么,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根据少数民族人口的多少决定是否给予照顾是否合理呢?从价值平等的原则看,是不应当给予照顾的。但是,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给予特殊照顾,是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的要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对少数民族给予特殊照顾,保证少数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以便各少数民族在国家和地方事务决策中充分地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是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证”[5],因此,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根据少数民族人口的多少决定是否给予照顾的规定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是以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认识为基础的。
其次,对少数民族照顾的具体条件,也是根据认识作出的一种判断。根据选举法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6], 30%是一个临界点,不足30%的,给予照顾,达到30%及以上的,则不能给予照顾。30%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程度,这个程度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因为从实际情况看,29.99%与30%的差距已经很小,由于不足30%,从理论上讲,还属于照顾范围,可以得到照顾。30%就是能否给予照顾的具体条件,这个具体条件的确定,是以人们的认识为基础的。
再次,照顾到何种程度,也是基于认识的一种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针对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照顾程度:一是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二是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15%以上、不足30%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30%”;三是“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是在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6]。这四个方面的规定,都是关于照顾程度的规定。这些关于照顾程度的规定,也是根据人们对实际情况的认识作出的。
此外,作为确定差别的某些“依据”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依据”发生变化时,“合理程度”就会发生变化,而由“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决定的“合理差别”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依据”可能会由“合理”变得不那么“合理”或完全“不合理”了,由“依据”决定的差别的“合理程度”也是如此。因而,“合理差别”的平等也会发生变化。
从选举权利平等的制度安排看,根据“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确定的“合理差别”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合理依据”中,其中的某些“依据”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依据”发生变化时,存在“合理差别”的选举权利平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相对平等逐步向不平等的方向发展,当这种不平等比较明显时,就需要对“合理差别”进行调整。因而,选举权利的相对平等是具体的、历史的。也就是说,这种相对平等本身也是相对的。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代表名额分配的城乡人口比例问题,就是如此。
根据1953年制定的第一部选举法和1979年制定的第二部选举法,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农村和城市人口分配比例为8︰1。从我国政权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看,当时确定这样一个分配比例是合理的。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13.26%,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仅占20.60%[7]。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势必造成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过多的情况,这既不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也不利于照顾方方面面,因为城市是各方面代表人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从价值平等的角度看,按8︰1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显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农民一票的价值,只有城市居民的1/8。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乡人口比例不断发生变化。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城镇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6.23%,1995年上升到29%。显然,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过程,就是8︰1的分配比例由合理向不合理变化的过程。因此,1995年对选举法进行第三次修正时,将分配比例由8︰1调整为4︰1。同样,从我国政权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看,这一比例在当时来说也是合理的,从价值平等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
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速度也加快,到2009年底,城镇人口比例由1995年的29.00%增加到46.60%[8], 14年间增加了17.60%。也就是说,随着城镇人口的逐步增加,4︰1的比例逐步由合理变得不合理。因此,2010年对选举法进行第五次修正时,根据我国城乡人口的变化趋势,取消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城乡人口按不同比例分配的规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了城乡人口选举权的平等。
(三)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
选举权利是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在进行选举权利分配时,需要从政治平等的角度出发,把“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结合起来。
“群体平等”,就指不同群体之间的选举权利平等。在选举权利分配时,从整体上考虑不同群体的选举权利平等问题,是政治平等的基本要求。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对一些群体给予照顾,保证其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从表面上看,不符合价值平等的原则,但是,它有利于保障各种群体,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权,符合政治平等的要求。选举法对于“群体(或整体)平等”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总则中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二是在代表名额分配中,对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作了照顾性规定;三是规定代表名额分配“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四是规定“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6]。这些规定所反映出来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平等,而是整体上的平等。
“个体平等”,是指公民之间的选举权利平等。如前所述,在选举的不同阶段上,选举权利配置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从整个选举过程看,选举权利呈现出“阶梯式”的层级特征,在这个阶梯的每一层级上,条件相同的人,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在选举权利分配和行使上的具体体现。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情况看,选举法关于代表名额分配、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出、投票选举等问题的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四)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
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是指在选举过程中,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机会。从选举制度看,就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相同的公民参加选举提供相同的机会。
1.选举机会开放,起点平等。这是机会平等的首要内容。所谓选举机会开放,就是根据合理法律的规定,对条件相同的公民开放相同的选举机会,使公民在获取机会的起点上实现平等。前述选举权利是分层次的,享有各层次选举权利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机会开放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选举机会都对任何人开放,而是根据合理法律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即在选举权利的每一层次上,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机会,站在相同的起点上,而不符合条件的公民,则不能享有相应的选举机会。除了合理法律规定的条件外,不得有其它任何歧视性条件,不得使条件相同的公民在获取机会的起点上出现不平等。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除代表名额分配外,对公民开放其他任何选举机会都是有条件的。例如,参加选举活动和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机会,只对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有影响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疾病的公民开放,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公民,在获取机会的起点上是平等的。
2.选举机会的实现过程平等。选举机会开放,起点平等,为公民利用和实现选举机会提供了可能,但是,仅有起点上的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选举机会的实现过程平等。一是保障公民平等利用选举机会的自由。对于是否利用选举机会,公民有选择自由。但是,不管公民如何选择,只要作出的选择是自愿的,那么,选择行为就是自由的、平等的。如果公民因为某种压力选择利用或放弃利用选举机会,选择就是不自由的,因而也是不平等的。此外,如果在法定条件之外,增加或变相增加公民利用选举机会的条件,进而增加部分公民利用选举机会的难度,迫使部分公民选择放弃利用选举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作出的选择也不是自由、平等的选择。二是保障平等利用法定途径和方式实现选举机会的自由。公民一旦选择利用选举机会,在争取选举机会的实现过程中,公民对于法定途径和方式的利用是平等,也是自由的。公民既可以全部利用,也可以部分利用,不受任何歧视,也不得有任何超越法定途径和方式之外的特权。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看,虽然大家都站在制度规定的同一起跑线上,但是,由于在天然禀赋、职业、家庭条件、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和身体状况等方面,公民个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公民对获取和利用选举机会的态度和行为会有所不同,对选举机会的利用情况和取得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一些人放弃利用,一些人选择利用;一些人全部利用,一些人部分利用;一些人利用起来很熟练,一些人则较为生疏;一些人实现了当选目标,一些人没有实现当选目标。这正如赛跑一样,起点虽然相同,但起跑后的速度、到达终点的时间和取得的名次不同。也就是说,选举机会虽然是平等的,但通过利用选举机会获得的结果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完全平等。
三 选举权利平等的保障
(一)合理的法律制度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平等就是法律的精神与生命。缺乏了对平等的追求与维护,法律则将成为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9]合理的法律制度是指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从选举权利平等的角度看,合理的法律制度,是指采用合理标准分配选举权利,保障选举权利平等,有效促进选举权利行使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一是采用合理的标准分配选举权利。所谓“合理标准”,是指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着合理差别而没有歧视的标准。这只是关于“合理标准”的一般界定。从实际情况看,不同的选举,同一选举的不同历史阶段,同一选举过程的不同阶段,选举权利分配的“合理标准”不尽相同。
首先,在不同的选举中,选举权分配的“合理标准”不尽相同。例如,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一般只有村民享有选举权利,其他人员参加选举,需由村民会议决定;在居民委员会选举中,一般只有居民享有选举权利;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无论是村民还是居民都享有选举权利。这样分配选举权利是合理的。民主的核心是利益问题,村委会选举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与城镇居民的利益无关,而居民委员会选举正好相反④。在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选举的是县乡两级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这与辖区内所有公民都存在利益关系。
其次,在同一选举的不同历史阶段,选举权利分配的“合理标准”不尽相同。在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1953年制定的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是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也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活动,从建国初期的情况看,根据上述标准分配选举权利是合理的,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1979年制定的第二部选举法对于享有选举权利的规定,与第一部选举法相同,对于没有选举权利的规定,有两点变化: 一是规定“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336;二是规定“无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不列入选民名单”[10]340。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选举权利分配标准进行的重大调整。这样调整也是合理的,因为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因其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作为公民,应当享有选举权利;“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均属于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⑤的人,没有选举权利。而对于无法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不列入选民名单的规定更为科学,既把他们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区别开来,又考虑到了某些精神病患者可以行使选举权利的实际状况,例如,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患者,如在选举期间没有发病,是可以行使选举权利的。
再次,同一选举的不同阶段,选举权利分配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在代表名额分配阶段,以国籍和户籍(或居住状况)作为计算人口、分配选举权利的标准,就是“合理标准”。非我国公民,虽然在我国居住,不能计算在我国的总人口数之中,也不能计算在居住地的人口数之中,不能参加选举;而我国公民,没有某地区的户籍(或者在某地区居住),不能参加该地区的选举,不能将其计算在该地区的人口数中,因为他与该地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此外,采用这两个标准,有利于选举的组织管理工作,避免多地参选,这也是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重要措施。在选民登记阶段,根据选举法规定,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力标准)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政治标准)的人不能参加选举活动,也就是不赋予其参加选举活动和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也是合理标准。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不能准确表达或者不能完全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享有选举权利;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虽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政治权利被依法剥夺,不能享有选举权利,因为选举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
此外,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一贯坚持的“一地参选,一人一票,一票一值”原则,以及对于少数民族和人口特少行政区代表名额的照顾,也都是我国选举权利分配中的“合理标准”。
二是采用科学的选举程序保障选举权利的行使。采用“合理标准”分配选举权利,只解决了法律制度中实体部分合理性问题。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仅有实体规定的合理性和平等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选举程序,从程序上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的行使。如果没有科学的选举程序予以保障,选举权利平等就很难实现。科学的选举程序,也是正义的程序,是符合客观实际而又严密的法律程序,它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选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相适应,时间、空间和行为要素设置合理,过程完整而没有漏洞,救济机制完备。关于科学的选举程序及其价值问题, 将另撰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合理的法律制度是选举权利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它为公民平等享有和行使选举权利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果法律制度不合理,选举权利平等就无从谈起。
(二)严格执行法律
任何法律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就很难把制度规定变为现实,实现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合理的法律制度虽然对选举权利平等和实现选举权利平等的程序作了规定,但这只是一种制度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平等。要把这种制度规定上的平等变成现实,就要求选举机构在选举过程中严格执行法律,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如果选举机构不严格执行法律,制度规定再完美,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在选举的实践中,选区划分还存在着极不平等的情况,在很多地方的选区划分中,选区之间的人口悬殊过大是一种常见现象,有的相差几十倍之多⑥。这是由选区划分的制度规定不合理造成的。根据法律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也就是说,选民既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参加选举,也可以在单位参加选举。而在计算人口数时,以户籍为依据,在单位参加选举的选民,其人口数被计算在户籍所在的选区,而不是单位所在地的选区。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居民选区的人口数很多,但选民数很少;一些单位选区的选民数很多,但人口数很少,有的选民数超出人口数,大大超出了合理差别所允许的范围。
(三)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
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对于有效解决选举纠纷,保障选举权利平等,实现选举公平公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多数国家在进行选举制度设计时,非常重视救济和裁判机制在保障选举权利平等中的作用,对选举权利的救济机制和选举纠纷的裁判机制作出明确规定。
选举纠纷主要有三种,即选民资格纠纷、选举效力纠纷和当选纠纷。这三种纠纷引起的选举诉讼分别为选民资格诉讼、选举效力诉讼和当选诉讼。而选举纠纷的裁判机关,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选举,也会有所不同。从历史和现实看,选举纠纷的裁判机关主要有议会、宪法委员会(法国)和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中,又有普通法院、行政法院、选政法院和宪法法院之分[11]236-245。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作为选举纠纷裁判机关,“在政党政治的作用下,议会审议常被多数党用作攻击少数派的武器”[11]240,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纠纷裁判的公平公正,不利于保障选举权利平等。从能够查找到的资料看,宪法委员会是法国采用的一种选举纠纷裁判和监督机制。宪法委员会主要就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全民公决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裁决选举纠纷。而在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中,宪法委员会很难承担起监督和裁判职责,在保障选举权利平等方面很难发挥作用。司法机关作为选举纠纷的裁判机关,由于其地位较为独立,组织体系完备,相对而言,在裁决选举纠纷和实施权利救济中,其公正性更为可靠,也便于及时就地进行选举权利救济,在保障选举公平,实现选举权利平等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也是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公民在选举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对待,选举权利受到侵害时,在通过其它途径不能得到补救的情况下,公民还可以寻求司法救济,通过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在选举权利案件诉讼中,司法机关的判决为最后决定。如果司法不公正,公民通过司法途径不能获得救济,选举权利平等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
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选举权利救济和选举纠纷裁判主要由选举主持机构和司法机关负责。一是在选民资格问题上,公民如果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作出最后决定。二是在选举效力和当选的有效性问题上,选民或者代表如果认为选举中存在违法行为,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提出,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进行调查处理。如果情况属实,依法确定选举或者当选是否有效。对于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选举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危害选举权利平等的行为,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对被侵害的选举权利实施救济,是保障选举自由和选举权利平等的重要措施。
此外,选举领导机构、指导机构、执政党、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其它社会组织,通过对选举工作的领导或者指导和监督,在纠正选举违法行为,解决选举纠纷,进行选举权利救济,保障选举权利平等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所起的作用,最终会通过选举主持机构的决定和司法机关的判决体现出来。
(四)平等的经费保障
选举经费是选举权利平等的物质保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要搞选举,就需要有经费的支持和保障。没有经费的支持和保障,选举就无法进行,选举权利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选举经费对于选举权利平等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保障选举权利平等,也可以产生消极作用,影响选举权利平等。而选举经费的来源和保障机制,是选举经费能否在保障选举权利平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而选举经费的来源和保障机制不同,对选举权利平等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选举经费的来源和保障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选举经费来源的一个主要途径。来自公共财政的选举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支出:一是选举行政经费支出。选举行政经费是选举机构运转和选举活动正常进行的保证,选举过程中的很多公共性支出,如雇佣选举工作人员(选举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印制选举文件、宣传材料和选票,购买办公设备和文具,租赁投票选举场地等,需要由公共财政提供保障,不能由政党或候选人负担,这是保障选举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二是资助政党或候选人的经费。公共财政对候选人的资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和地区,选举任务不同,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当今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如果候选人接受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联邦财政可以对候选人提供资助,但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联邦财政不提供资助;而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中,公共财政对参选的各个政党给予一定的资助,等等。
2.政党经费。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总统或者议会选举中,政党都会拿出一定的经费直接或者间接用于选举。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在总统选举中,政党都会拿出一定经费资助本党的候选人,或者用于选举宣传。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各政党都要拿出大量经费用于议会选举。政党的选举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员缴纳的党费;二是社会捐赠;三是政府的资助或补贴。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拥有经费越多,选举的投入也就越大,胜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3.候选人个人的竞选经费。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候选人用于竞选活动的费用,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候选人的自有资金,即候选人用自己的钱进行竞选。二是候选人向公民、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募集的资金。三是政府对候选人的资助或者补贴。四是政党资助。同政党一样,候选人的竞选经费越多,投入也就越大,胜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公共财政经费看,选举行政经费支出的公共性特征非常突出,是公民行使选举权利的基本保障,因此,在保障选举权利平等中所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任何公民,只要参加选举活动,选举机构必须为其行使选举权利提供相同的保障。例如,选举机构必须为公民提供相同的选举咨询服务和公共信息服务,为选民投票选举提供相同的写票环境和投票场所,为选民投票选举提供相同的选票或者投票设备,等等。这些,都是行使选举权利的基础性保障,也是一种平等的保障。而公共财政对于政党和候选人的资助,也是平等的。因此可以说,公共财政提供的保障,是一种平等的保障。
从政党和候选人筹集选举经费的情况看,法律赋予了所有政党和候选人平等的筹款机会,但由于筹款能力不同,社会对政党和候选人的认同程度不同,政党和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会有很大区别,在资金保障上,政党之间、候选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从政党和候选人自己出资的情况看,财产状况不同,用于选举的经费也不同,财产越多,可用于选举的资金越多,反之亦然,这使得所有政党和候选人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经费保障上出现了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仅此而言,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是金钱政治。
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权机关领导人员选举中,选举经费都由公共财政支出。由于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权机关领导人员选举中,既不存在多党竞选,也不提倡候选人个人竞选,因此,在公共财政支出中,不存在对政党和候选人的经费资助或补贴问题,而介绍和宣传候选人的费用,统一由公共财政支出。由于介绍和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较为简便,用于介绍和宣传候选人的费用不是很多,占选举费用的比例很小。例如,在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介绍和宣传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代表候选人,印发代表候选人的介绍材料,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或者在闭路电视上宣传介绍代表候选人等;在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和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员选举中,主要在代表团会议或者在大会上介绍候选人,印发候选人的介绍材料等。这些都不需要太多的选举经费支出,不需要也不允许候选人个人筹集选举经费。
由公共财政保障所有的选举经费支出,避免了个人财产状况对选举权利的行使造成影响,在经费保障上,使得所有公民和所有候选人都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平等。但是,候选人筹集选举经费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候选人向社会公众宣传介绍和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进行选举动员和选举竞争的过程。不允许候选人筹集选举经费,不利于候选人进行选举动员,充分发挥候选人在选举动员中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选举人充分了解候选人,使得选举人的投票选举行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进而会影响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的公平性,不利于保障选举权利平等。
注释:
①“消极要件是取得选举权不应具备的条件,如被剥夺公权或政治权利,精神健全要件(精神病人不享有选举权)、财产条件、种族资格、受教育程度等。”参见王雅琴著《选举及其相关权利研究——美国选举个案分析》第8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高彩玲《选举制度的平等原则刍议》载《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5期;姜瑞林《选举权的平等保护》载《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14期。
③参见姜瑞林《选举权的平等保护》载《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14期;高彩玲《选举制度的平等原则刍议》载《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5期。
④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和居民杂居,村民和居民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在一些地方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居住在村里的居民享有选举权利;在一些地方的居民委员会选举中,社区居委会辖区内的村民也享有选举权利。
⑤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这种刑罚一般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这些罪行是严重对抗国家制度的罪行,具有敌视或者蔑视国家制度的性质。因此,对于这类犯罪分子,剥夺其政治权利,是为了防止其利用所享有的政治权利继续从事对抗国家制度的活动。
⑥关于选区划分中存在的这种情况,参见袁达毅著《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研究(第2版)》第10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史卫民、雷兢璇著《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第327-3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王雅琴.论平等选举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9):68-70.
[2]蒋明华.也论选举平等[J].理论观察,2006(6):104-105.
[3]梁卡特.选举权生而平等——比较中美城乡选举平等性[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11):134.
[4]吴爽,张宏伟.论平等权与合理差别[J].理论观察,2009(1):54-55.
[5]敖俊德.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选举制度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4(1):7.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N].人民日报,2010-03-15(15).
[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和科技统计司,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6.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0-02-25].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00225_402622945.htm.
[9]胡玉鸿.平等概念的法理思考[J].求是学刊,2008(3):81-88.
[10]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一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1]胡盛仪,陈小京,田穗生.中外选举制度比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OnEqualityofVotingRights
YUANDa-yi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Beijing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
Voting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and are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Equality of voting rights refers to that all legal citizens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in election and includes equality of qualification and equality of value. Equality of voting rights is a kind of “step-type” equality with different levels; it is a relative equality with “rational differences”; it is an equality combining “collective equality” and “individual equality”; it is“opportunism equality”. Equality of voting righ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tical equal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sign of voting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equality of voting rights are: rational legal system, enforcing laws strictly, sound petition and judge systems, and equal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
voting rights; equality; political equalit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D034.4
A
1674-9014(2011)05-0031-10
2011-08-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举制度建设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研究”(04BZZ014)。
袁达毅(1957-),男,湖北通山人,北京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政治制度。
(责任编辑:张群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