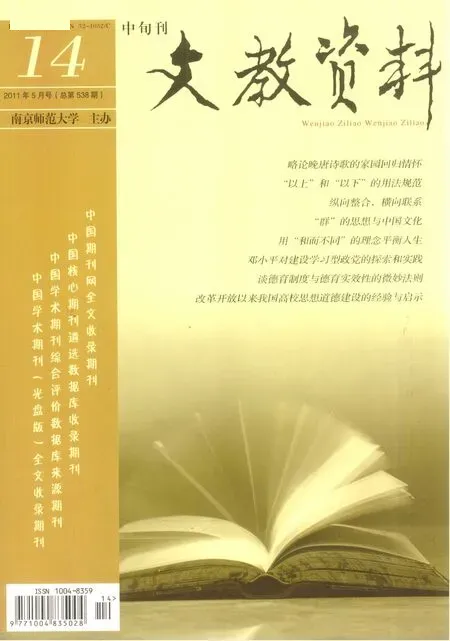略论晚唐诗歌的家园回归情怀
应春波
(湖州师范学院 求真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一
唐代诗歌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显示了其独特的诗歌风貌。相对于前面三个阶段,特别是盛唐的诗歌而言,晚唐诗歌无论在格局、气度,还是在神韵、境界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盛唐诗歌的飞动之势、壮阔之气和酣畅之情,在晚唐诗歌中已经渐渐消隐和撤退了,代之而起的,是晚唐诗歌中太多的消极、无奈和苦楚。如果说盛唐的诗歌犹如一位英勇的侠士纵马奔腾,那么晚唐的诗歌就像一位受伤的征夫,带着流血的伤口,拖着疲惫的身躯,步履蹒跚;如果说盛唐的诗歌更多表现出奔腾的力量,那么晚唐诗歌则更多体现出回归的迷惘。政治的黑暗,战乱的频繁,生命的伤害,心灵的凄寒,让晚唐的诗歌表现出了无尽的伤感和回归的情怀。
且看赵嘏《江上与兄别》一诗:“楚国湘江两渺弥,暖川晴雁背帆飞。人间离别尽堪哭,何况不知何日归。”再看温庭筠《渚宫晚春寄秦地友人》一诗:“风华已眇然,独立思江天。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秦原晓重叠,灞浪夜潺湲。今日思归客,愁容在镜悬。”再看杜荀鹤《湘中秋日呈所知》一诗:“四海无寸土,一生惟苦吟。虚垂异乡泪,不滴别人心。雨色凋湘树,滩声下塞禽。求归归未得,不是掷光阴。”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晚唐诗人们强烈的回归情怀,而这种回归情怀的凸显,是和晚唐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诗人们强烈的家园情怀分不开的。
二
客观而言,晚唐诗人的家园情怀包括两类:儒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和道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所谓儒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更加注重对家园的依恋,对故乡亲人的牵挂,多侧重于对实体家园的向往。所谓道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即更加注重心灵的平静与回归,多侧重于内在心灵的寄托。
相对而言,晚唐诗人在抒发儒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时,多注重身体向实体家园的回归。诗人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所以诗歌显得更加凄凉、悲楚。如杜牧的诗句:“又落他乡泪,风前一满衣。”(《逢故人》)李商隐的诗句:“岂关无景物,自是有乡愁。”(《无题》)等等。而在表达道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时,多注重内心向心灵家园的回归,所以显得更加的自然、平静。如储嗣宗的诗句:“唯有田家事,依依似故乡。”(《南陂远望》)薛逢的诗句:“荣华不肯人间住,须读庄生第一篇。”(《九华观废月池》)等等。无论是儒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还是道家意义上的家园情怀,在表达对“家园”(现实的和理想的)的眷恋和期待“回归”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
那么,晚唐诗人的这种“家园”的眷恋和“回归”的期待是如何通过诗歌表达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直抒胸臆的表达
这种表达方式是诗人情感瞬时爆发的结果,是内心情感强烈涌动的体现。且看杜牧《送友人》一诗:“夜雨滴乡思,秋风从别情。都门五十里,驰马逐鸡声。”诗人将“乡思”这一深切的情感以“滴”这一动作来表现,突出了“乡思”之苦,而这“苦”又在漫漫夜雨中显得悠远而深刻,可见其悲凉与苦楚。
再看贾岛《下第》一诗:“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诗人病中思乡,以直抒胸臆的诗歌表达方式让这种思念具备了更强的打动读者的力量。
(二)托物言志的表达
托物言志是中国古代诗人惯用的情感表达方式,晚唐诗人在表达家园回归情怀时,也常常寄情于物,托物表志。通过对大量晚唐诗歌的披览,我发现晚唐诗人的家园回归情怀常托在两类“物”上。其一是“雁”,且看下面这些诗句:
未到乡关闻早雁,独于客路授寒衣。(杜牧,《中途寄友人》)
故园何处风吹柳,新雁南来雪满衣。(赵嘏,《曲江春望怀江南故人》)
行逢海西雁,零落不成行。(马戴,《早发故园》)
以雁寄思,以雁的来去自由来反衬诗人自身归家的不自由,这是中国诗人的习惯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在晚唐诗歌中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晚唐诗人的家园回归情怀所托的第二类 “物”则是“书(信)”,且看下面这些诗句:
百回信到家,未当身一归。(贾岛,《客喜》)
雁飞关塞霜初落,书寄乡闾人未回。(刘沧,《秋夕山斋即事》)
一夜塞鸿来不住,故乡书信半年无。(杜荀鹤,《湘江秋夕》)
这些诗歌都用了“书(信)”这一实体的“物”来承载诗人无尽的思乡之情,诗人们把思念家乡的情怀附着在一封封书信上,表达了既深且重的家园回归情怀。
三
在简略分析了晚唐诗人家园回归情怀的表现以后,我认为,有必要探讨晚唐诗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浓重的家园回归情怀的原因。具体而言,晚唐诗歌家园回归情怀的出现是和晚唐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晚唐诗人自身的原因分不开的。
(一)晚唐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晚唐是一个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的时代。据《旧唐书·僖宗本纪·干符四年》载:“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踰七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盖以递相观望,虚费糇粮,州县罄于供承,乡村泣于侵暴。”“(中和二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自灞上分门复入,处存之众苍黄溃乱,为贼所败,巢怒百姓欢迎处存,凡丁壮皆杀之,坊市为之流血。”《旧唐书·昭宗本纪·龙纪元年》载:“初,自诸侯收长安,黄巢东出关,与(秦)宗权合。巢贼虽平,而宗权之凶徒大集,西至金、商、陕、虢,南极荆、襄,东过淮甸,北侵徐、兖、汴、郑,幅员数十州。五六年间,民无耕积,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宗权既平,而朱全忠连兵十万,吞噬河南,兖、郓、青、徐之间,血战不解,唐祚以至于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亦载:“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所处这样的时代,晚唐诗人们对自己的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对整个晚唐社会已经彻底绝望,他们在政治上无法找到出路,仕途又坎坷多艰,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深感凄凉的诗人们,回归家园是他们最好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二)就诗人自身而言
晚唐诗人凄寒的生活经历直接催生了他们浓烈的家园回归情怀。晚唐诗人大多饱受战争或漂泊之苦,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在“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潸然是偶然”(郑谷,《江际》)、“战马到秋长泪落, 伤禽无夜不魂飞”(张蠙,《言怀》)、“半夜病吟人寝后,百年闲事酒醒初”(李昌符,《客恨》)的无尽伤感中,回归家园成为了他们必然的选择。正如晚唐诗人刘沧在《秋日旅途即事》一诗中所写的那样:“驱羸多自感,烟草远郊平。乡路几时尽,旅人终日行。”
此外,由于社会黑暗,仕途多舛,晚唐诗人们虽然饱读诗书,却没有用武之地,奔走于仕途,却始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方面,只要读一读晚唐诗人的这些诗歌就会有清楚的认识:“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题崇庆寺壁》)“永巷闲咏一径蒿,轻肥大笑事风骚。烟含紫径花期近,雪满长安酒价高。失路渐惊前计错,逢僧更念此生劳。十年春泪催衰飒,羞向清流照鬓毛。”(郑谷,《辇下冬暮咏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名从近事方知险,诗到穷玄更觉难。世薄不惭云路晚,家贫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为身累,坐月眠霜思枉干。”(张蠙,《下第述怀》)……社会的黑暗,生活的凄寒,旅途的困顿,心灵的创伤,迫使晚唐诗人为了寄放自己的心灵而不得不选择回归田园,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这是晚唐诗歌具备浓烈的家园回归情怀的最直接也是最真切的原因。
晚唐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大量的家园回归的情怀从一个侧面体现和印证了唐代诗歌由外拓向内敛演进的轨迹。诗歌发展到晚唐,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诗人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已经丧失了盛唐诗歌的外拓精神,转而向内敛发展,这体现了唐代诗歌由盛转衰的历程,也宣告了“诗国高潮”的沉重谢幕。
[1]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
[2]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