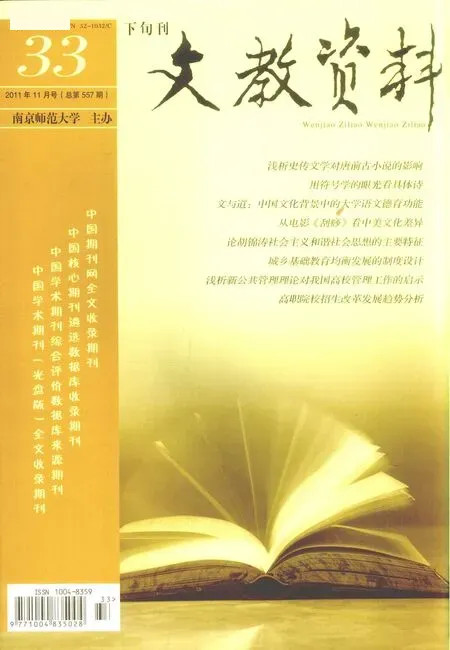论旅游文学作品中的情景相生
刘永生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学历数千年发展,成就斐然。中国古代旅游文学在创作中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旅游文学作品是叙述生活的艺术,是人生哲理的艺术反映,一般在浓郁的感情中有理想信仰、人世经验、社会风云、生活智慧的闪光。作品的情感、脉络,作为作品的内在结构线索潜藏在作品之中,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原本散漫零乱的意象,把它们联结,聚合成和谐的整体,而此时的景往往就是情的载体或标志。“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寄托情感于景物之中,融合景物于情感之里。但情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而是因感触景物而生情寄兴。
一、旅游文学的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
(一)旅游文学的概念
关于旅游文学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意见,但归结起来大体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划分:狭义旅游文学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范围比较狭窄,专指在徜徉自然或市井乡里的旅游过程之中或之后用文字模山范水抒发性灵的文学作品;广义旅游文学是宽泛意义上的旅游文学,范围比较宽,凡记述描写部落迁徙、士卒征戍、游子离家、帝王巡游、贵族狩猎、官宦归隐、士大夫贬谪、士子游学、艺人游艺、学者游历考察、僧侣拜谒传经、商贾异地经商等旅行和旅游过程中所见所闻及抒发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都归于旅游文学。它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体裁既包括传统的游记、散文、诗词曲赋、楹联、题刻、小说、科考纪实、小品等,又包括新技术背景下的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不单指旅游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期间的文学创作,内容涉及对锦绣山水、名胜古迹、田园村居、园林寺院、风物民俗等的描述,还包括特定主体(可以是非旅游者)对旅游活动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感知与评价,或者对他人旅游活动及相关旅游文学的感知分析记录等。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旅游文学概念,原因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是在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最初就产生在广义旅游文学概念所包含的旅行和旅游之中,这和中国古代文学最初就产生于先民的劳作之中同出一理。
(二)旅游文学内容体系
旅游文学从题材分类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诗歌、楹联类。
包括以客观的自然景观中的山水为描写对象的山水田园诗,以室外景物或旅游展览为对象的景物诗,由自然景物、送别旅行等引起的咏怀送别及旅行诗,以及传统形式的诗、词、歌、赋、曲、楹联、韵文,等等[1]。
2.散文类。
包括各类游记、速写、小品、杂文、解说词等随笔、旅游日记,以及基于旅游活动的书信、报告、录音记录、科考报告,等等。
3.题刻类。
包括名人题字(词)及摩崖石刻、碑刻(纪念碑、诗词碑、墓碑、标示碑)等。
4.传说故事类。
包括风物传说、民俗、节庆故事、名胜典故及重大纪念性事件、名人掌故等。
(三)旅游文学特征与功能分析
1.地域性。
首先,山川景物自然风光具有地域性,北国风光不同于南国烟云,如王维在《使至塞上》中所写:“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反映的是诗人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夏出使河西节度府至凉州时的见闻。又如唐诗人岑参写的边塞诗句:“平沙莽莽黄入天”,“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描写了我国西北沙漠飞沙走石的情状。
其次,各地的民俗风情不同。比如川牌。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四川纸牌。在西南地区十分流行,特别在四川境内更是家喻户晓,人人能玩。川牌的历史比扑克久得多。据民间传说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至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
2.时代变迁性。
旅游文学记录某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是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经济变迁、生态资源等综合情况的资料及证据,反映出发展的走向及脉络,具有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价值,随时代变迁形成特定的文化传承影响力,对当前旅游地形象及宣传产生一定影响。如林升的《题临安邸》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3.艺术审美性。
旅游文学不同于单纯的导游材料和旅游手册,许多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语言洗练流畅、生动活泼、富有文采,状物栩栩传神,记事真切感人,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等诗句将动静有度的形象美,对比鲜明的色彩美,以及音律美、嗅觉美、触觉美、人性美等集于一体,做到情景契合或达到景、情、理水乳交融,让人产生余音绕梁之美感,也容易使旅游者产生意欲亲临体会的情绪价值。
4.知识性。
旅游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或很高的科学价值,对地理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民族风俗、博物特产等知识及了解人类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起着传导的作用。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志在考水文、地质、植物及其形成,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清代学者钱谦益赞其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其中关于我国西南石灰岩地区地貌的纪录,更是世界科学史最早出现关于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
二、旅游文学作品的情景相生
古人在描写景物时,都注入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注入了他的思想主张,作品的情感、脉络,都会作为作品的内在结构线索潜藏在作品之中,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原本散漫零乱的意象,把它们联结、聚合成和谐的整体,而此时的景往往就是情的载体或标志。自古至今,文人骚客在舞文弄墨之时,大多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但情景交融,也非融而无法、汇而无度,造成文章思想、内容的乱杂。比较此类作品,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情景的关系——情随景生,情随景迁。
(一)情随景生
作者原本对外界物境并无自觉的情思意念,仅于社会生活活动中随机遭遇某种物境而偶然因境生情,触发所想、所思、所悟,进而升华到情境混融的境界。正如王昌龄的《闺怨》,描绘少妇艳妆登上自家阁楼,原本即无额外的情感思绪,只为闲来随意观赏陌上春色,未料春色无意人生情,远处杨柳的新绿蓦然触动少妇内心深处隐含的情愫,令其不觉因境而联想起和夫婿的长别,辜负了青春,辜负了韶华,悔不当初让夫婿远戍边关觅取功名,从而强烈地抒发了人生患得患失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又如李商隐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诗人心绪不佳,傍晚时分驱车登上古原欲排遣不快。日暮伴随着心境的落寞,特显出诗人当时的情怀是何等的阴晦和无奈。未料登上古原之端,偶遇灿烂夕阳,光辉无限,天地之间蓦然气象万千。尽管时近黄昏,却令诗人不禁心旷神怡,情怀开阔,因而焕然一新,触动感发,赞叹不已。同时联想到光阴难留,不免又为之惋惜和珍惜。诗歌于字面上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境界上确实耐人寻味。
乐游原也称乐游苑,从汉宣帝修建到晚唐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地坪平坦开阔如原,故别称为古原,乃长安东南方的一处高地庙宇,登之可以俯瞰全城景物,是当地望远开怀的好地方。诗人在其他诗歌中有所流露,曾经多次登过古原。本来故地重游,应无特别的悬念,唯独此次于失意而不可适从之际,偶遇美景当空,由景感发,心光闪现,令心境交融而得以高度升华。诗人其时临高怀远,沐浴着光辉夕阳,场景如此壮观而震撼人心,因此而抒情,原本是相当自然的心态。但诗人在此更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转折句,令此壮观的场景不失时机地即兴辉映到情愫之中,而这种情愫适时适地的抒发和浩瀚的光辉夕照共鸣起来更于瞬间迸发出非常强烈的艺术渲染的能量,使诗歌整体的艺术境界因而得到了无限的提高。当然,许多学者认为诗人在诗中的意境是悲观的,甚至有“迟暮之感,沉沦之痛”的评价。此说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肯定作者对“夕阳无限好”是持乐观积极的态度的,与李商隐另一首诗中“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两句的诗意相得益彰,境界上也相类似。即使存在许多的惋惜,但在境界上也不能掩盖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的向往追求,对光阴无比珍惜的真实意念。
我们再看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渡。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正值青年,他怀着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出四川至湖北宜都荆门山时所作。诗人自长江上游乘船远行,出三峡驶向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这时,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行至荆门山,展现在诗人面前的是平原旷野,荆门山已经渐渐退到了身后。波涛汹涌的长江冲下山峦,流入广阔的原野。长江流过荆门山以后,河道弯曲,水面稍稍平静一些。晚上,一轮明月倒映在清澈的水中,月影好像一面从天上飞下来的玉镜;白天,江面上云蒸霞蔚,呈现出海市蜃楼的美景。诗人欣赏到如此的美景,不由得想起离别多日,已在万里之外的故乡。于是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吟出了“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深情诗句。诗的首联叙事,交代出游的目的,颔联和颈联写景,尾联抒情。全诗触景生情,情由景生,写景抒情,水到渠成。诗人在长江上乘船出游,眼前的景离不开水。诗人也一再写水:写长江的水奔腾而去,写明月倒映水中,写江面上的云霞和水汽仿佛海市蜃楼一般美丽。写水已经做足了功夫,最后抒情也是由水而发:我仍然爱着故乡的水,千万里一直伴随着我。说故乡水,实际上是含蓄地表达思乡之情。景和情完全融合在“水”中,浑然天成。
(二)情随景迁
情随景迁简言之是指作者的情感以景物为中心线索,产生变化,不同之景产生不同之情,甚至同一景的不同特点、不同角度也能让人的情感发生变化。《岳阳楼记》中“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中的“异”指的是迁客骚人登楼时因所见洞庭湖景色阴晴变化而产生的悲喜不同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迁客骚人容易从所见景物变化联想到自身境遇的变化。这就是常说的“情随景迁”。如《水经注·江水》一段,先以“自三峡七百里中”点明地点和范围,接用二十六字概写巍峨绵亘、隔江对峙的三峡总貌,重点在山。然后分用三小节描写夏季、冬春和秋季的景色,刻意写水,既能纵览乾坤从大处落墨,又能别具只眼而洞察幽微,缓急相间,动静相生,笔依物转,情随景迁,于寥寥一百五十余字中,历历如绘地再现了三峡(主要是巫峡)的险峻奇秀。文中描写春冬二季的景象,以“素”、“绿”绘色,以“怪”、“悬”、“漱”绘形。 这些皆与“清荣峻茂”相照应。而写秋景,则重在绘声,“长啸”、“凄异”、“哀转”,渲染了肃杀的气氛。其描绘手法因时而变,因景而异,显得变化多端,摇曳生姿。作者的情感则蕴涵其中,一个“趣”字,确切地表达了此时的愉悦之情,而末段的“凄”字,既是对猿声的描述,也是对秋景所触发的感情。
再如《鼎湖山听泉》就是采用移步换景的方式来结构全文的。七星岩之游“走得匆匆,看得蒙蒙”,作者想这次来鼎湖山也未必会有太多的收获,因而表现出来的心态有些怅然、失望;过了寒翠桥,泠泠淙淙的泉水声扑面而来,没见泉水,先闻泉声,作者的心境亦随之改变,“顿生雀跃之心”。转下去,见泉思女。由泉水那半含半露、欲近故远的娇态,想到了常常绕膝下的爱女,表现了作者对泉的爱意萌生。青山幽泉,置身其中,如入清澈之境。此时的作者,个人的情感已抛在一边,整个身心已完全融入景中,有一种了无杂尘、物我两忘的轻快之感;亭前仰观和殿前漫步几段文字,虽直接写泉的地方不多,但绝非闲笔。它一方面是在蓄势,在为感情有升华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给作品赋予时代意义,作者要听得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泉声;作者真正听得山泉声音精妙的是入夜时分的听泉。深夜听泉,别有滋味,作者听得是如痴如醉。听之中,生感,生悟,生愿,听泉的过程无形中也就成了自我心灵的净化过程。
作者在写景之中能注意显示自己感情嬗变的历程,情随景迁,由景生情,由情而悟。
总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人墨客正是在纵情山水之余,将自我融入其中,才能最贴切地感受景物,才能写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情景交融的佳作。
[1]唐诗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