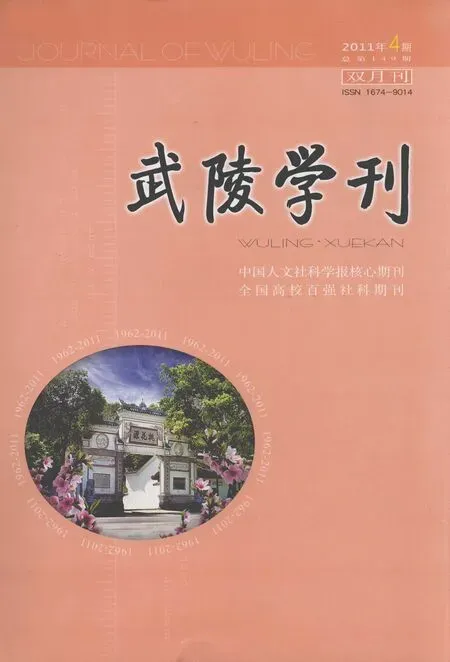池田大作的自然观论析
曾建平
(井冈山大学,江西吉安343009)
池田大作的自然观论析
曾建平
(井冈山大学,江西吉安343009)
自然观是人们看待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性质、地位的观点的总和。池田认为,西方的机械论自然观是导致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与自然被分割开来,最近300年终于确定了“西方支配世界”、“人类支配自然”的格局。当前需要改变这种局面,拯救人类,就要回到东方“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依正不二”的观念中去。“天人合一”论认为,天道与人道在其根本上是一致的,人心或人性中都具备着天性和德性。这一思想构成了中国儒家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根本。而佛教则以“依正不二”和“一念三千”来展示它的大宇宙、大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关系。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内涵相同的哲理,是异曲同工的。
池田大作;自然观;环境思想;西方哲学;东方思想;佛教
一般而言,如何看待自然,看待人,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个基本问题决定着一个人所具有的环境思想。因此,自然观是环境思想的前提。池田先生的丰富的环境思想,是与他的自然观分不开的。本文旨在梳理这些思想以探明池田环境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 池田大作对“自然”内涵的理解
“自然”这个概念,在科学和哲学的历史上经历了曲折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不同的概括,增加和丰富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自然概念的语义学演变不仅表明了它的内涵变化,而且反映了自然观念的嬗动。
在古希腊中,“自然”(φνσιs)一词的始源意义是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总是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柯林伍德评述说:“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唯一含义,并且是作为贯穿希腊文献中的标准含义。”[1]48其后它才有自然事物的总和或聚集之义,这时它开始或多或少地与宇宙或世界(Κóσμο)一词同义。在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文献中,φνσιs只是在事物的本性或本状意义上使用,从来没有指自然界,“‘自然’对于他们从没有意味着世界或者意味着那可以组成世界的诸事物,而总是指本质上属于这些事物的、使得它们像它们的表现的那样行为的某种东西”[1]49。“自然”的其它含义都可以还原或者解释为由自然的本意派生的。
中世纪“自然”一词拉丁文来自希腊文φνσιs,音译为physica,其前缀phyo的本义是产生、成长、本来如此、自身绽出。因而,凡是自身呈现的都是physis,人和社会、生活和习惯、伦理和法律、灵魂和神等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一样均属于physis,这样的physis实际上等同于存在,它已扩展了古希腊语φνσιs的含义,把属人的现象也囊括于其中。
由拉丁语演化而来的英文physics,其构词成份physio具有“自然的”和“物理的”意义,这表明了它与拉丁语physica的渊源关系,而现代英语中的physics虽有“关于物的原理”,与汉语“物理”一词中的一义切合,但主要涵义是指“物理学”或“物理性质、物理过程、物理现象”,缺少与古希腊语φνσιs的旨趣。秉承古希腊“自然”含义的英文是Nature,它的基本含义,一是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聚集,二是指本源(source)或原则(principium)即本性。
20世纪的美国思想史家拉夫乔伊(Arthur0.Lovejoy)详细地例陈了西方思想史中“自然”的66种涵义并指出“自然”一词的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等规范性用法都是由physis和nature在文学和哲学中的用法的涵义演变过来的[2]。
池田也考察过“自然”这个词的含义[3]85。他认为,英语中的nature在日语中译为“自然”。因此,现在我们也使用“自然”这个词。不过,这个词开始作为相当于nature的意思来使用是比较晚的,它原来是另外的意思。与现在的“自然”的意思很近的词,以前是“山川草木”或“花鸟风月”,即以具体存在的事物的名字来指称。日语中没有相当于nature的词,说明日本先民对自然界的把握不是客观的整体地把握。不仅如此,“自然”这个词最初是从中国学来的,它本来的意思是“自然而然”,表示一种遵从根本原理、听其自然的存在状态。排除虚伪做作,听其自然,作为人的应有状态被看作是一种理想。日本的古典诗集《万叶集》中的“自然”也是“自然而然”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观带有浓郁思辨性质,主要有“元气说”;“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形、气、神理论与非生命、生命和人的本质理论。在中国古代,“元气说”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的气组成的,“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各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总之,中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辨解说,它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辩证统一,而且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出统一考虑。
由此可见,与西方自然观不同,东方自然观是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人们怀着与自然的一体观而生活,对动植物有着强烈的亲近感,而且在实践上实现着轮回,甚至认为动物和人都是可以轮回的。在日本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欧洲有位学者到日本来讲授进化论,当这位学者介绍了进化论的观点,怀着不安和好奇的心情,希望了解有什么反应时却大失所望。学生们只是淡淡地听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感到很吃惊[3]85。池田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西方进化论把自然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而感到兴奋和吃惊时,东方人却并不感到兴奋和吃惊。在他们看来,这实在不过是平常的思想而已。因为,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体的东方思想从一开始便认为自然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 池田大作对西方自然观思想的批判
池田先生对西方自然观思想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正是在西方一神教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他说,现代文明之所以走到生态恶化这一步,其根本原因归结起来有两个:一是认为自然界是与人类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们忘记了自然也是遵循一定规律的“生命的存在”。尽管自然界与人类生命的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与人类生命相互关联的。二是犹太一神教认为人类是最接近神的存在,所以理所当然地要征服其他生物和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思想深藏在现代思潮的底部[4]32-33。
那么,西方自然观究竟有着怎样的涵义,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知道,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自然作为一种观念、图像、隐喻、象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然观的转向就是自然图景的转换。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过两次,现在正面临着第三次调整。
在原始社会,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一种尚未分化、没有区别和规定的、混沌的状态中,他们对于人和外物,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还没有意识也不知道区分,一切现象在他们眼中只有一种神秘的“互渗”关系。在社会意义上,人只有俯首于自然才能在自然中生存。从这种人我不分、物我不分的混沌(chaos)自然观到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自然观是西方自然观的初兴。也就是说,在古希腊,人、物相分后,第一次出现了万物有神的有机论自然观。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自然的主要涵义是“生成”、“生长”、“本原”,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原”又变成“本性”、“本源”和“原则”等。这样“自然”开始出现裂痕,“自然物”的出场和“自然”的退隐、遮蔽就不可避免。由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宗教自然观就演变为神学自然观。自然观第一次发生了转向。
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严格说来是古代有机论自然观转变为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然成了上帝的作品,没有自律性,完全是上帝的他在、外在,自然的地位大为降低。自然物作为上帝的作品的位置得以确立,自然的生成即上帝的创造,自然的拯救即趋向终极的上帝。这一点在爱留根纳那里具有伦理色彩,而在托马斯·阿奎拉那里更具有目的论的色彩。池田认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本来就有等级的划分,认为首先存在的是创造主“上帝”,下面是“人”,再下面是上帝赐给人的“自然”[5]279。
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为自然从上帝或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竭尽所能,并从根本上尘封了有机论自然观和泛神论,形成机械论自然观。这是自然观的第二次转向。
近代兴盛的科学使自然归于沉寂。开普勒正式抛弃了泛灵论的自然观,而伽利略则首先给出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基本框架,笛卡尔适时地对此作出了哲学的概括,牛顿等科学家则把这种框架建构成近代科学的庞大体系。这样,自然就完全落入了科学的操纵中,世界图景渐趋机械化,自然观的第二转向全面完成。基督教中世纪的结束虽然使人们摆脱了神的束缚,但人们“仍然拖着圣经的思考的外壳,即认为自然应当和人分开来理解,并为人所利用。应当说正因为抛弃了神这个绊脚石,对自然的篡夺反而更加激烈了”[3]86-87。这种思想是促成这次转向的一个重要基础。池田先生认为,在近代西方,首先提出“征服自然”的是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进一步完善了一神教的自然观,明确地提出要彻底征服自然的“支配自然”的思想。这是一种与“和自然共生”互不相容的自然观。这种思想与笛卡尔的“机械论”、伽利略的“实验科学”结为一体,推进了科学技术革命。而最近300年终于确定了“西方支配世界”、“人类支配自然”,也就好像是直接体现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5]279-280。
正是自然观的第二次转向使得人与自然出现严重的分离,科学向自然进军取得了合法资格。对此,池田先生进行了揭示,他说,在自然科学的进步与技术发达的背景中,有着支撑西方独特的自然观的神的意志这一思想与人类要满足其欲望的冲动的结合。甚至可以认为,为了遵从神的意志而对统治自然所作的努力,在这里是与人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西方可以怀着绝对的自我肯定的信心,把满足其欲望的行为看作是正义的——这恐怕就是近代西方的动力[3]86。
近代西方的自然观沉寂了其早期的有机论,使科学技术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人的欲望被解释为合理的冲动,由此征服自然的进程也开始了空前的扩张。然而,正如池田先生所说,在中国的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纵然精通各种法术,想飞到宇宙的尽头去,这犹如人在掌握科技之后企图为所欲为,但结果却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人类虽然也能利用其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自然界的个别事物,但不可能越出自然宇宙总体运营之外[3]80。在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中,人的主体性得到完全张扬,人的自信心得到空前强化,以致人们无法不相信“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主体性被无限度拔高,科学技术的无限度运用,终究使沉默的自然不再沉默——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其它各种全球问题纷至沓来。
人类历经近代的发展,饱尝了环境危机的痛苦之后也在不断反思: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到底有无限度?人类理性的疯狂增长到底有无限度?自然的给予到底有无限度?池田先生在强烈批判西方自然观的同时也看到,最近西方也正在发生“知”的思考方式的转变。比如说,由“机械的世界观”转向“生命的世界观”,由“元素还原主义”转向“总括对待主义”,由“不连贯自然观”转向“连贯自然观”,等等,其方向都是向东方的整体概念靠近,而且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里,开始使用争取万物“共生”的关键词,如生态学、结构动摇、自我组织化、局部和全部协调、自动平衡、共生感,等等[5]287-288。
从哲学角度看,自然观的这种转变可称之为第三次转向:从机械论自然观到新有机论自然观或生态伦理学意义的自然观。这种转向不是对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简单回归或复兴,而是一种根本的、内在的超越,它的终极目的是要将人类理性的限度与自然给予的限度恰当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像这之前的有机自然观一样抑制人的主体性,无限地赋予自然的有灵性,也不像这之前的机械论自然观一样泯灭自然的灵性无限地扩张人类的理性。
三 池田大作对东方自然观思想的审视
在西方,一神教自然观影响着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把人与自然分离、客观看待自然和企图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思想成为了近代科学文明发展的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印度继承了“自然与人一体性”的感悟,并形成了理论[5]236。
那么,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自然观方面有什么样的生态智慧?池田大作和季羡林一致认为,这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天”既指“广大自然”,也意为“最高主宰”及“最高原理”。“合一”有自然的天与人合一,信仰的天与人合一,德性的天与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等诸种意蕴。而其原初之意是自然的天与人合一,后来才演化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的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源于西周时代。《周易》将其表述为“三才”思想,即天地人“三才之道”。这种思想历时2000多年,为大多数古代哲学家宣扬、阐释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基本格调。
在儒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易传》提出“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中庸》则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相连,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董仲舒说:“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张载接受了通贯性天的观点,第一次将“天人”合题:“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转称》)在这里,天和人是实在的,“天人”之“用”是统一的,但以变易为本性。程朱学派承接此说,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在儒家看来,天、地、人三者是世界上相生、并存的三个要素,它们的统一就是世界的整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传·系辞传下》)从表面上看,天、地、人三者应分施不同的职能,阴阳为天之道,柔刚为地之道,仁义为人之道,但事实上,正是这三种职能的匹配,才构成了宇宙整体的运行,“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三才论”集中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题,表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总之,在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个存在论的命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从价值论视角出发,这一命题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一种至高的目标,实现这种目标是人生的当然使命。
在道家思想中,“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基础,而“德”是具体的“道”,是一事一物之所以为自身的根据。老子把宇宙的法则称之为“道”。依“道”而生成的人是宇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42章)。归根结底,人们应当遵循相当于“道”的自然的规律。现在生态学已经阐明了大自然相互关联的规律。它注意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破坏了大自然的这个规律,人类本身也将会灭亡[5]247-248。《老子》所包含的“天人一体”思想被庄子明确表述为“天与人一也”(《庄子·秋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与人类并生共存,万物与人类合而为一,人既离不开天地,也离不开万物。如果说儒家的“三才论”表达了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那么道家的“四大论”则是“天与人一”的自然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说明宇宙万物由此“四大”构成,而不独唯人为中心,因而人类要以天地万物和谐一致的方式来对待人及人之外的世界,“不自见,故明;不自足,故彰;不自我,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22章)。道家所持的“天与人一”的思想本质上不是一个客观性的事实命题,而是一个价值命题,它有助于矫正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维护人与自然的一体。
池田大作显然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说,在中国思想中,虽然也有像荀子、王充那样否定“天人相关”的例外,但是,“把作为中国思想的两大潮流而又处于两极位置的儒家和道家对比一下,在儒家的最高规范的‘天’与道家的最高规范的‘道’之间,就其自然观来说,我觉得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5]249。
在印度的思想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像中国那样的“天人合一”观念,但也有着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梵我如一”的主张。关于“梵”(brahman)这个词的起源,据著名的东方学者奥尔典贝克解释,是“神圣而充满咒力的‘吠陀’的祈祷词”。这一解释现在基本上被认为是定论[5]251。在吠陀的文献中,尽管不否认有神秘的仪式主义的倾向,但在“梵”这个词中,确实存在着人具有正面对待自然的“力量”这一主体性的一面。也就是说,认为人不是被偶然或神任意拨弄的被动的存在,而是可以与自然、宇宙互相交流的存在。当婆罗门教开始堕落,仪式中心主义带上迷信的色彩,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就大力歌颂作为大宇宙的一员、而且面对宇宙而独立的存在的人的高大、伟大。这就是所谓的“宇宙即我”和“我即宇宙”[5]252。
对于东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不但作为东方宗教家、思想家的池田先生情有独钟,而且许多西方学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科学史家萨顿总结道,在科学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三次东方智慧的大浪潮。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6]140-141他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智慧第四次滚滚而来的时代,其主流就是东方有机论的精神渗透到现代科学之中,形成不同于机械论的新科学传统——现代有机论。我们知道,西方环境哲学思想作为解读自然的一种新范式正是以有机论为基础的。这种早已蕴涵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并被保有数千年的观念,与其他观念一道构成了东方的“历史遗产”。汤因比在与池田先生对话时赞叹地说,东亚的这些历史遗产,诸如“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与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这种“世界精神”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4]277。
一些西方生态伦理学家如施韦泽在构建自己的理论学说时更是自觉地从东方生态思想遗产中汲取智慧。施韦泽认为,“动物保护运动从欧洲哲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但在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中,人对动物的责任具有比在欧洲哲学中大得多的地位”。他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朱,说他们是深刻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告者。早在1934年,他还写过《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神秘主义和伦理》一文,高度评价印度伦理学的普遍性:我们的伦理行为不仅与我们的同类——人相关,而且必然与所有生命相关。他表示,如果在汉学领域能够得到有权威的朋友的帮助,他会立即出版一本关于古代中国思想的著作,因为古代中国思想给予了他最大的鼓舞。他指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与东方传统生态思想的融合其作用是双向的:“我们乐于承认,与我们相比,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们也确信,我们现在在言论和行动中为实行人对动物责任所做的一切,也有其重要性,也能推动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7]12-75。
在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生态危机之时,东方思想中崇尚与自然调和的观念显得极其重要。池田先生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能不能同大自然协调、和平共存,对人类来说,是关系到生存的大问题。为此而必要的‘共生的道德气质’,我认为,就在中国思想的精髓‘天人合一’论中搏动着。”[5]232
四 池田大作对佛教自然观思想的揭示
尽管对东方思想推崇有加,但作为宗教家,池田大作十分钟情的显然还是佛法的自然观。在池田看来,佛法自然观主要体现在“依正不二”和“一念三千”等思想之中。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形成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及“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印度,众生是通过智慧而获得解脱,一向与植物相区别。而中国的佛教认为,草木也和人及其他众生一样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也就是说,主张人与自然环境在都有佛性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即是说,佛教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自然观,不仅对人,而且对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都承认其尊严性。这样就形成了以包括各种生态系统的大自然为“依报”、以人为“正报”的“依正不二”论[5]239-240。
池田认为,佛教是从整体的相关性方面来掌握因果,因果在空间上强调的是一种圆环状的连续,在时间上则是无限延续的循环。前者基本上被称作“缘起”的思想,后者被称作“轮回”的思想。关于前者,佛教初期的经典中简洁地揭示了这一思想:“有此时有彼,生此时生彼;无此时无彼,此灭而彼灭。”后来作为“依正不二论”、“一念三千论”等原理而获得完成。关于后者,后来展开为“生住异灭”四相和“成住坏空”四劫的原理。简单地说,一切事物永远重复着发生、成长、稳定、崩溃和消灭的循环。因此,他痛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迫切要求有整体的、综合的因果的观点[3]84。
池田对佛教的“依正不二”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偏好。他说,“天人合一”论认为,天道与人道在其根本上是一致的,人心或人性中都具备着天性和道德。这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思想中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根本。佛教则是把大宇宙、大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当作“依正不二”论而展开的。……这一表示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哲理,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天人合一”论是异曲同工[5]232-233。所谓“依正不二”,首先是由中国天台宗的妙乐大师湛然在《法华玄义释然》中做出阐释的。这里的“正报”是指生命主体,“依报”是指其生存环境。如果说“正报”是人,那么,“依报”就是指包括生态系统的地球环境。这即是说,人的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性是“而二不二”的关系。人与自然及自然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也可称作“生命网络”,意即任何生命都不是孤立地、只依靠自己的生存,那些乍一看彼此没有联系的生物与自然之间也有着惊人的关联。日莲圣僧在《瑞相御书》则从“正报”的立场出发对“依正不二”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十方乃依报,众生乃正报,譬依报如影,正报如身。无身,则无影,无正报,则无依报,而正报又通过依报而形成。”在这里,“十方”是指整个空间或环境,“依报”就是一切环境;“正报”相对“依报”而言,可以指众生的身心,即“生命的主体”。“依报”和“正报”表面上是各个不相同的物体,实际上两者密切关联;“依报”如同身影,受“正报”这个生命主体的支配,因“正报”而变革;反过来,作为生命主体的“正报”是受其赖以生存的国土、环境等支持才形成[8]。如同“身”和“影”不能分开一样,“正报”和“依报”也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池田依据佛法的“依正不二”原理,认为“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合理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出了“自然与人都是有机关联的‘有生命的存在’”,“人领有自然,自然也领有人”的结论[9]。
而所谓“一念三千”是天台对人与宇宙的思考方式。它把人和自然全部统合起来,认为在人的“一瞬间的心”,即在“一念”的作用下,看到了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天台在“一念三千”论中,把大宇宙的结构称作“三世间”。这里所说的“三世间”,是指“五阴世间”、“众生世间”和“国土世间”。联系“依正不二”论来看,“五阴世间”和“众生世间”则相当于“正报”,“国土世间”则是“依报”。“正报”(五阴世间、众生世间)和“依报”(国土世间)成为“不二”,形成大宇宙、大自然,而且都包含在“一念”之中。这种“一念三千”论与印度哲学的“梵我一如”以及中国思想的“天人合一”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是东方思想的极致[5]259-260。
在这些思想的主导下,佛教提出最基本的恶是“杀生”。人类由于其智慧而制造并使用了可怕的物器。只要有这种力量,杀害任何动物都很容易。正因为如此,如不禁止屠杀,人的罪恶会无限地增长。佛教正是由于这种观念而主张禁止杀生的[3]81。佛教生命观的基本态度是众生平等,生命轮回。所谓“众生”包括人和一切动物,他们在生命意义上有高低序列,但在生命本质上是平等的,并且所有生命都在六种形式中轮回(“六道轮回”),人和畜生互相转化。人若行善止恶,来世是人,甚至脱离苦海,涅槃成佛;人若杀生作恶,来世可能投胎为畜生(“因果报应”)。因而,佛教认为,诸恶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佛教还提出“无情有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等主张,认为生命之外那些无感情无意识的事物如草木瓦石等类,也与有意识的生命一样,都具有佛性。池田先生十分看重生命的这种广义性、至上性。他特别指出,仅仅强调人的生命尊严是狭隘的,“只尊重人的生命,往往会使人类陷入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人,也容易陷入只尊重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信仰者、特定阶级的人们的生命的狭隘圈子中。与此相对照,把尊重生命的精神推广到动物身上,才是最根本的尊重生命的精神”[10]。
池田解释说,之所以在东方会出现佛法的所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应当互相协助”的主张,“看起来这是气候优良的亚洲的生活环境有利于这种思想的形成。在经过严酷的环境中,人要与自然作斗争,于是产生畏惧自然之心。而在肥沃的土壤、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量的条件下,农作物在自然中丰收,滋润了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风土中,大概易于形成自然是保护我们人类的思想。人们争取与自然融合,变为一体,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3]85。这是一种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万象的敏锐观照而产生的思想,对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启示——要清除公害,除了依靠“依正不二”的理念之外,别无他途[4]30-31。
[1][英]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2]Lovejoy,A.O..Some Meanings of“Nature”[M]//Lovejoy,A.O.&Boas,G.eds.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in Antiquity.NewYork:Octagon Books,1973:447-456.
[3][日]池田大作,[法]路奈·尤伊古.黑夜寻求黎明[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5][日]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M].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6][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40-141.
[7][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8][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M].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00-601.
[9][日]池田大作.人生箴言[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197.
[10][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梁鸿飞,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06.
B313.5;B82-058
A
1674-9014(2011)04-0033-06
2011-05-06
创价大学日中友好学术资助项目“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池田大作环境思想研究”。
曾建平(1967-),男,江西新干人,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伦理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伦理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张群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