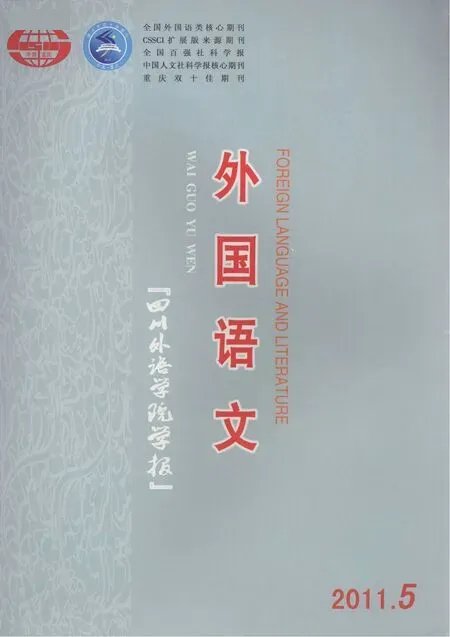解构主义语境下文学翻译的美学价值取向
王大来
(温州大学 城市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1.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与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文本意义只是涉及到读者对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意图等因素获得准确而完美的答案,如果阅读活动所涉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只是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那么文本作者就成了文本理解和阐释的绝对权威,译者的任务只是获得文本预先设定的“完美”答案,从而用目标语言实现原文的意义。解构主义对文本确定意义的解构,打破了作者主宰文本意义的权威。在解构主义看来,文本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神威要意”,作品的意义是游移变动的,不为文本所凝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复制原文本,而是在文本提供的多重意义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既然翻译和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密不可分,译者又有可能对文本意义获得多种理解和阐释,那么是否在文学翻译中存在任何指导性原则用以规约译者的理解?译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有多少可看成是真实可靠的而必须融入到译文之中,又有多少应该留给译文读者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本文旨在运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下进行理论探索,从而揭示文学翻译的一个原则: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应尽力使译文读者获得原文美学价值的享受,不能因填满原文的空白而剥夺译文读者的想像力,从而损害原作含蓄的美学效果。
2.源语中心论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开始都非常直观,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翻译直接呈现的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译者是原意的传达者,译文要“忠实”原文的意义,这就是源语中心论。源语中心论认为,源语文本是翻译的出发点,是翻译展开的依据,译者必须通晓原文,掌握原文的意义和内涵,忠实地再现原文中的意义和神韵。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译者必须了解作者,研究作者,明确作者的写作动机、写作风格和写作特点等。文学研究的传统作者论认为,书写是作者的一项工作,作者对于自己将要书写的对象、形式和内容往往先有腹稿,并知道他的书写活动怎样引导自己铺排陈设文本的情节结构和事态发展的前因后果,作者控制着整个书写活动,成为自己文本的创造者和主宰。作者被认为具有对自己的文本拥有最初的解释权和最终的处置权。此外,传统文本意义论认为,每一个作者的创作都包含有一定的创作意图,即作者创作的艺术动机,因此作者生产出的文本都包含有确定的意义。意义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隐匿在作者精心编排的情景布局上。意义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通过细读、分析和探索去理解和把握。
翻译研究的源语中心论遵循的就是文学研究的传统作者论和文本意义论,它视原文和原作者为原文意义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把忠实于原文和作者的意义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在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规定性传统译论的影响下而不受重视。传统译论视翻译为艺术创作,译者是翻译文学的创造者,但译者的创造被视为二度创造,即是说,译者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天赋和能力,而这种天赋和能力只允许他更好地去理解原作者和原作,而不是作为一个个体的创造力去进行富有个性的创造,译者的表达就是亦步亦趋地把原作的精神或神韵表现出来。译者必须克制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或把自己的这种创造力转化为复写原作艺术精神的能力,译者要求隐身,译文要让读者感到如同作者的原创。
源语中心论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文学翻译并带来了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文本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那么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文再现的客观现实作出反映,是客观现实反映的反映。作家的创作是对真实的再现,译者则是对“真实”再现的再现。作家是原创,译者是二度创作。因此,长久以来,翻译就是“模仿”、“复制”、“再现”等,译者就是所谓的“画家”、“模仿者”、“翻译机器”和“舌人”。德莱顿虽反对译者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趋,但仍旧将译者看作是庄园里劳动的“奴隶”,“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卞之琳说得再恰当不过了:“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他转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孙致礼,1999:18)
3.解构主义对源语中心论的解构
源语中心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即用译入语将源语表达的事物重新表达一遍,这种转换实际上是用两种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它预设了源语和译语可以表达同一确定的意义。在源语中心论看来,文本意义的理解就是使客观存在的文本意义结构得以自然展现的过程。所谓正确理解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自己的偏见,回归文本的意义结构。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对文本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文学翻译要求译者把自己和原作者融为一体,与作者一起重新经历作品中所展开的快乐或痛苦的精神之旅,因为作者才有权力赋予他的作品以确定意义,译者的理解只是理解出文本固有的意义。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产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Bassnett,1996:13)。文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意义的实现有多种可能性,不同读者可能对文本获得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读者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作品意义的积极建构者,也就是说译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有可能发挥主体性和能动创造作用。解构主义对文本确定意义的解构,对翻译来说,打破了作者主宰文本意义的权威,破除了在传统译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翻译原意转换之说,传统的翻译被解构了。作者,这个文本的唯一来源,统领文本意义的权威不在了。源语中心论试图发现文本最终的、确定的叙事结构的努力也失败了;多元意义、开放的文本出现了,重写的、创造性的、主体的读者或译者诞生了。
其实,对作者权威地位的解构始于对文本意义的否定。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作者之死》中指出,以往的文学研究一直围绕作者展开,对作品的解释就是努力找出作者的意图,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带来的结果就是要得到作者一个人的声音,作者成了统治文本意义的上帝。他进一步指出,文本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神威要意”,文本写作既是消解意义,又是生产意义,同时滋生出多元的文本意义。作品的意义是游移变动的,不为文本所凝固。事实一经叙述,就与客观现实断开了联系,写作也就成了语言符号的游戏,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葛校琴,2006:229-230)。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文本的意义难以确定,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存在多重意义,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德里达主张用“转换”(transformation)来代替翻译,主张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翻译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被丢失和遭压抑的东西,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葛校琴,2006:122)。德里达把意义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不像结构主义那样将意义视为一个“终点”和“固定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复制原文本而是在文本提供的多重意义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译者是新文本的创造者,他的作用是催生出一个新的文本,衍生出新的思想,使人类的精神成果不断繁衍、增殖。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出发,译者是原文本的解构者,也是新生文本的创造者,但是译本一旦写成,译者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译本又会产生多重的意义,翻译就是意义的不断推迟和延异(differance),在这样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原文不断地被解构,译者成为文本的解构者。
4.文学翻译中的美学价值取向
4.1 文学作品中美学价值的生成机制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形式进行的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经过提炼、加工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魅力,往往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像空间。如果科学术语是约定俗成的和常规的语言,那么文学语言便是对常规的超越,是变异的语言。文学语言打破了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原有的联系,创造出由新鲜词汇产生的新意义,引起人们对事物的关注,并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因此,文学作品可以看成是作者所创造的语言符号世界。作者既是社会个体同时又是艺术家,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其独特的个人生活体验,必然会产生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看法和观点。在文学创造中,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表达他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思想和情感。文学作品的形象是作者用来产生心里画面的语言表达,同时又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我们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具有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形象能够激励读者充分发挥想像力,从而把作品所描绘的画面在大脑中加以形象化。在此过程中,读者在视觉和听觉上产生愉悦的感觉从而获得美学价值的享受。由此而论,文学作品的形象又具有美学价值。
文学作品是想象的艺术。本雅明(Benjamin,1992:71)在他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之所以成其为艺术,并不是在于它传达了什么语言信息,表达了什么内容,而是在于它是如何表达的。在文学作品中,作品不会给读者提供问题的现成答案。文学作品所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作品的一系列图式结构,其功能便是激励读者获得文本的形象,进而探索他想获得的答案。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图式结构显然与文学形象有关。但是,作品并不直接提供其文学形象,需要读者努力去发现和探索。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作品正是运用理解的基本结构来激励读者生产文学形象。事实上,作品要表达的意义或者作品的语言所直接揭示的意义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语言赋予了读者对其意义的开放性。文本的不完整性产生了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了文本意义之间的空隙,留给了读者想像的空间。由此,伊瑟尔(Iser)提出“空白”(blanks)和“具体化”(concret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读者通过“空白具体化”(concretization of blanks)这一过程,消除了文本的不确定性(Iser,1978:181-185)。在文本的整个图示结构中存在着许多空白,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一个个空白的过程中实现了文本的理解(Iser,1978:123)。
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一个被动的活动,需要读者发挥想像力和联想力。文学作品的一个诱人之处就在于读者的能动参与。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就像一个竞技场,读者和作者在这个竞技场上共同参与一个想像的游戏。在这游戏中,如果什么都给了读者,那他就无事可做了,阅读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枯燥乏味。因此,高明的作者往往会在作品中有意识地为读者留下许多想像的空间,即“空白”,通过空白的具体化,读者完成审美历程并获得独特的审美快感。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常会把其意向读者的,诸如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词语以及历史典故等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预设在文学作品中作为空白以体现他的美学创造和艺术动机,同时又给读者留下想像的空间。文学作品所预设的空白激励着读者发挥想像来填充,从而构建出作品所表达的形象。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一个个空白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审美快感,以及欣赏文学作品的“符号化的方式”(mode of significance)。
4.2 文学翻译的美学价值取向
解构主义使文学批评的聚焦点从以往关注作者的创作意图、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转移到目前关注读者的作用、挖掘文本言之未言之意上来。这种视角的转换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以往只关注原作者、原文本和原文意义的研究,转移到原文的读者,即翻译活动的译者中来,使译者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的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当下焦点。
读者作用,文本言之未言或不定意义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作者、文本以及意义的认识,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阅读时能够完全无视作者或文本结构意义的存在。在阅读和理解时,纵使有多种的意义和阐释,读者,尤其是译者还是不可能抛开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这个根基。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就其本质来讲,与其说是一种阅读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受到了制约的活动。译者的任务首先是重构作者的世界,进入作者的思想境界。译者不是原文作者,他充当的角色是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译文读者达到原文作者思想的彼岸。译者应以原文文本为准绳,发掘其深层的含义。译者通过阅读和对原作的整个世界进行重构,把握住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了解作者的意图、态度以及作品人物的感情等。
关于文本对阅读行为的制约作用,瑙曼(Naumann)提出了“接受指令”(the givens for reception)这一概念。接受指令指的是,在阅读行为前文本本身存在的各种要素。“接受指令”这一命题表明,文本不但生产出满足读者接受要求的物质材料,而且还生产出文本接受的方式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文本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结构和图式预先设定了读者接受的方向、读者的反应以及读者可能对文本的评价(范大灿,1997:17-20)。而伊瑟尔则用“图式”(schemata)、“文本范式”(textual pattern)以及“文本的整体系统”(overall system of the text)等概念阐释文本对于读者理解的制约作用。阅读过程就是读者对文本的“空白具体化”的过程,当文本的各个图式结构相互关联时,空白即消失,读者完成阅读活动(Iser,1978:183)。通过“空白的具体化”,即填补文本的空白,读者重新建构文本的“整体系统”,形成自己的理解,完成审美历程,获得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实际上,读者要填补的空白即“隐含性的东西”(something invisible),存在于文本的“整体系统”之中。“整体系统”是由文本的各个图式组成的结构。“整体系统”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指南,从而为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总的框架。因此,我们认为译者在阅读活动中创造性地理解和阐释文学文本时,原文作者并未消失,他的写作轨迹仍然是作品理解的重要框架,文本的“整体系统”或图式结构对译者理解和阐释文本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事实上,读者的阅读活动虽不在文本之中,但却受到文本的影响和制约。(Iser,1978:168)
“如果说,作者的本意由于作者处于历史性的演变之中会有所演变从而表现出一种不确定的话,那么,已经由作者完成并变成了一个客观存在体的文本,它的本意应该是相对确定的。”(谢天振,2000:25)如果解构主义一味夸大读者的作用,强调文本意义的游移、无本源,那么,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译者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性理解和阐释的合理性将陷入纯粹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美国文学解释学批评家赫斯(E.D.Hirsch)针对这种个体相对主义的文本理解策略提出了客观解释学理论。赫斯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原意,将它视为最好的意义,即最合理的解释标准”,“一篇文本的重要特点在于,可以从它分析出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各不相同的复杂的意义,而其中只有作者的意义才具有这种禀有统领一切意味的确切资格”。赫斯把作者的原意与作者的原意和阐释意义的叠加分别用“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来区别。他认为:“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它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符号序列中,通过他所使用的符号表达的意思。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或一种印象、一种情景、一种任何想像中的东西。”(Hirsch,1967:8-25)据此,赫斯将“意义”看成是作者或说话人的话语中所蕴含的意向性。他声称,不变的意义才具有客观性。只有寻找到这种客观的、已经存在的作者的原意,并排除自己的个体相对主义阐释因素,才能谈得上解释的有效性,否则所解释的意义不具合法性。
众所周知,翻译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是否在翻译中有什么指导原则来规约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呢?译者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有多少可看成是真实可靠的而必须融入到译文中,又有多少应该留给译文读者自己去探索和发现呢?奈达和塔布尔(Eugene A.Nida&Taber)指出了翻译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超额翻译(overloading translation),即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许多对原文的理解成分。他们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该避免超额翻译(Eugene A.Nida&Taber,1969:30)。第二个问题是欠额翻译(overloaded translation)。由于译者对原文的主题知之甚多,因而认为译文读者也和译者一样对原文的主题同样非常熟悉,结果翻译出的译文读者往往不能理解(Eugene A.Nida&Taber,1969:99)。有些译者由于自己本身又是文学批评家,因而更容易生产出超额翻译的译文,而有些译者忽视了译文读者的表示接受能力的信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要比原文读者小这样一个事实,因而生产出欠额翻译的译文,给译文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缺省成分。在翻译中,译者应避免这两种类型的译文。
的确,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文读者的信道容量要比原文读者的信道容量小,译者需要在译文中增加“冗余信息”(redundancy)以使译文读者对译文获得连贯的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在译文中插入他自己的主观倾向和看法。正如金堤和奈达指出,译者不是在重写原文,他在译文中不能增加他认为是有用的信息或者删掉太难的内容,他只能把原文中隐含的结构在译文中加以明确表达(Jin Di&Nida,1984:104)。译者不能把他从原文理解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通过译文传达给译文读者,否则就会损害原文含蓄的美学效果。由于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最感兴趣的往往不是作者说了什么而是作者未说的内容,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最值得译者重视的,就是不要剥夺译文读者发挥想像力的权利。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尤为重要,因为译文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满足于只是欣赏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译文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一是希望能够欣赏到外国文学特有的韵味,领略到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异国情调,二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想像力从而获得原文美学价值的享受。相反,如果译者在译作中因填满了原文的空白而剥夺了译文读者的想像力,那么,其译作便会同嚼过的甘蔗一样,失去了原文的滋味。因此,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不应忽视原作的存在,而应为译文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从而更好地展现原作的魅力。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文学语言的本质属性,也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张冰,2000:163)。根据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陌生化就是艺术性或是文学性的代名词,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陌生化的效果,也就不能称作文学作品。文学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是力图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拉近读者与现实的距离,而是刻意将“已知”的变成“未知”的,从而拉大作品接受者与表现客体之间的距离,给读者以咀嚼、体味与感受的空间。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指出:“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艰涩(difficulty),增加理解和感知的难度和时间,因为理解和感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上的目的,因而一定要加大和拉长。”(Brooker,1999:65)
文学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有一种求“异”的趋向,用作品中新奇的、陌生的东西来吸引读者,满足他们求新、求异的要求。因为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学翻译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美学价值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作的时候获得探索美学价值的享受。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坚持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信息取向,应尽力保持原作中的差异性和陌生性。任何一个旨在传达信息的翻译作品所能够传达的除了信息之外别无他物,而信息又是文学作品中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除了信息之外还包含一个最为本质的性质,即深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性的”东西——一种只有文学家译者才能够传达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用文学的美学价值取向取代信息取向。要想将原作中美学价值的东西传达出来,译者应通过适当的方法将原文中的差异性和陌生性这种具有美学价值和美学效果的东西在译文中加以预设,以便保持文学作品中某种“诗性”的东西,保持原文语言中的鲜活性和陌生性,因为文学作品最忌讳的就是使用一些失去新鲜感和陌生感的陈词滥调。
如前所述,读者在阅读中需要填补作者在文本中留下的“空白”。在译文的生产过程中,译者应该尽力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空白”。他应该把他理解原文时所填补的空白转换成留有“空白”的译文,以便译文读者同原文读者一样有机会填补原文的“空白”。因此,译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发现原文的图示,寻找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在目标语言中建构原文的文本图示和文本意图,从而使译文读者同原文读者一样能够欣赏到原作的美学价值,并获得美学享受。事实上,译者是洞察力最敏锐的读者,他在理解和阐释原作时,可能发现作者使用的诸如暗含意义、象征手法、文字游戏、双关语以及其它修辞手法所隐含的美学价值。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他应该把这些美学价值的东西留给译文读者和文学批评家。译者的任务与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不同,文学批评家可以在文学批评中明确阐释作品的美学价值,以便读者更好地从某一角度来评判作品的优劣;而译者永远不要忘记他是译者,他充当的角色是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译文读者达到原文作者的思想彼岸。译者必须在译文中隐藏起来,让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直接对话。虽然译者在翻译中不能完全避免个人的参与,但是他应该尽力减少其参与的程度,从而让译文读者尽可能地获得原文美学价值的享受。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是原作的直接阅读者,既懂源语又懂目标语,因而在欣赏原作的美学价值时具有优势。然而,他应该在译文中让译文读者自己去发现原作的美学价值,以便译文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
5.结语
通过以上对源语中心论的文本意义的解构,以及对文学翻译中再现原作美学价值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文学文本不应该只有一种理解和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复制原文本,而是在文本提供的多重意义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正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解构了作者或文本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作品获得了再生。但是,译者不应把他从原文理解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通过译文传达给译文读者。译者在理解和阐释原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原文作者使用各种表现手法所隐含的美学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他应该把这些美学价值的东西留给译文读者,不能因填满原文的空白而剥夺译文读者的想像力从而损害原文含蓄的美学效果。因此,译者应该尊重原文作者的艺术动机和美学创造,认真审视原作中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所隐含的美学效果,根据原文的具体情况和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尽力再现原作的美学价值。
[1]Bassnett,S.The Meek of the Mig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C]//R.Alvarez& M.Carmen-Africa Vidal.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6.
[2]Benjamin,W.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C]//R.Schulte& J.Biguenet.Theories of Transl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3]Brooker,P.Cultural Theory:A Glossary[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
[4]Hirsch,E.D.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5]Iser,W.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6]Jin Di& E.A.Nida.On Translation[M].Beijing:China Translation Press Co.,1984.
[7]Nida,E.A & 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8]范大灿.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9]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2]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3]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