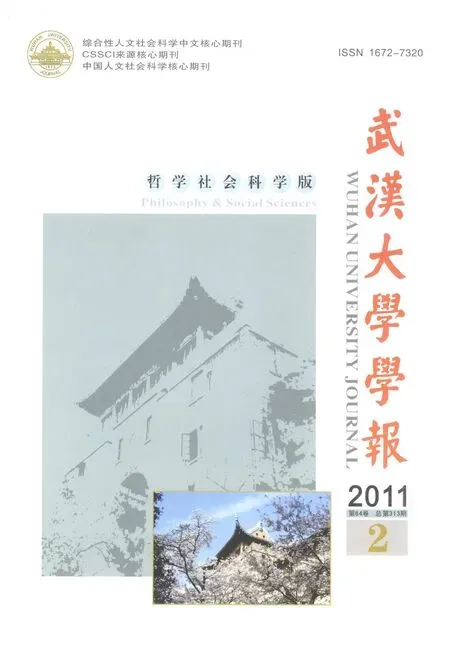经济共和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分析
储建国
经济共和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分析
储建国
西方社会有一种经济共和主义传统,它源于对原始社会生活的回忆,以及对理想城邦生活的一种想象。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研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又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现实分析而超越这一传统,将应该追求的共有、共治和共享的经济生活解释为必然发生的事。这种将规范批判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产生了经济政治研究的一个飞跃,但也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经济政治分析;经济共和主义
对经济生活做政治的分析,以揭示其中支配性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经济政治研究的一大特色①刘德厚教授认为这种研究应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经济政治学,参见刘德厚:《关于建立经济政治学的几个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43页。。这种特色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其深厚的传统,那就是源远流长的经济共和思想。这个传统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政治和经济没有分开,寻求一个共和的城邦,既包含了政治生活,也包含了经济生活。在一些古代思想家的眼中,一种共和的经济生活也就是一种正义的经济生活。这种经济共和思想是对原始社会共同生活的一种留恋和改造,它后来一度衰落和消失,到近代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经济共和思想蕴含着对现实经济的正当性追问,它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经济政治研究的思想来源。
一、共和传统与马克思规范批判的标准
怀有古代共和理想的人都会对经济生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感到不安,对剥削和压迫感到愤怒。马克思正是这种愤怒者队伍中的成员。这种愤怒是一种义愤,是因为看到别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而感到的愤怒。这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愤怒者心中已经有了正义的标准。就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标准通常是通过社会教育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近代欧洲知识分子心中的正义标准恰恰来自共和主义传统。年轻的马克思对社会压迫现象充满愤怒,他的这种愤怒与近代欧洲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共和主义教育无疑有着密切的关联。只不过,思想敏锐而深邃的马克思将这种愤怒的根源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生活。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憧憬三代之治那样,马克思恩格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始共同生活进行了美化,认为在朴素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基础上,古代人类曾经有过和谐的共同生活,也就是在一种真实的共同体中所过的生活,一种没有异化的生活。
“异化”之所以成为早期马克思论说中的核心概念,与他心中那种没有异化的原始生活有关。在他进一步的描述中,这种生活也就是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化、没有国家强制的生活,或者类似柏拉图所说的,“我”和“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分的共同体生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协调一致的生活。当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之后,共同体依然存在,而且以国家的面目出现;表面上国家代表公共利益,但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分化甚至对立的状态下,公共利益只是幌子,国家真正代表的是私人的利益,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建立在阶级统治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页。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借用他的异化概念,可以认为,这种共同体是从真实共同体那里异化出来的,失去了原来共同体中的那种和谐与统一,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分裂与冲突。
将这种逻辑运用到经济领域,需要对异化概念进行某种改造,马克思因此而形成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在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共同体中,不存在一个人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压迫别人的现象,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如何在自己的支配下享用的。因此,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自己能够支配劳动的过程和成果。异化劳动表现的核心是人的异化,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论承继了费尔巴哈的还原式思维方式,它先在理论上设定一种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转而用这个“本真的标准”去监测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即“本真状态→异化状态→复归本真状态”③孙 亮《:“类本质异化”思维方式与“费尔巴哈思想遗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这种本真状态究竟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层次描述中概括出非异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人通过劳动能够满足人之为人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身体保存与愉悦的需要(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自我控制的需要(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过程)、自我尊重的需要(通过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能动地、现实地实现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2-101页。。如果简单一点,可以把这种人之为人的需要表述为“人需要保存自我、愉悦自我、控制自我、尊重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自我与那种原子化的自我不是一个意思,前者是一种类的自我,一种社会关系总和中的自我,一种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自我。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然而,谈论人的异化离不开“一个本真的人”、“一个标准的人”、“一个理想的人”之类的前提。马克思显然对于先验地谈这个东西感到不满,他希望从历史中、从现实中、从社会中去寻找真正人的标准。马克思经过考察,发现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而自由自觉的劳动则是真正人的标准。所谓“保存自我、愉悦自我、控制自我、尊重自我和实现自我”就是“自由自觉”的含义,而马克思强调的核心又是在控制、尊重和实现三个方面。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比较起来,这里非异化的人(理想人)的需要显然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想个人只有在理想社会中才能达成,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和谐与发展的。原始社会提供了某种相互和谐的原型,通过公有制和民主制达成某种程度的控制自我和尊重自我,但在实现自我方面显得非常落后。而这种“落后”的结论又是通过与后来的社会相比较而得出的。马克思似乎通过了一种“反思提升”的方法,通过对人类发展的过去与现在进行相互比对,发现了理想人和理想社会的标准。理想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自由自觉的人,理想社会则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通往理想人和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改变那些让人异化、让劳动异化的社会关系,发展那些让人通往自由自觉之状态的社会关系,而这里面最核心的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因此从哲学批判走向了经济政治批判。这种转向尽管有分析思路的变化,但有着价值标准的一致性,那就是前面所说的理想人和理想社会,而这种标准就是共和思想的标准,与古代共和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二、从规范批判到现实分析
马克思不是像一些具有古代共和倾向的学者那样,停留在简单的规范批判层面,而是转入了经济政治的现实分析。他又像古代共和思想家那样,认为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生活不仅需要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且需要体现人的价值。而现实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贬低人的价值,其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用更清楚的语言来说,就是少数人占有和支配着多数人的劳动,让多数人丧失了人的价值。所以,马克思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核心任务就是证明一部分人的劳动是如何被别人占有和支配的,并因此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而这里面的一个逻辑关联就是非异化的劳动或者说自由劳动构成了人的价值的核心内容。
在批评近代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观点予以简化,那就是资本家通过支配工人的劳动过程而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因而,马克思将前面那些人的需要简化为一个需要,那就是人支配自己劳动的需要,一个人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为衡量这个人是人、而不是非人的关键标准。这种“非人”是“奴隶”的代名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讲得很明白:“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0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想让政治经济学成为研究如何让人成为人的学问,反对那种将人变成奴隶的学问。这是古代共和传统的重要体现。
然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能够通过计算来进行研究的学问,也就是说能够进行定量的研究。马克思需要将那些关于人的定义的抽象概念进行量化处理。“异化”的概念很难量化,马克思放弃了这个东西,但死死抓住“劳动”这个概念,并希望通过不那么复杂的加减乘除,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明白自己的劳动是如何被别人支配,并让自己变成另一种奴隶的。
马克思首先沿续源自亚里士多德、由亚当·斯密发扬光大的做法,将劳动视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来源。商品首先是用来满足人的某些需要的,不能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这种价值被称为使用价值。这种看起来似乎最重要的价值却是一个难以分析的东西,在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分析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关键是要看一件商品在同另外一件商品交换时所体现的那种价值,它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只有确定了这种关系和比例,不同的商品之间才能进行交换。寻找这种量的比例关系,是西方学界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进行的努力,而且从一开始就指向人的劳动。
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继承了古希腊思想中寻求“共相”的传统。将两种东西进行比较,如果说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相等,那么它们当中必存在不同于这两种东西的第三种东西,而且是更为抽象的东西。马克思将这种思维过程称为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过程,这种本质或共相也是一种物,一种抽象物,那些具体物因含有这种抽象物而统一起来。各种商品所含有的那种抽象物就是劳动,它不是产生于自然界,而是产生于社会,是“共同的社会实体”③《资本论》第1卷,第12页。。
这样,马克思运用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将商品之间的经济关系界定为社会关系,在古代的思维里,这种社会关系也就是政治关系。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性的交换——因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
如此之后,商品之间的确有了一个比较的基础,但这种抽象物如何衡量呢?这又需要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最具体又最容易计量的单位就是劳动时间。这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威廉·配第曾在《赋税论》中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看法。他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斯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④威廉·配第《: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2页。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高度,成为“用劳动时间确立价值的宗派领袖”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之后,劳动价值论便从一种哲学的规范批判转变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分析,但这种转变会带来价值的减损。
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量,实现了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的转化,但这个劳动时间显然不是任何个别的劳动时间,否则就无法比较,否则那些越懒、越不熟练的人生产的商品反而越有价值,因为这种具体的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比较多。为了克服这种荒谬的结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形成价值的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资本论》第1卷,第13页。这种说法跟斯密对自然率的表述方式差不多,他们让“一般社会条件”成为决定自然价格(接近真实价值的价格)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所说的“正常的生产条件”应该指的是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它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②《资本论》第1卷,第14页。。这里面讲的主要是技术因素,包括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换句话说,“技术”构成劳动价值的一个限制条件。
马克思接着又对劳动价值施加了另一个社会性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必须生产出对别人有用的东西,“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③《资本论》第1卷,第15页。如果生产只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那就只是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或商品价值。马克思没有讲这类产品没有价值(使用价值),因为它们还是对人类有用。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这样的劳动就没有价值,马克思甚至认为“不能算作劳动”(一种比较奇怪的表达)。可是,什么叫“有用”呢?这种判断基本上取决于具体人的偏好,你生产出任何人都不要的东西能具有价值吗?因此,“偏好”也构成劳动价值的限制条件。这个条件似乎没有技术条件那么强,因为只要是别人需要的东西,能够进行交换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里面的价值量就不取决于需要程度,或偏好强度了,而是取决于里面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跳跃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两种产品,尽管都花费了同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它们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价值如何比较呢?马克思认为,任何劳动都可以换算成某种简单劳动,也就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④⑤《资本论》第1卷,第18-19页。这样解释之后,一方面给换算带来了方便,另一方面则也带来了不同劳动在价值上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裁缝一个工作日的价值有可能相当于雇农两个工作日的价值。这仍然可以归结为技术所带来的差异。
然而,在商品交换中,劳动时间仍然是一个不能抓在手中的东西,它需要以某种东西表现出来。在物物交换中,一件商品构成另一件商品的价值表现,即简单相对价值形式。当另一件商品成为衡量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形式时,简单相对价值形式便发展成一般相对价值形式,这件商品便成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理论上,任何商品都具有货币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成为货币。”⑥《资本论》第1卷,第55-56页。但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专门成为货币的商品需要某种社会权威的确认,从而成为其他商品共同的价值尺度。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相对价值量就是价格,这种转化完成后,在技术上就将价值尺度的问题变成价格标准的问题了。可是这种转换一旦发生,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也就发生了,价格可以表现价值量,也可以表现其他的东西。当价格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时,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表现⑦《资本论》第1卷,第69页。。
货币不具有普通商品那样的使用价值,但拥有它,则意味着拥有各种潜在的使用价值。因此,在通往商品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占有普通物品的欲望迅速转化为占有货币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仅是一种消费欲,而且是一种权力欲。占有货币意味着占有了权力,它是从古代社会权力中分离出来的私有权力。马克思描述道:“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①《资本论》第1卷,第101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古代共和秩序的解体是非常敏感的。
为了占有更多的货币,或者说,为了占有更多的私有权力,一些货币拥有者便想方设法地用手中的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马克思认为,一些货币拥有者开始追逐货币—商品—货币的过程,与普通商品交换者追逐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有质的不同。前一个为卖而买的过程让货币成为资本。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认为,交易的原本目的是以有余换不足,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后来发展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贩卖”,那就是不合乎自然了。他们所用的手段相同,但所求的目的不同,而且后者这个目的是没有限度的,让人们把一切才德都用到这个目的上,破坏了城邦的优良生活。“贩卖”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而从“贩卖”那里发展出来的“钱贷”更加可憎,它强使金钱进行增殖。“如今本钱诞生子钱,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到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32页。这里所谓“不合乎自然”,也就是不合乎正义,不合乎理想。其实马克思所谓“异化”的思想也渊源于亚里士多德,他的前述思想的展开让人明显感受到亚氏的气息。一种东西产生出来,背离了其原初的好的目的,那就是违反自然,就是异化。马克思欣赏亚里士多德对高利贷(就是前面所说的“钱贷”)的谴责,引用他的话说,“所以,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是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③《资本论》第1卷,第135页。
在原有货币额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增殖额,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本所有者的目的。他通过经典的分析,揭示这种增殖额的实质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坚信,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是资本家通过支配工人的劳动而侵占的。在马克思眼里,这种生产关系是一种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尽管不满足于这种道德化的词汇,但这种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他不会那么愤怒地描述工人被剥削的现状。那些描述只能表明“不人道、不公平”之类的词汇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用“罪恶的”一词可能更合适。这种愤怒延续了古代共和的思想,也就是要“把人当人”的思想,让人们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享有尊严的思想。没有这个思想,马克思是不可能写出那些文字的。马克思大段地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文字,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的经济政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经济政治思想的升华,所以,马克思称他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经济政治的现实分析并没有脱离其规范批判的标准,反而是更强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马克思所拥有的古代共和的情怀。
三、替代的经济共和方案
由于揭示了现实经济中交换的自由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生产领域中的剥削关系,马克思无法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共和方案上往前走。他们尽管都具有古代共和的情怀,但马克思显然更为激进,更为彻底。他的经济共和方案要变革斯密没有触动的生产关系,所以他批评现实中的共和国是形式的,是虚伪的,而他要建立的共和国是实质的,是真实的。因此,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社会共和国的秘密就是马克思所开设的经济共和方案。如果理解了从古代到近代共和的理论与实践,就能理解马克思经济共和方案的奥秘。
我们要牢记,马克思的经济共和方案不只是经济方案,更是一个社会方案,它是对原始公有制和民主制的一个升华,是包含了后来发展进程中富有生命力的新因素的升华。这种新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人的解放,二是社会的联合。在结合这两个新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马克思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共和方案,一个引起众多争议的方案。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上来重新建立。”①《资本论》第1卷,第731页。
如果理解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结合他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描述,这段话应该不难理解。马克思描述了三次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否定,这种私有制是一种小生产私有制。第二次否定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第三次否定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新个人所有制对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
第三次否定实际上是将两种私有制中的自由个人的因素与社会性的因素结合起来,完成了对原始公有制的升华。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是新的个人所有制,而不简单地以公有制称呼它,是因为他想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公有制与原始公有制是不同的。要理解这种个人所有制,需要在“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社会理想下面,从共有、共治和共享三个层面来理解这种经济安排。
就共有层面来说,新个人所有制的一个基础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实际上是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自觉地占有,而不是像原始社会那样自发地占有。至于这种共同占有的形式,是值得讨论的,由联合起来的地球人进行共同占有大概符合马克思的理想状态。在各个特殊的国家、社会、群体还被某些力量阻隔的情况下,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股份制之类的个人共有制都是一些过渡的状态。
就共治层面来说,新个人所有制的另一个基础是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制或简称自由协作制。这个基础的重要性决不亚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的表述中甚至被放在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愤怒在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受资本家支配,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是与西方自古以来的那种“自由人”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是人的异化的最核心的含义。要摆脱这种状态,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基础,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具有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制基础。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协作制呢?马克思给协作下了一个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②《资本论》第1卷,第307页。这种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新的生产力,这种力叫集体力,它大于个人力量之和。马克思又一次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③《资本论》第1卷,第307页。其实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国家与社会是没有分化的,政治动物就是社会动物。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管理是一种专制的管理,是主人对奴隶的管理。“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剌斯坎的祭司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象股份公司那样的结合资本家。”④《资本论》第1卷,第316页。很明显,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者的协作是与这种专制的管理相对立的,意味着一种民主的管理。
就共享层面来说,新的个人所有制的一个结果就是自由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恩格斯将新的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理解为对消费资料的所有。就共享层面来说,他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新的个人所有制不只是指共享层面,还包括前面所说的共有、共治层面,尤其是“自由劳动者协作”的共治层面,是马克思之后的那些阐释者有所忽视的地方。
四、结 语
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分析主要是写给工人阶级看的,因此他尽可能让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他的整个思想就是想讲明白如何在经济生活中“把人当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或者说继承了更久远的共和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强调人是有目的的动物,人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变得更像一个人,而这种追求需要群体性的努力。可是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从劳动异化到劳动价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讲人的目的时,有三层意思:一是能够活着;二是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三是能够幸福地活着。其中第二层意思是马克思所在乎的最核心的标准。这种尊严的含义来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由人”,如果用否定方式来表达,就是某种“非奴役”的状态,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可以任意地干涉你的行为而你无法拒绝时,你就处于这种状态。马克思发现工人相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处于这种状态,那是一种剥削的状态。因此,摆脱剥削既是马克思的哲学主题,历史学主题,又是其政治经济学主题。这个主题是西方共和传统中“自由人”概念的延续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憧憬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①《资本论》第1卷,第247页。围绕这个主题,他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了揭露,对理想经济生活进行了描绘。作为西方共和传统的一个延续,这项工作究竟在哪些地方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呢?
首先,这项工作不同于西方共和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非历史地谈论正义问题,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也就是把一个应当发生的过程变成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但这里面存在逻辑上的困难,你即使发现过去的历史中存在某种趋势,但你凭什么判定这种趋势是好的、进步的、正义的呢?因此还是需要非历史性的想象和推理,一种基本层次的正义原则是不依赖于历史过程的,尽管这种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②G.A.Cohen.Self-ownership,Freedom,andEqual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p.14.。恩格斯那种关于“自由人”的表达就是跨越历史的,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理想的标准,但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对“自由人”的具体内容进行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心中存在非历史的正义理想,但这种理想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能实现,他们试图脱离那种纯粹道德的指责,而将这种理想的实现描述为一种必然的规律,从而让它更为人们所确信。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让人们产生了某种科学的狂热,或者说迷信,让“对社会的研究”屈从于“对自然的研究”,从而让那些不能够科学化的东西也科学化了。马克思也不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所以才有“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的想法。
其次,为了充分突现剥削的不正义,马克思运用了劳动价值论,并发展了剩余价值论。如前所说,劳动价值论源远流长,但马克思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含义。他的关键点在于认为商品的价值反映的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内含于其中的“共同社会实体”,或者说反映了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的本质,或类本质,这个东西就是劳动。理解这层意思非常关键,因为这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联结点。在以前的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者那里,是不需要这个联结点的。有了这个联结点,我们才可以理解哲学中人的异化概念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中以剩余价值概念呈现出来的。概念上的替换也许并不重要,譬如说,将“异化”换成“剥削”也许会有强度上的差异,但并不影响实质性的关注。关键是要论证那种剥削关系是存在的,是不正义的。马克思经济政治分析的核心任务是证明它的存在。但他在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难以处理的连环套: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受社会需要的约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社会需要一般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到生产者那里,从而导致社会劳动时间在不同商品间的转移,于是出现了“价格—价值—需求—价格”的约束循环。尽管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转化”工作,但分析的困境依然存在。马克思在继承古代经济共和思想的同时,试图运用现实的科学分析超越那种纯粹规范性的批判,但如何将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仍然是摆在当代经济政治研究者面前的棘手任务。
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ZZ00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5CZZ003);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责任编辑:叶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