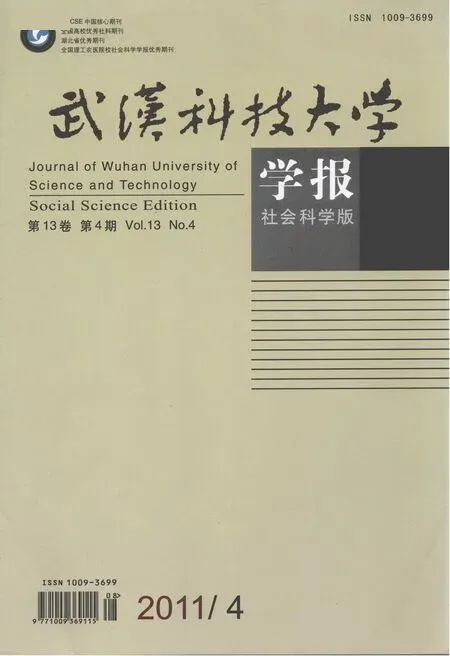“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变化,国家权力从农村基层有所退出,国家从农村社会提取资源日益困难,提取成本不断攀升,乡村治理面临困境。在此背景下,乡镇基层政府将一些能够有效完成税费等资源收缴任务的乡村混混和“强人”纳入村级干部体制参与乡村治理,尽管这些乡村混混和“强人”品行恶劣,但由于能力强而被委任为村干部,导致1990年代“有才无德”村干部在农村大量出现,这种状况即使在农业税取消后也未发生实质改变。本文根据对两湖平原地区十几个村庄的实地调研①这十几个村庄都是农业型村庄。按照社会科学的匿名规则,本文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已作处理.,从村级治理层面对这一悖谬现象进行探讨,以揭示其原因。
一、村干部的“才”“德”悖谬
在两湖平原地区农村调研时,常听到村民对个别村干部的评价:“这个人贪污、霸道,还乱搞男女关系,道德非常败坏”,而乡村干部对此的评价却是:“这个人虽然道德作风不太好,但确实很有能力”,语气中颇有几分赞赏,这构成了村干部“才”与“德”分离的悖谬。
在调研中还发现,那些评价迥异的村干部,大多与乡村混混能扯上关系,要么这些村干部本来就是混混,要么与乡村混混是合作或同盟关系,要么亲人或朋友中有非常厉害的混混。而乡村混混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常常在乡村组织中寻求“靠山”,与乡村干部保持良好关系。
C市沙桥村村支书万某与乡村混混保持着“同盟”关系。万某贪污、侵占集体财产,道德十分败坏,但其工作“能力”却得到肯定,“当政”十多年来,沙桥村被治理得“很好”,各项工作都位于全镇前列,万某也因此颇得镇领导重视和支持,镇书记、镇长换了几任,对他的支持却始终没变[1]。与沙桥村临近的李集村村支书的侄子、副村支书的儿子都是混混,他们常常借助混混的力量治理村庄。例如,2004年,村民因抗旱问题准备上访,村支书出面阻拦,村民们指责他失职造成抗旱缺水,冲突中一位60多岁的农妇被村支书推倒而骨折,这激怒了在场的村民,近70人将他围起来,而当村支书的儿子和侄子带着钢刀赶到,在场村民就没有人再敢说话。
J市尚武村的村干部也与混混有着复杂关系[2]。治保主任黄老四,家有兄弟六人,全乡无人敢得罪,六兄弟中,最先“发迹”的是老大,黄老大胆子大、狠气重、心计多,1980年代末就当上了村主任,并从这个位置上侵吞大量集体资产,捞取了“第一桶金”,后来又很传奇地在乡电管站站长、开发区某居委会主任和乡兽医站站长等好几个“油水多”的职位上任职。黄老大当村主任时,让老四当了小组长,老四后来也成了村干部,据说老四是“六兄弟中最本分的”。老五曾当过乡粮管所主任,后成为市粮食局干部。老六原来杀猪卖肉,后来开饭店,现在农贸市场收管理费。黄家老六主导着全镇猪肉价格,致使当地猪肉价格高出周边其他集镇。黄家兄弟黑白两道通吃,心齐手狠,打架一起上,没有一个村民不害怕,在当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镇上的混混对黄家六兄弟非常敬畏,有事随叫随到。四组组长廖某,以前因“混社会”触犯法律逃窜在外。在四组,组长工作很难开展,长期有人跟组长对着干,曾出现前几任组长多次被村民殴打的情况,前任组长就是因被村民殴打而撂手不干。1981~1989年期间,四组就先后换了四任组长,基于这种状况,村里认为只有廖某出任四组组长才能“摆平”四组的“混混兄弟”和“大社员”,并许诺在公安部门抓捕时给予庇护,就这样廖某当上了组长。廖某任组长后,依靠那些“混混兄弟”打击出头闹事的“刺头”,使四组得到“有效”治理,同时也利用各种手段捞好处,侵吞集体生产费和管理费。
1990年后,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工作中,存在乡村混混和大社员不交税费、不出义务工等现象,村干部通过正常合法途径奈何不了他们,往往不能完成上级任务,而混混背后组织势力强大,普通村民十分畏惧,因此,混混被体制吸收成为村干部,或者村干部借助混混对村庄进行治理,往往能够高效率地完成任务。但是这种治理格局却是以集体资源不断流失以及村集体以至政府的合法性大受侵蚀为代价。一旦“有才无德”村干部登上村庄政治舞台,必然会在村庄内部更加肆无忌惮,想方设法侵蚀集体资源、谋取个人利益。他们谋取利益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截留上面下拨的款项,如救济款、扶贫款和工程款等;二是变卖山林、堰塘和果场等集体资产;三是收取税费时搭车收费。在上述村庄中,到1990年代末,村集体资金大多被耗光。
在两湖平原,“有才无德”村干部非常普遍,在我们调研的5个市(县)的11个村庄中,有7个村庄的主要干部属于这种类型。J市的尚武村、C市的沙桥村和李集村、L市的付村以及S县的邓湾村,近十多年来一直由混混或与混混关系密切的村支书“当政”;C市的临沙村与混混关系密切的村支书三年前才去职;M县的湖场村一直由兄弟多、做事霸道的“强人”担任村支书;只有 Z市的普村、X市的陈村和C市的新王村、王村,近十年来一直由“老实”的村民担任村支书。
二、基层政府的态度与困境
在两湖平原,乡村混混一般都会与乡村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对于这种“良好”关系,既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可降低“混”的风险的应对之策,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黑白合流”的表现[3-5]。乡村干部为何要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将他们吸收进村组干部体制中呢?这固然与乡村干部的腐败有关,但更多情形下并非如此,而是与特定治理背景下的乡村两级行为逻辑有关。
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村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实际情形与法律规定有很大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6-7],这个乡村利益共同体几乎决定了乡村两级的行为逻辑。
乡镇基层政府承担着向农民收缴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及殡葬改革政策等各项目标任务,尤其是税费收缴工作,其完成好坏是县市级政府考评乡镇基层政府政绩的主要依据,也是乡镇基层政府支付教师工资和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主要财政资金来源,对乡镇基层政府意义重大,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1994年中央财政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权小责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成为常规,县乡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几乎总是不堪应付,这样,县乡财政就严重依赖于农民上缴税费。
乡镇政府在收缴税费及执行政策时无法直接深入每家农户,因此村干部的作用和地位显得尤其重要。而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从理论上讲代表村民利益,并没有协助乡镇政府向农户收取税费的积极性。乡镇政府为了及时、足额地完成税费收缴任务,需要从经济方面(直接撤换、点名批评等常规行政手段,对于处在正式行政序列之外的村干部而言并不十分在意,他们更在乎实际的利益)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因此乡镇政府常常以默认甚至鼓励的方式,默许村干部在收取税费时搭车收费,损害村庄及村民的利益,如低价变卖村集体资产及向村集体高息放贷等。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不是选举产生的村干部,都愿意在乡镇政府的默许乃至鼓励下捞取好处。组织分散且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无法抵抗,村集体利益受损,造成村民不满进而上访,乡镇政府尽管对村干部的劣迹十分清楚,但也不会进行查处,因为查处一个,就会影响其他村干部积极性。
乡镇政府默许村组干部借机“搭车收费”、贪污、侵占集体财产并适时予以庇护的前提是村组干部能力要强,能够完成税费收缴的任务。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危机日趋严重,农民负担问题成为整个乡村治理体制的关键,税费收缴成为最困难的一项工作,特别是“钉子户”的出现及其治理对村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钉子户”的存在在熟人社会中会产生巨大的扩散效应,一户不交税费,其他农户也会跟风不交。
“钉子户”有两种,一是“问题户”,其以乡村干部解决自己特定问题为缴纳税费的前提;二是“无赖户”,他们没有特别原因,就是拒绝缴税。在“钉子户”之外,还存在由于家庭特别贫困而缴不起税费“特困户”[8]。在村庄熟人社会内,这三种类型比较容易区分;但在治理层面及工作实践中,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认定“特困户”非常困难。尽管村庄中大家都知道谁“特困”,但“特困”与困难是连续分布的,缺少让所有村民信服和可供操作的认定标准。一旦“特困户”税费得以减免,更多困难户也会要求照顾,从而最终影响税费的收缴。因此,对于“特困户”,乡村两级不能随便“开口子”。但只要有“开口子”的可能,就会有困难户拖延缴纳税费。因此,拖欠和催缴就变成了村民和乡村两级围绕着“开口子”所进行的一场博弈,对“特困户”的照顾迟早会催生“无赖户”。那些借口困难而长期拖延缴纳税费的村民就变成了乡村两级眼中的“无赖户”。
其次,区分“问题户”也非常困难。对于“问题户”所提出的问题合理与否,乡村两级和村民之间常常缺乏统一认识而难以区分。对于政府来说,缴纳税费是每个农民的法定义务,任何“问题”都不能构成不履行义务的理由,而农民的逻辑可能是:你想要我缴税,就得解决我的问题。但关键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边界,任何问题都找政府,且不说问题不合理,即使是合理问题,也可能无法解决,政府的解决能力毕竟有限。因乡村两级财政能力有限而致使农民合理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状况在1990年代的中西部农村非常普遍。对于乡村两级看来“问题”不合理的“问题户”,很容易被归纳进“无赖户”一类,进而予以打击,但如果“问题户”的“问题”合理却无法解决,会给乡村两级收税造成很大麻烦。
基层政府收缴税费的困境在于:少数农户,无论其理由是否合理,无论政府能否将其区分(这种区分一方面并不能使不具合理理由的农户缴税,另一方面,区分出来的合理问题政府却可能无法解决),总是拒绝缴纳税费,因此基层政府最简单的做法是不予区分,对所有不缴税费的农户都强制进行征税。但强制征税的过程中,工作重点是打击“无赖户”,通过“拔钉子”抑制其不缴税费的扩大效应。
三、“有才无德”村干部的比较“优势”
将欠税农户诉至法院、集中力量“暴力收税”及乡村混混替代征税等是重点打击“无赖户”的主要方法。但哪种方法为最优呢?“有才无德”村干部又是如何在其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呢?
应该说,将欠税农户诉至法院这种方式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可以省却许多麻烦。按照法律,依法缴税是农民的法律义务,贫穷、“问题”等都不构成抗税的理由,法院进行判决很容易,但判决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判决的执行同样需要由农民缴税来实现,法院试图去执行生效判决,难度比乡镇政府收税更大,如果判决无法执行,只会伤及法院自身的权威和司法的合法性。当法院遇到抵制时,社会影响会更糟糕。事实上,在1980年代就出现了诸多法院介入强制征税招致抵抗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非常坏。而且,一旦法院介入税费收取,法院事实上就会成为农民和乡镇政府之间矛盾的仲裁人,而在治理危机深重的1990年代,法院根本就无法担此重任[9]。因此,最高法院从1993年开始就多次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法院不得参与收取税费工作,也不受理行政机关对农民税务争议所提起的诉讼,但对于农民不满行政机关加重税费负担的,可以受理。这意味着在地方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中,法院只能“救火”,不能“加油”。
集中力量“暴力收税”的方法也行不通。虽然通过组织收税“小分队”、出动派出所公安干警、强制开办“法制学习班”等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会使农民对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容易导致恶性事件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恶性事件多发,中央一再明确规定不允许用“小分队”强行“暴力收税”,公安部门也规定严禁警力介入向农户收缴税费事务。
乡镇政府收缴税费可以借用的各种力量日趋减少,征税难度却日趋增大。乡村两级完全陷入税费征收工作,税费征收成为1990年代的日常工作和中心工作。在欠税日趋严重的条件下,各种办法被想出来,提高平均税费以填补欠税所造成的空缺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方法会导致新的欠税,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缴税,甚至缴纳不起税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混混、狠人及“有才无德”村组干部浮出水面,在收税、征地这样的事情中,乡镇基层政府办不成的,交给乡村混混和“有才无德”村干部却能办成。因此乡村混混、狠人及“有才无德”村组干部成为乡村干部拉拢的一种资源和力量,被吸收进村组干部体制内。从治理手段上讲,利用乡村混混和“有才无德”村干部确实是成本较低的选择。一位官员讲,只要不出恶性事件,可以“为我所用”。基层政府基于治理层面的需要,容易与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把其作为收税的替代手段。
对乡镇基层政府而言,吸收乡村混混及狠人进入村组干部体制,默认“有才无德”干部的存在,可以实现多重目的:
一是混混及“有才无德”村组干部不讲理、“讲狠”,使用暴力能够顺利完成税费收缴任务。在乡村混混及“有才无德”村组干部那里,不存在农户家庭困难不困难的问题,也不存在“问题”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因为混混及“有才无德”村组干部给农民的起点预期就不是合法和正义的,他们不讲理,只讲狠,家族势力比较强,背后还有着庞大的乡村混混关系组织网络,普通村民对其没有不畏惧的,因此往往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碰到混混来征税时,二话不说,赶紧交了了事,以免“鸡蛋碰石头”。而普通的村干部因在那些“无赖户”面前毫无威信,甚至可能受到人身威胁,也大多选择不作为。这样,“有才无德”村干部和混混不讲理不讲法,反而能够高效率地完成收缴税费的任务,比那些德行高尚的村干部表现得“有能力”得多。
二是矛盾得到转嫁。混混及“有才无德”村干部收税也会遇到麻烦,甚至也会与不怕狠的村民发生冲突,导致恶性事件。但这种恶性事件与乡镇基层政府卷进其中的恶性事件毕竟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农民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乡村混混被吸收进村组干部体制以后,基层政府某种程度上从收取税费的矛盾中抽身出来,相对置身事外,而矛盾被转嫁到村庄内部,转变成为村庄内品行败坏的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直接的部分就转变成为混混村干部与那些不与之合作的其他狠人、混混之间的矛盾。从治理技术上说,依赖乡村混混,将他们吸收进村组干部体制中收取税费,比政府亲自组织收取税费要优。尽管将乡村混混吸收进村组干部体制会导致政府合法性的降低,但这种政治风险要经历缓慢的增加过程,具有非即时性,而政府亲自组织收取税费所导致的政治风险则是即时的。一旦基层政府可以有限地置身事外,它就可能成为村庄矛盾的裁判者。当收税导致矛盾和恶性事件时,受欺负的村民可能到县乡去上访,去告那些贪污腐败、品行恶劣的村干部。但县乡政府很明白,收税已经将他们和村干部连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虽然县乡可以处在矛盾裁判者的位置上,但不可能成为公正的裁判者,他们往往成为“有才无德”村干部的庇护者。
三是工作中的抵制分子得以减少。因为抵制缴税的往往不是老实的农民,而是村里的混混和大社员。
正是乡镇基层政府基于治理的切实需要,以及“有才无德”村干部在村级治理中表现出的特殊比较“优势”,才使得“有才无德”村干部长期得以合法、合理存在。
四、悖谬现象的意蕴
乡村混混成为“有才无德”村干部,这在本质上回应的是,在村级治理中应对钉子户问题,其“有才”就体现在能够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手段将税费收起来,其主要特点在于依赖乡村混混的暴力手段治理钉子户,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暴力,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近代以来,收取税费过程中的钉子户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不得不增加从农村社会的资源提取,以建立现代警察制度、教育制度及发展现代军事工业等。传统的基层治理制度难以满足从农村社会提取大量资源的要求,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现代行政体系,以有效地从农村抽取资源。晚清至民国,在抽取农村资源和国家政权建设之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国家政权未能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而是靠复制扩大旧有的代理人制度,从而造成了政权内卷化[10]。国家机构没有提高效益,从农村抽取的资源大多被增加的中间机构所消耗,从而导致基层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并产生了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组织体系延伸到农村熟人社会的最基层,能够有效地从农村提取资源用于现代化建设,并由国家直接组织村庄进行公共品供给。在高度革命化和道德化的环境中,钉子户治理几乎不构成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要继续从农村提取资源,但又放弃人民公社体制,这导致收取税费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压力下,乡村混混被吸收进入村组干部体制,迫使村民交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两级的税费压力。在村庄层面,传统的宗族制度受到破坏,国家力量的撤出使得村庄公共品缺乏制度化供给机制,为乡村混混提供了活跃其中的制度空间。他们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以不具合法性的暴力进行钉子户治理。这表明,基层治理陷入困境,“有才无德”村干部的出现,正是这种困境的表现。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乡镇不再需要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反过来,村干部报酬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负担,同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政策执行的压力已经大为降低,乡镇甚至可以脱离村干部单独执行或依赖司法系统执行。这样,之前存在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有了被打破的可能性。乡镇在村级治理中可以不再依赖混混和狠人、不再需要对乡村混混保持“战略性容忍”,因此可以按照村民自治原则,将那些“有才无德”村干部选掉。遗憾的是,政策部门缺乏对那些“有才无德”村干部进行清理的动力,相反,却忙于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合村并组,期待“官退民进”。实践已经表明,“官退”之后,往往不是“民进”,而是乡村混混与邪教组织的跟进。在两湖平原的许多村庄,混混进一步弥散[11],而且,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不可能再借拒缴税费与政府谈判,基层政府更加倾向于不顾及农民的需求和偏好[12]。因此,“有才无德”村干部并没有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有才无德”村干部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存在局部弱化。十年前强世功、赵晓力等人对“炕上开庭”的微观个案的研究早就揭示,基层政权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权力运作上必须借助作为支点或导管的村支书,运用人情、面子、“一打一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自我技术等种种行动策略和权力技术[13-14]。苏力则在宏观上论述了国家权力为了取得对基层社会的局部性支配地位,而采取“送法下乡”这种权力运作方式[15]。这些论述说明,在使乡村社会得到有效的治理上,国家权力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表明当前的基层国家权力与作为其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种种不平衡。在这种力不从心和不平衡的状况下,国家权力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讲究策略和正确使用权力技术。当前,“有才无德”村干部的存在,可以从这个谱系中得到理解,它所反映的不过是国家权力不足状况的继续和不断“深化”。
[1] 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J].青年研究,2010(2).
[2] 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M]∥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3] 孙远东.论乡村地痞对农村基层行政的影响[J].开放时代.1999(3).
[4] 肖业炎,张艳.农村地痞恶势力类型、危害及其治理[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5] 于建嵘.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J].战略与管理,2003(5).
[6] 贺雪峰.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和进路[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7] 贺雪峰.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M]∥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8] 吕德文.在“钉子户”与“特困户”之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 钟瑞庆.农民负担问题中所体现的冲突解决方式[J].中外法学,2001(5).
[1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66-68.
[11] 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12]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2007(2).
[13] 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M]∥王铭铭,王斯福.乡村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88-520.
[14] 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M]∥王铭铭,王斯福.乡村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20-541.
[15] 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