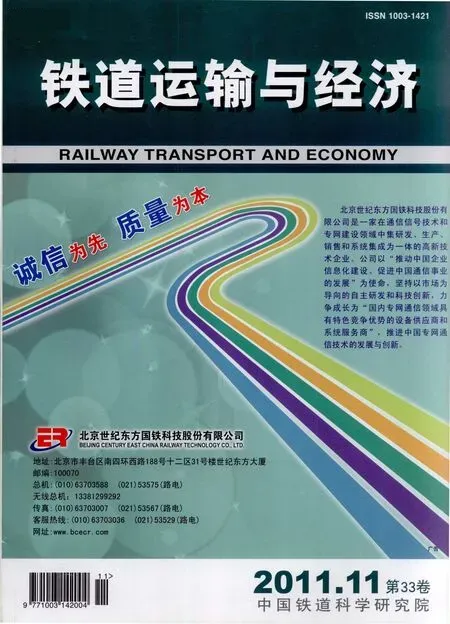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改进构想
左春玲
(北京物资学院 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北京 101149)
集体动劳争动议争中的议劳是方劳当动事争人议通的常一为种规重定要的表多现数形人式 。(集或体为劳某一团体),而且拥有共同争议内容和争议请求。当劳方争议主体与企业管理者 (或雇主组织) 因劳动权益与义务,或者集体合同的签订或履行等问题而产生争议,则两争议主体之间的争议即为集体劳动争议。近年来,随着经营创新工作的推进,铁路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铁路站段合并引发的集体合同主体变更等。我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后,铁路职工劳权意识日益增强,如因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权益受损而提请劳动仲裁等,铁路企业产生越来越多的集体劳动争议风险。由于集体争议涉及面广,处理不当将影响铁路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建立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置机制是铁路系统劳动管理者应着手研究的重要问题。
1 集体劳动争议中调解组织的作用
在实践中,调解被认为是处置集体劳动争议的最经济、便捷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与仲裁或诉讼相比,劳动争议调解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优越性:尽量不破坏争议双方的合作关系,以更为灵活的机制安排给予当事人最大的自主选择的自由,使争议主体最大限度地主张各自的合法请求;在仲裁、诉讼之前,解决、过滤掉大量的集体争议,降低社会成本,避免双方当事人的尖锐对立。
1.1 调解组织必须满足的条件
对集体劳动争议而言,调解一般是在发生争议双方进行团体交涉失败后,请求调解组织 (第三方) 出面进行斡旋或调解,最终促成争议双方达成和解的一种争议处理办法。从理论上,调解组织在劝说、引导和寻找新的争议解决路径等方面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
(1)调解组织应该具有中立性。调解组织的介入会在实质上改变集体劳动争议的博弈格局,正是这种改变有可能为争议的解决寻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调解组织不中立,如与其中一方当事人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则其在改善博弈格局、促进形成新的均衡方面很难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还会催动调解破裂。
(2)调解组织应该能够被集体争议双方所信任。集体争议双方之所以延请调解组织介入纠纷解决,就在于都相信调解组织对纠纷有足够权威的认识和判断力,能够公正地提出解决意见。
(3)调解组织中具体负责调解的人员应该具备丰富的调解技能。要达到预期的调解目的,调解人员需要对争议双方的心思路径、潜在要求和谈判情势等进行敏锐而准确的把握;需要对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和操作惯例等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还需要具备突破纠结局面,创新性地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如果说调解组织的中立和得到信任是实施调解的前提,那么,丰富的调解技能则是保证调解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1.2 提升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效率的途径
提升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效率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选择适格的调解组织;建立促进争议双方妥协的压力或诱导机制[1]。
(1)适格调解组织的选择。根据国际经验,调解组织大致有以下两类。①由当事人通过协议设立或由民间团体主导建立。这类调解组织通常负责处理争议双方在自愿原则下一致产生的调解请求。②由政府主导设立。这类调解组织主要处置国家规定需要进行强制调解的那些集体劳动争议。
(2)建立促进妥协的压力或诱导机制。调解组织要想在集体争议双方之间实施其调解策略,除了具有高超的调解技巧之外,还必须要获得争议双方的实质性配合。这种配合,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妥协。对于争议双方,妥协意味着要通过某种放弃来获得某种对己有利的利益或承诺。对于放弃什么、寻求什么,需要通过压力或诱导机制进行选择。例如,对于侵害劳动者劳动安全的集体争议,如果法律规定了更严格、更容易量化处理的损害赔偿方法;或者显著增大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则争议双方、至少是雇主一方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将会提高,调解组织实施调解策略的运作空间也会增大。
2 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铁路企业一般实施纵向金字塔式的管理,企业主体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一旦发生比较重大的集体劳动争议事件,铁路企业的正常运行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集体合同规定》针对国家是否要对公益性企业重大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强制调解,以及在强制调解程序实施过程中,争议双方能否启动其他争议行动等缺乏明确规定。劳动争议处置机制期望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调解组织在防范和化解集体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并尽可能减少集体争议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2.1 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概况
我国铁路企业以铁路局为单位相继制定了企业内部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如《哈尔滨铁路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暂行办法》等,陆续组建了三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即在铁路局设立劳动争议调解指导委员会,成员由铁路局行政部门、工会、职工代表等组成,主任多由铁路局工会副主席担任,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培训工作。原各铁路分局级单位建立一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各基层站段建立二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005年铁路分局机构撤销后,原来二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由铁路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二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成员均由所属单位的行政部门、工会和职工代表组成,办公机构设在同级工会,具体负责劳动争议纠纷的预防、调解和处理工作。
近年来,随着铁路系统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生产力布局调整、劳动组织优化整合、新线集中建设及新装备的大量投用,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率有所上升。为了稳定劳动关系,贯彻“着重调解,及时处理”和“预防为主、基础为主、调解为主”的争议处置思想,各铁路局纷纷着手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例如,成都铁路局 2010 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完善局属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通知》、《关于公布路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成名单及工作制度的通知》等文件;专门召开成都铁路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座谈会,宣讲文件,进行培训,交流经验,部署劳动争议协商调解工作。因此,以铁路局为单位的调解制度在形式上得到了强化[2]。
2.2 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调解制度在形式上的强化并没有相应地带来调解效率的提高。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比例,以及调解成功的比例仍然徘徊在 10% 左右。从理论上分析,影响调解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调解机制仍然存在明显缺陷。
(1)按照既有法律和制度,铁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运行成本由企业承担,调解组织由于对企业存在经济依附性,从而不再具有“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此外,构成铁路企业争议调解组织的三方人员,无论行政管理人员、工会人员还是职工代表,均来自于本企业内部;这种人员遴选机制也使调解组织无法形成超然、中立、公正的地位,难以获得调解所需要的权威。
(2)既有法律和制度易使铁路企业各级工会在进行劳动争议调解时陷入角色模糊甚至角色冲突的境地。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工会是劳动者劳权意志的合法代表,因此其不应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介入集体劳动争议处置;另一方面,铁路企业工会同时接受党委领导,在建制上被统一纳入到行政系列。由于铁路局辖内各级工会与企业管理方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因此,也不具备成为中立组织的条件。
(3)铁路企业基层调解组织的能力条件难以满足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集体劳动争议本身往往都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争议所涉及的制度规范也十分庞杂。负责具体调解工作的人员需要能够正确、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分析这些复杂问题,还要有能力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调解意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成争议双方和解。在现实中,我国铁路企业调解组织中的调解人员往往难以承担这种高度专业性的活动,他们大多只是对相关制度有所了解,在理解上还难以做到准确和透彻。
(4)既有法律和制度缺乏促进推动或诱导争议双方妥协的机制安排。从经验来看,影响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双方妥协倾向的因素主要是当事人在纠纷中的制度性、非制度性手段的有效性。通常,劳方争议主体在就业机会、采取集体争议行动的成本等方面会面临较大压力,故而其妥协倾向相对显著;而企业管理方在应对集体争议的手段方面存在着明显优势,因此其妥协倾向相对较弱。我国在法律规制方面,没有对这种权势失衡给予足够的平衡,这使得争议双方尤其是职工一方不愿选择调解途径来解决争议;即使申请了调解,调解组织施行策略的空间也比较狭窄。
3 发达国家的集体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及启示
集体争议得到及时化解或调解是发达国家构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时达成的共识,其调解制度的重点是通过制度来构造适格、称职的调解人 (第三方)[3]。
3.1 部分国家的集体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情况
(1)美国。在美国集体劳动争议经常发生,联邦政府和许多州为此专门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公共调解机构,其中美国联邦调解调停局是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设立了国家劳资小组,组员12人,由总统任命,有6人是来自资方的具备足够名望的人选,其余6人则来自劳方,也从具备足够名望的人中选出,组员任期3年。对于具体的集体争议调解者,美国法律规定,神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名人或其他适格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担当调解人。美国法律规定,只要调解调停局认为该项争议可能对产业运行带来严重威胁,调解调停局可以主动或应争议中的一方或多方的请求,对争议进行干预。如果经过一段时期,调解难以奏效,调解调停局就必须敦促争议双方自愿寻找别的办法来解决争议而不采取罢工、闭厂等压力行动。当调解陷入困境时,还可以采用“实情调查”程序来突破困局。“实情调查”是依靠外来者调查争议事实并提出报告,通过提高争议的公开性迫使争议双方达成妥协。
(2)英国。在英国负责集体劳动争议调解的机构是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 (ACAS)。该委员会是政府出资建立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由贸工部资助。ACAS 由一名主席领导,主席人选可以来自社会名流、大学教授或律师等,其管理机构是三方委员会,集体争议的调解申请可由集体争议双方 (即工会或雇主方) 分别或共同提出,ACAS 也可以主动向争议双方提出调解。ACAS 主持的调解遵循当事人一致性程序,是一个完全自愿的程序,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终止调解。这种调解只要是双方有调解意愿即可进行,并且不要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3)日本。在日本负责集体劳动争议调解的机构是劳动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在遇到下述情况之一时,将介入调停。①当争议双方向劳动委员会提出调停申请时;②当争议双方或一方依据“集体协议”的规定向劳动委员会提出调停申请时;③当事件涉及公益事业,争议的一方向劳动委员会提出调停申请时;④当事件涉及公益事业,或者因事件规模较大或涉及特殊性事业而对公众利益造成明显危害,劳动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向劳动委员会提出调停申请时。调停结束,劳资双方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调停意见。调停意见对当事人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4]。
(4)德国。在德国集体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两类。其中,权利争议是指一方当事人不按集体合同规定履行义务,而使对方合法权益受到侵损而产生的争议;利益争议是指争议双方为确定集体合同项下的某种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或变更原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引起的争议。德国对利益争议采取自愿调解原则,主要依据调解协定来规制调解程序。通常调解协定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出调解申请,或者集体谈判破裂时自动进入调解处理程序。调解机构由雇主团体与工会派遣同样数量的代表及中立的主席组成,主席可以是法官,也可以由政府的高级官员、大学教授、医生或其他知名人士来担任。调解委员会所作的调解方案,除非当事人双方同意,否则不具拘束力。如果当事人双方一旦接受,则该调解方案与集体协议具有同样效力。
3.2 启示
(1)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中立调解组织,如美国、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国家级的独立的争议调解组织。
(2)调解组织的调解人员通常由技能丰富、具有权威的中立人士担任,而且其人选的甄选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3)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对公益事业发生的集体争议进行强制性调解。强制调解机制一般要求当事人依法履行参与调解活动、进入调解程序的义务,但不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或处理方案。强制调解机构可由政府设立,或者由法律授权的机构担当。
(4)这些国家在调解程序、重大争议调解的特殊安排、实情调查和预防性调解等调解机制方面也具有比较成功的经验。
4 铁路企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改进构想
(1)建立中立的行业级调解组织。在理论上,调解组织的中立性是保障其获得信任和实施公正、有效调解的前提。在我国现有制度条件下,铁路系统完全有必要成立行业级调解组织。行业级调解组织能够不受劳动关系当事人利益的束缚,居于中立地位,从而能够保障其调解效率。铁路行业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可按三方原则组建,即由铁路总工会、铁道部和第三方代表共同组成,主席由铁路总工会派出的首席代表担任,第三方代表可由铁路法院法官、铁路和高校或人保部门等相关机构的专家等兼任。
(2)调解制度中增加强制调解程序。铁路企业是具有公益属性的企业,为了减少发生集体劳动争议给社会公众带来权益损害,有必要在现有铁路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中增加强制调解程序。建议从两个层面对强制调解进行规制。①规定铁路企业一旦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当团体交涉无效后,应当首先进入调解程序。为了有效推进基层调解工作,各级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可以请求行业级调解组织派出调解指导员对工作进行指导。②规定一旦铁路系统内部发生涉及公众利益或规模较大的集体劳动争议,铁路系统行业级争议调解组织应主动介入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争议当事人不得采取任何压力行动。
(3)调解制度中增加促进妥协的压力或诱导机制设计。压力或诱导机制可按两个路径进行设计。①向妥协倾向小的一方施压。可以通过铁路内部规章要求企业管理方如果作出不利于职工的决定而引起集体争议,必须通过其人力资源部给职工以充分的解释,包括给出事实与规范依据,听取职工意见。此外,国家还应适当调整劳动争议处置的相关法律,如增加仲裁或诉讼的时效;加大对侵权的惩处力度等,以从铁路企业外部来推动调解。②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争议当事人自愿通过调解途径寻求争议的处置。这主要是对调解第三方进行规制改良,可鼓励争议当事人共同选择其所信任的中立机构担任第三方,并组织和主持调解活动;也可鼓励当事人各方委托比较专业的、公正的代理人,如律师、社会工作者、法律顾问等,共同组成第三方等。
[1]陈步雷. 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构造分析与改进构想[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8):7-17.
[2]韩 崴. 哈尔滨铁路局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作情况的调查与建议[EB/OL]. (2008-05-06). http://bbs.chinacourt.org.
[3]潘泰萍. 集体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 (2):156-158.
[4]韩淑华. 集体合同争议解决机制问题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5):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