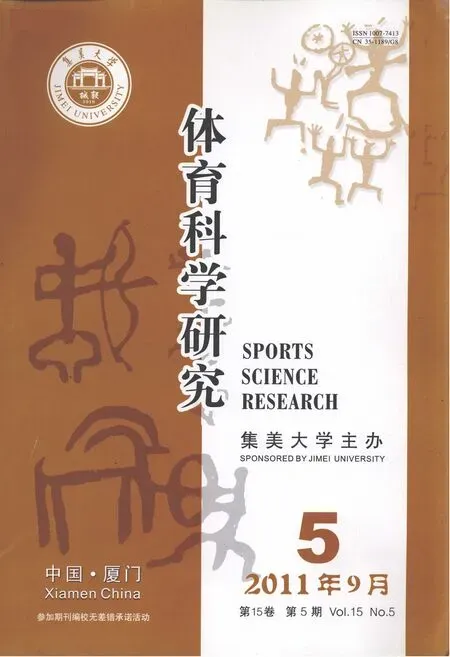论中国社区体育的发展——基于批判的视野
王志威
(华南农业大学体育部,广东广州 510642)
论中国社区体育的发展
——基于批判的视野
王志威
(华南农业大学体育部,广东广州 510642)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社区民众在中国体育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自己享有体育锻炼的环境和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认识不深,政府定位不准;针对特殊群体的体育需求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缺乏完善的管理和维护机制;社区体育专业化组织程度不高,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社区体育;体育管理;体育设施;体育软实力
社区体育是现代生活品质基本保障之一,其具体功能体现在减压、锻炼身体、促进家人、邻里、朋友等人际之间的交流,提高学生学习的专注力、毅力,还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尤其是能够减少青少年犯罪等。而金字塔式“金牌主义”的体育发展体制,在鲜花、掌声之后还有运动员的伤病、就业等问题。
自建国以来,中国金字塔式的体育体制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旧有的体育体制,在提升国家声望,提高国际影响力上,效果甚佳。但是,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社区体育逐渐成为必备的生活条件之一,现有的体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社区体育的发展,是民之所需、民之所求、民之所爱。体育政策的制定就是圈定体育发展与人的关系,而中西体育政策偏重不一,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政策偏重于公民对公共体育的权益分享,中国则偏重于体育对国家及民族的整体影响,相对忽视了体育更多的社会功能。从休闲的角度,成思危(2002)提到:“我们的经济和人民的休闲意识已经有了基础,构成了一个在理论、实践、政策、宏观调控等层面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建议政府未雨绸缪,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循序渐进地推进这方面工作的开展”[1]。
社区体育可以承载诸多的社会功能,学界和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深度认识以及合理地解决问题。本文以批判的视角,从政府调控和社区自觉两个层面,寻找社区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对社区体育的认识不足,定位不准
1.1 公众和政府对社区体育的认识不深
中国历来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穿短打衣服,会被认为是下层体力劳动者粗鲁的表现,执笔的文人一般都很少挽袖。自清军入关以后,曾又数度禁止民间的习武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结社行为一直受到严格管束,某些体育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体现。即使有为数不多的体育活动,也是在工会或者集体的组织下进行,例如,风靡一时的广播操及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现在基本悄无声息。进入市场经济后,原有社区体育活动组织体系被打破,公众对自我体育活动的意识逐渐加强。但是,中国公众对体育的认识时间很短,体会不多,整体认识上还是不够深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区体育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还不如英国100年前的发展水平。公众对社区体育的认识不深,且中国人多喜欢,例如看电视、打麻将、聚餐、去歌厅和逛酒吧等,而对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中小城市,这种现象显得更为普遍。根据《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对没有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的障碍原因分析表明,60%为缺乏健身意识。
事实上,大城市的部分社区已经具备了体育活动的设施条件,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在“非典”时期,通过政府临时的强力宣传,部分城市居民才开始认识到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这些事实都表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意识到体育的各种功效,没把参与日常体育活动当成习惯。另外,由于物质条件限制的因素,中国尚未全部进入小康社会,还有很多人在温饱边缘徘徊,居民主要还是忙于生计,无心情也无基本的条件去进行体育活动。
从政府层面,自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要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都具有“一阵风”的行政风格,风后一般无人过问,缺乏长效的运营体系,甚至有的地方只在墙上刷口号,却无实际的建设行动。在发展理念的认识上,我们存在一定的误解,“我国休闲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休闲文化,而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体现是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这也是我国休闲文化的基本内涵,也是我国休闲文化的本质[2]”,“休闲行为可以多种多样,但指导休闲行为的精神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而在现实中,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恰恰缺乏科学性、大众性和民族性。此外,上述观点认为“休闲”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休闲是否有“白猫”、“黑猫”之分,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作为一种增强国民体质、提高国民素质、舒缓国民压力的工具,体育应该超越各种主义、哲学类别的限制。社区体育是属于一个形而下的概念,需要实在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它的发展。
1.2 体育的发展定位不准,缺乏民族特色
二战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主义两大阵营,开始在体育竞技上较量。20世纪60年代,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将体育运动工作重心放在少数具有特色的运动项目上,重点培养能在国际赛事中拿奖牌的竞技型人才,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国际影响力以及提升国家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有些国家逐渐主动退出体育竞技上的较量,转而集中在经济、科技上的竞争。在这方面,中国不仅不退,反而加大了经费的投入。直到现在,这一政策变化不大,各级政府仍将不少的经费用于培养专业运动员,体育发展定位尚未真正面向大众,缺乏对社区体育事业的整体关注(可能与政绩评估标准有关,奖牌数量是很好评估的),这是导致社区体育事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之一。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体育的政治工具性才开始减弱。中国社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时间上明显晚于西方。随着政府体育部门的权力逐渐分化后,政府扮演起组织者、协调者、管理者的角色。竞技体育由政府直接管理,而群众体育由社会行业负责。但是,从功能上看,将体育视为国内政治工具仍然是主流观点,社区体育的发展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因此,官方对体育发展的定位也制约着我国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被边缘化。民族传统体育是文化标志,也是民族的一个标识,是维持世界文化多样性最基本的保障条件。我们经常讲,发展体育要中西结合。但实际上,中国现有的体育活动基本上是舶来品,基本上丧失了民族特色。即现在流行的许多体育活动,基本上都是源于英国及欧洲大陆。这说明,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原创精神以及对传统民族体育的传承与发扬远远不够。所以,在发展社区体育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同时,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冲击之下,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需要政府的支持。根据中国社会循序渐进的改革特点,目前,最具操作性的发展定位就是维持“金牌主义”和“社区主义”之间的平衡发展。
2 缺乏完善的管理和维护机制
2.1 官方管理机构设置存在缺陷
官方部门的横向合作机制有待改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逐渐关注社会协调与人文的发展,这给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背景。为了推动社区体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政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政府应该开始“自身革命”,政府的职能应由建设型转为服务型,首先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政府部门之间有更多的横向协作。在发达国家,社区体育的发展涉及多个政府行政部门。而我国行政体系权责划分多属于上下垂直型,数十年未变,横向部门间相互独立,甚至行政事务相互推诿,社区体育事业缺乏专门的管理和协调体系。社区体育的发展涉及到艺术、旅游、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它们分别归体育局、文化管理部门、旅游部门、市政部门等管理,但这些部门间的横向权责协调体系有待优化。这是造成我国社区体育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不能满足居民合理体育活动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在体育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置的改革上,往往力度不足,措施欠佳,所以社区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
体育局主管群体工作的部门、街道办、居委等,往往难以顾及繁杂的社区体育组织与管理。社区自治社团的发展,又受到种种限制,尤其是对法人资格的限定,严格意义上说,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体育的组织与管理,还得依赖于官方与非营利性体育组织。我国社区体育的现状,与英国战后恢复经济时的情况相似。当时,社区体育既有英国政府的强权干预,又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虽然,英国的体育管理机构设置模式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行政设置特点,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设置专门的儿童游乐、体育志愿者组织等评估机构。
2.2 社区体育设施逐年递增仍显不足、日常维护缺乏
1995年,全国共有各类体育活动场馆61.6万个,共7.8亿m2,人均0.65 m2。其中,仅44.1%整体开放,21.3%部分开放,4.6%没有对外开放。场地的定址、器材、灯光、通风、换气、厕所、停车等,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影响居民体育休闲活动的进行[4]。以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圳为例[5],它仅有体育场馆2 791个,公共体育场馆77个,公共体育场馆的总面积为628 095.02 m2。作为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没达到城乡建设部及国家体委(1986)体计基字559号文件规定的“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公共体育场馆316.8~484 m2/千人”的指标,这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
1996—1999年间,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政府,先后为“全民健身”工程投入近245亿元,花在公园、广场、学校和街道等建设方面,新建或修复的体育场地、器材总数达11 089套,其中,45%供群众无偿使用,39.06%象征性收费,6.25%按市场价收费。此外,《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的体育健身场所,大都是近三四年才开业的。这些健身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体育活动的开展。但是,也应看到,在社区体育资金投入和运动场馆建设、器械购置等方面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我国人均体育用地面积为0.6 m2左右,发达国家超过2 m2,而美国更是达到14 m2。
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共有各类体育活动场地85万余个,场地面积达13.3亿m2,历年累计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1 914.5亿元。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148.15元。虽然与1995年底数据相比,各项数据有了较大的提升,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共增加了11.8亿m2,增长110.28%,场地面积共增加了5.5亿m2,增长70.51%。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38 m2,增长58.46%,年平均增长率为5.9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增加了117.09元。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了1.58个,增长31.6%。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不均衡性,有些地方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社区体育发展长期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的状态。大多数中小城市的社区体育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这都与各级政府社区体育的建设意识不强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社区体育还缺乏场地的日常维护和器械的检修保障,使用体育器材时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材的报废率上,中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一方面造成资金投入的压力,另一方面造成资源浪费。在体育设施的日常维护上,英国节约改造模式值得中国借鉴。英国人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但受到多变天气的影响,有时只能进行室内运动。因此,英国室内体育条件越来越好,设施越来越多,设施功能也随之增多,同时,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室内体育设施的维护。通过观察、访问,笔者了解到,在英国,很多室内游泳池,尤其是学校游泳池,是在室外游泳池(有的是在一战时期建立的)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这既可以节省资源,又可以减少财政支出。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见。
2.3 特殊人群的体育设施建设缺位
老龄化是21世纪初我国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人口老龄化给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1997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占总人口的7%,达8 700万。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大,2000—202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期间,老年人口将从1.27亿增加到2.29亿,年递增率为3.0%,即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从9.81%升到15.53%[6]。对北京老人进行调查,发现84.5%的人每天外出活动1~2次,11%的老人每天外出3次以上,在外出活动时间上,23.7%在1小时之内,62.9%达1到3小时。另外,对上海1 446位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发现,66.7%的老人足不出户,42.2%仅在家门口附近活动[7]。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必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社区体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针对老年人的活动场地、体育设施的设置上,我国现行的社区体育条件,无法满足老年人锻炼的需求。
此外,在针对残疾人公共活动的软、硬件投入方面,我国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以广州为例,虽经亚运会的改造,但是很多道路的盲道设置还是不达标,公共场所的轮椅通道不多,公共厕所也缺乏残疾人的专用位等。对残疾人来说,如果这些最基本的公共设施都无法得到满足,那么他们锻炼的体育设施就更不到位了。
3 软实力发展不足,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状况调查》显示,在我国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只有33.3%的人接受过体育锻炼方面的指导,其中接受体育教师(教练员)指导的人数比例最多,为15.3%,其次为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其他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所占比例在5%左右。还有2.7%的人依照参考资料进行体育锻炼。
我国社区体育软实力的发展,似乎与时代脱节,具体表现为,缺乏相应的运营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目前,全国共有职业社会指导员8 000余人,平均每百万人才6名。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各种休闲教育的理论都提到,政府应将休闲理念与具体休闲活动纳入学校课程当中。然而,我国体育休闲的教育环节相当薄弱,无论是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缺乏相应的体育休闲课程,只有极少数院校有这类课程。
3.1 社区体育事业缺乏深度教育理论的指导
在社区体育的发展上,英、美两国走在世界前列,研究也较为透彻。美国休闲教育的发展推动力,来源于社会的休闲咨询机构和社会团体(公园与娱乐协会、美国健康协会、体育和休闲协会等)[8]。在体育教育的理论上,早在1918年,全美教育协会就在《重建中等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到有价值地利用休闲时间,从休闲生活中获得身心之休息和愉悦,并充实精神生活来发展人格。中国的学校体制过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在人口的压力下,升学竞争异常激烈,社会现实情况与个体内在需求发生冲突。于是,青少年往往是以牺牲个人内在需求为代价,以求适应社会现实。
美国休闲教育委员会,在编写休闲教育资料时,曾将曼蒂的《休闲教育的范围与程序》作为休闲教育实施工作的标准模式。在体育教育的实践上,美国充分发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袋鼠之囊》是美国学校休闲教育最详细的指导手册,由教师、公园工作者、志愿者、宗教人士、娱乐工作者编写。而在社区体育事业上,我国各大高校缺乏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和理论探讨的专家队伍。总而言之,在社区体育教育研究上,我国起步较晚,对于该事业的管理问题研究缺乏系统、科学、规范、成熟的论证。
我国近几年才开始对休闲业进行研究,而研究社区体育管理和运营的人才更少。体育活动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是休闲教育的重要实施途径之一。休闲、体育运动和教育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未来高校体育教育朝人性化方向发展的潮流[9]。各大体育院校主要关注竞技体育选手的培养,而缺乏对社区体育事业管理和运营方面的研究。课程设置也主要集中在学生的体能和技能训练上。另外,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相关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导致其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市场脱节,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3.2 政府缺乏行业管理人才和决策人才
我国体育事业的人才,主要是以退役运动员、转业军人、体育院系应届毕业生为主,缺乏社会休闲的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引入机制缺乏科学性:退役运动员过于关注竞技类体育事业的发展,忽视体育休闲事业的发展;转业军人过渡到体育休闲事业,属于半路出家,缺少该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体育院校毕业生直接上岗,没有实践经验。由此可见,这一选拔人才的方案,不利于社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这种人才机制下,不同的领导者有着不同的风格,对社区体育的关注程度不同,这导致社区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稳定性的连贯性。
3.3 市场缺乏高水平的商业运营人才
目前,在社区体育事业发展上,我国极其缺乏高水平的商业运营人才。以“第二届北京国际体育与休闲设施及用品博览会”为例,在体育休闲市场日益扩大的今天,这样的展会却办砸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能掌握全局的专业规划人才和商业运营人才,尤其是具有休闲与体育知识的专业人才。在这个博览会上,一家公司的广告使用北京申奥会徽和五环图案,违反《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中的规定。可见,高素质的体育休闲商业运营人才极其稀少。法制社会下的市场经济,对体育的运营、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们不仅要研发体育产品,而且要对产品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文化内涵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如今,我国这类人才紧缺,导致社区体育产品及服务较单一,且缺乏创新性和实用性,国内社区市场尚未铺开,更加难以打入国外社区市场。
4 结束语
根据英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经验,当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时,社区体育的发展就必须引起当地地方政府的重视,当超过全国7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时,这时,中央政府就应该出台系统的政策与法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社区进程的高峰期,政府应未雨绸缪,预留社区体育的发展空间。
社区体育与社会进步的统一,是体现社区体育所蕴涵的人文价值理念与科技所奉行的科学价值理念的统一。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国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国际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体育事业的发展再现分化,应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目标之一[10]。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区体育是在政府统一组织、规划、领导和管理下发展起来的,非营利性体育组织体系尚未建立,社会资本的整合作用还未发挥出来,很难满足多层次的人文关怀需求和居民不同的体育诉求。但是,笔者乐观地认为,在未来20至50年,中国社区体育发展将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1]成思危.“2002年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的讲话稿[R].北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2002-10-15.
[2]毛冬宝.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及其文化建设[D].长沙:中南大学政治学院,2001:37.
[3]施树英.马克思主义休闲观与我国休闲文化建设[D].长沙:中南大学政治学院,2003:26.
[4]成雄.发展休闲娱乐体育问题探讨[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8(4):109-110.
[5]王菁.深圳公共体育场馆的现状及多功能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3):1-3.
[6]张建萍.我国女性休闲生活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形态[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2):46-50.
[7]孙樱.我国城市老年人休闲行为初探[J].城市问题,2000(2):29-30.
[8]张洁.美国闲暇教育的发展及启示[D].石家庄: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00.
[9]赵龙.大学生运动体闲阻碍因素的分析[D].成都:四川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2003:50.
[10]肖进勇.现阶段我国体育行政部门管理手段探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6):28-29.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in China:a Critique Perspective
WANG Zhi-wei
(P.E depart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Through the study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this essa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tatus quo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sports in China.It points out that while i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sports,China doesn't satisfy the public's demand for sports or give them enough rights in this regard.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public awareness,the government's incorrect positioning,the lack of a mechanism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stenance of community sports for special grou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the under-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and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community sports;sports management;sports equipment;sports soft power
G 80-0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7-7413(2011)05-0006-05
2011-06-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TY018)
王志威(1973—),男,湖南湘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责任编辑 江国平]
——示范区建设中的云南体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