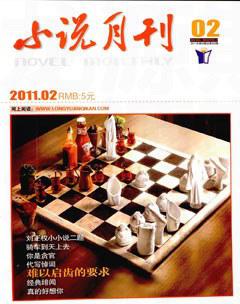银针刘一手
余显斌
刘一手是我连襟,村长,兼医生。真名,我不说了,凡小镇人,无所不知,算得小名人。至于刘一手,是自封的,意谓自己一手银针,无病不治。
这话,把牛都吹死了。
我喊;“大水哥!”他忙摇手,更正:“喊一手哥,或者刘医生。”那神态,让我很不爽。
他会中医,至于西药,一窍不通。
我有虫牙,常痛,一痛就捂住腮帮子,老娘们儿一般,稀稀溜溜,屁滚尿流地赶去让他治。
他要动银针,露一手。我忙挡住,喊爷啊,别用银针,痛,还慢。
无奈,他就用西药,一边找药,一边问:“你说用啥药好?”
我痛,本来鬼火乱窜,让他一句话,更是火上浇油,道:“老鼠药。”
他一愣,问:“老鼠药,没听说治牙痛啊。”很谦虚的样子,向我请教。
我白他一眼,道:“老鼠药包治百病啊,一副下去,什么痛也没有了。”说完“哧”一声笑了。他指着我,呵呵地笑,说:“该痛,该痛。”说完,捡药,全是泻药。回去,我一晚上上了八次茅厕,后来,干脆蹲在那儿,不动窝儿,免得来回跑;再说,也跑不了了。
他听到电话赶来,早准备了“泻立停”。以他说法,泻药下火,然后治泻,连环治疗,独门奇效。
“破医生!”我有气无力地说。
他很不满,道:“别胡说,喊刘一手。”
我没喊刘一手,喊刘阎王。他忙跑过来,捂住我的嘴,左右望望,好像有人偷听似的,道:“祖宗,你想砸我饭碗啊?”然后告诫我,这“刘阎王”以后千万别喊了,不然,我们的关系一刀两断。说完,走了,去了他的诊所。
这家伙,我不服他医术,服他胆大,把诊所开在十字路口,匾额大书:神针渡世。旁边对联,上联道:扁鹊再世犹自俯首下拜;下联曰:华佗重生也得自叹不如。
对联是自己拟的,堂而皇之,毫不谦虚。
在他开诊所第十年,出了件风流韵事。
整天,他拿银针,屁颠屁颠过了河对岸,给蓝英扎银针。蓝英已瘫了一年了,能扎得好?扎得好,蓝英的男人白春能扔了她,独自跑了吗?
我说:“大水哥,该不是旧情复燃吧?”
年轻时,刘一手和蓝英是恋人,后来,蓝英相中了白春,扔了刘一手,恓惶得刘一手站在镇河边上,三天三夜,准备跳河,不是我妻姐英雄救美,他小子已去了龙宫,做了龙王驸马了。
他听了,四边望望,忙摇头道:“别胡说,我是什么心肠的人,你不知道?”
“一肚花花肠子的人!”我指着他,“被梅子姐晓得,你完了。”梅子,就是我妻姐。
“我这是积德行善。”他说,忙忙走了。
他积德行善的事,终于被妻姐知道,当场揪着耳朵,扯回来。亲戚朋友全被请去,三堂会审。
据妻姐说,淫妇光溜溜睡在床上,只穿一条裤衩。
“给扎针!”他争辩。
“扎针?还扒光衣服?”妻子敲边鼓,帮忙审问。
“找穴位。”他求助地望望我。我转了头,对于陈世美,不落井下石,已算客气,我绝不帮忙。
妻姐提出离婚。妻子马上阻挡,一离,恰好入了这对狗男女的心愿。
大家一致表决:让刘一手写份保证书,以观后效。
刘一手没推辞,铺开纸,三下五除二,交上检讨。
妻姐说:“这没良心的蓄谋已久,连写保证书都准备好了。”说得他低头弯腰,无言以对。
当然,为了加大处罚力度,妻姐还加一条,分房睡觉:自己住楼上,他住楼下,以观后效,如果毛病不改,分家散伙也很顺畅。
他低头,仍无言。
一个暴雨的夜晚,屋后涨了水,妻姐醒了,忙下楼喊他,喊不应,打开门,里面什么人也没有,刘一手跑了。妻姐气得直跳,电话里告诉妻子,坚决离婚。
可刘一手好像知道这事似的,坚决不闪面。
一直到第二天,有人在下游见到刘一手,卡在乱石间,手上却紧紧捏着一筒银针。人,早已死了。
刘一手下葬时,蓝英来了,架着拐,能走了,伏在坟上,大哭。
原来和妻姐分居后,刘一手仍每夜过河,给蓝英扎针。那夜,扎完针,就往回赶,外面大雨倾盆,水如牛吼。
蓝英留他在那边住,说心里没鬼,怕啥。
他摇摇头,说怕梅子知道了伤心。说完,走了。谁知一走,再没人影。
妻姐听了,一声哭晕了过去。
责任编辑:丁丽 margury073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