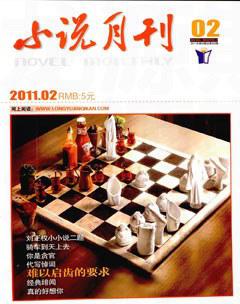北京啊北京
叶萍
礼堂后面有一大片空地,我们经常在空地上跳皮筋,踢沙包,歘石子儿,在黑夜里捉迷藏,我们像猴子一样窜高蹦低,像狗一样嗅着鼻子闻谁家的菜饭香,喇叭里整天放着李双江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北京啊北京》。
那时候,英子就站在院门口,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看我们玩,一边听李双江的歌声。
英子,玩吗?我们带你玩。我们几近讨好地引诱着英子。英子摇摇头,闪进院子里。英子从不和男孩子玩,也不和女孩子玩。
好几次,我趴在英子家的院门往里瞅,我不知道英子每天在家干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瞅见。英子家的院门仿佛铜浇铁铸似的。只是有一次,我听到英子妈说,英子呀,你可得好好学习,别和他们一样,你将来是要到北京上大学的。英子妈嘴里的“他们”是我们,我们在英子妈眼里是一群没有出息的野孩子,英子妈从不拿正眼瞧我们。
英子爸在北京工作,是他们单位驻北京办事处的,很长时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走路的样子拽得像西哈努克亲王。
英子爸喜欢对英子妈居高临下的说话,英子妈就低眉顺眼地承应着。给我把那件衣服拿过来,英子妈颠颠地跑进屋里去取。有一次,正是午睡时间,英子妈极为锐利的声音划破了人们的梦境,我为你生儿育女,现在你不要我了?门都没有。
你就会生个孩子,还会干啥?
英子,好好学习,别像你妈一样没文化,将来到北京上大学。
屋子里吵成了一锅粥,英子一个人蹲在礼堂后面的空地上,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拿着小木棍碾蚂蚁,碾死一只又一只。后来,英子把口香糖拿在手里又捏又拽,拽得像面条一样长,把蚂蚁一只只黏在上面。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口香糖,是英子看我傻得冒泡的样子,告诉我,那是口香糖,从北京买的。
英子,你爸妈要离婚呢。
我显得有些大惊小怪的把这个消息告诉英子,英子头也不抬地说,离了才好。我比英子更担心她父母离婚是因为不知道离婚后英子会跟谁,也许会被她的爸爸带去北京?我被自己的遐想弄得很难过。喇叭里传来了李双江的歌声,一直没学会的歌曲《北京啊北京》突然一下子学会了。那深情缠绵有些忧伤的旋律怎么也忘不掉了,写作业的时候都无法停下来。
母亲看我写作业还哼歌,就耳提面命地训斥我,不好好学习,将来连个媳妇也娶不上。这似乎成了礼堂后面那些没文化的母亲们统一的训子模式。
娶不上就娶不上。没有了英子,娶媳妇有什么意义呢。
英子如愿考上了重点初中。
瞧瞧英子,就是有出息。大人小孩都夸英子,英子成了礼堂后面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和榜样。我就是攀着这样的动力和英子走进一个学校。
高中的学习越来越艰难,英子开始出现头疼的毛病,她一边掐着太阳穴一边把练习题做的小板凳一样高,天不亮就起来背英语和古文。
这种煎熬的日子终于随着黑色七月的到来结束了。高考那天,英子家的一株仙人掌开花了,白色的花瓣,又大又好看。英子妈说,这是好兆头,英子一定能考上北京。
分数出来的那天,英子不敢去学校,英子的头又开始疼起来,像气球一样要涨裂,英子焦灼不安地瞅着窗外。窗外的杨树叶子已经发黄,风一吹就落在地上。
中午,英子妈回来了,阴沉着脸,一屁股坐到床上,一句话也没说。
英子的头越来越疼,掐得出血了还疼。
我发现英子有些怪异是在一个早晨,我和她迎面相逢,喊她,她不理,眼睛望向地面,眼神却不知在哪里,她的嘴里依然嚼着口香糖。此后几次,英子都这样,眼睛看着你却不知道你是谁,眼神游移不定没有归宿。英子的父母也发现了英子的怪异,他们领她去医院,大夫说,是精神分裂症。
英子父母不相信英子会得那种病,他们领着她去北京最好的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一家工厂做了技术员。有一天,等班车的间隙,一个声音从我耳边飘过来:“英子,你慢点儿!”恍然间,我以为是我的英子,扭头,我看见一个妇人在喊她前面一个咧嘴傻笑的女孩,那女孩在追赶一只蝴蝶,风吹过来,吹起她的头发。
很多年后,因为官场失利,生活不得意。我一个人跑到了北京。漫步在花灯异彩的长安街上,莫名想起了英子,也不知道后来英子怎么样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拼命向着生活最精彩的地方奔跑,精疲力竭,以至于精神恍惚,神情浑浊,也一无所获。我们值吗?我不知道。
在北京的生活依然暗淡,经常头脑一片空白地走在街上,无所目的。忽然有一天,一个声音传过来:“英子,你慢点儿!”我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在追赶一个咧嘴傻笑的女人。不确定那就是英子和她妈妈,但我感觉英子可能现在就是在过这种无人能理解的幸福生活呢!
责任编辑:徐小红missxu5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