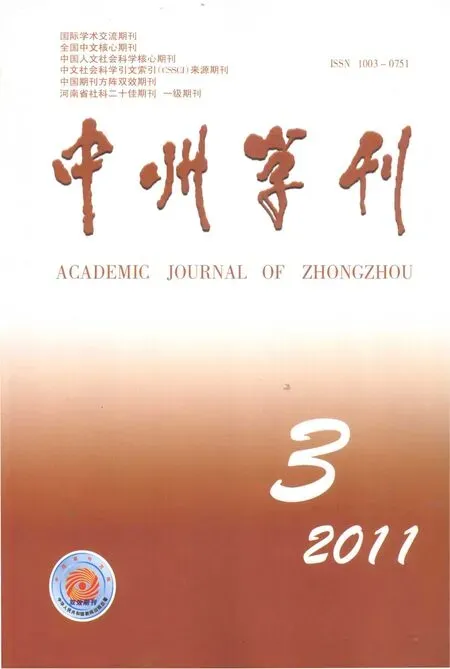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身份识别*——以朱自清为个案
张晓东
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身份识别*
——以朱自清为个案
张晓东
很多人是通过《背影》、《荷塘月色》来识别朱自清的,这样的视角过于狭隘,自然不能对朱自清有整体的把握。在朱自清的散文序列里,许多文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阿河》就是其中的一篇,它语义复杂,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特征。解读《阿河》可以一窥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奥秘,重启关于启蒙的话题,有助于对他们的身份进行重新识别。细读《阿河》文本,把它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进行有意味的对照,可以看出,对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认知要树立由简单的思想层面进入复杂的心灵层面的理念,特别要关注“深情”对“人”的重塑的极端重要性。
身份;复调;身体;启蒙;深情
中国现代知识者在自我与社会之间为自己寻找到的一个最佳角色,是担当大众社会的启蒙者。但总体上说,很少有人来质疑这种身份命名的合理性——现代中国像鲁迅那样思考问题的人太少了。重启关于现代中国启蒙的话题虽早已有人提出,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本文选取朱自清这样一个微观视角来提出自己的思考。很多人是通过《背影》、《荷塘月色》来识别朱自清的,这样过于狭隘的视角有很大局限,在朱自清的散文序列里,许多文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阿河》就是其中的一篇,它语义复杂,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特征。解读《阿河》可以一窥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奥秘,有助于对他们的身份进行重新识别。
一、一个虽隐犹显的世界
文学作品是有秩序的存在,秩序是创造者赋予它的。如果从创作动力学的角度去观察写作,其总是源于写作者意识深处的某种混沌的激情渴望,写作就是辨析、澄清,呈现这种激情的过程,感受者要为它去寻找最完美的形式。然而,写作的悖论也在这里,存在需借助于某种形式得以显现并为人们所感知,而完美的形式的寻找总是徒劳的,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听到过一些伟大的写作者抱怨表达的困难和痛苦,他们面对自己的文字不能确认它的真实性,他们分明真切地体味到自己所渴望呈现的东西已从这写出的文字中悄悄溜走。出色的写作者对语言表现力的关注往往落脚在语言的暗示性和延展性上,他们深深地知道,一部出色的作品不仅要让读者看到有秩序的那一面,还要让读者体味到秩序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存在。而作为一名读者,他常常需要体会的是写作者在语言的缝隙中留下的富有暗示性的世界,被隐藏着的文本;读者的许多阅读快感更多地来自于灵魂最深处的体验,对许多人性真相的触摸。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①中说到艺术欣赏时把它比作登山探险,艺术欣赏的快乐是发现真相的快乐。很遗憾的是,许多文组织起来的那个世界。他很高兴看到观念、感情、形象逃离被指定的地方,在自己的思想中四散飞扬。被阅读的东西形式上是符号化的,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且具有流动性,借助于阅读者的体验,艺术家的精神之流得以学批评,却常常不能表现出深度阅读体验的丰富性、复杂性、真实性,以至于福柯不得不以感叹的语气来表达自己内心期待的理想的批评境界。②现象界里的真实是,真实的读者在阅读中,常常怀着一种特殊的带有个人色彩的乐趣来打散那些由作家精心在他的身上流淌。阅读朱自清的《阿河》时我再一次获得了如此真切的体会。
《阿河》是一篇语义复杂的作品,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特征。作品的整体音调颇不和谐,而人们正可以从这不和谐的音调中去辨析这世界的繁复和人心的深度。
《阿河》文本的表层讲述了一个山里少妇的故事。阿河十八岁,“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她男人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我”认识阿河,是因为到朋友韦君家度假,阿河恰好被表哥阿齐介绍到韦家来做工。我对阿河的初始印象是:“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一段时间后,“我”却发现阿河不仅聪明勤快,而且很美:脱去陈装后的“阿河如换了一个人。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满了蜜一般。”不久,阿河夫家的人找上门来,阿河被辞退了。春假时“我”再来度假,“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今天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己拣中的;这种年头!”
朱自清讲述阿河的生活和他人对她的评述时,取的是旁观的态度。从阿河的一面讲,阿河对自己的生活困境采取了自我方式的反抗,并最终取得了境遇的改变;他人中除“我”及韦家小姐和她的朋友持理解同情态度之外,多是冷漠和讥讽;但缘由又有所不同,有的出于嫉妒,有的出于蔑视,有的出于偏见。朱自清只是客观地叙述,让读者自己去品味。
引人注目的是,《阿河》中还有一个潜藏的文本:“我”对阿河的内心欲望的故事。从这故事中可以看见写作者意识深处的景观,包含在知识分子对平民女性关怀的故事里面的,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体验和想象的潜意识世界,一个人性的欲望化世界。正是这个世界有力地拆解了由同情理解构筑起来的人道主义式的关怀,让人看清楚热烈的情感后面是自私的人性伪装,形式上虽不像“他人”的冷漠讥讽嫉妒,骨子里却同样昭示出人内心深处的“恶”。可这又是别一样的“真”。这样的情形不免让人揣测,这是否是“我”在面对“他人”对阿河以言语进行伤害时,自己并不为之辩诬的深层原因所在呢?本质上,“我”是无动于衷的,或者说,“我”的潜意识深处本就有以伤害报复阿河来抚慰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理欲望?朱自清叙述“他人”对阿河态度时的客观冷漠的语调和写“我”对阿河渴望时的直抒胸臆处处都在昭示这一点。
一方面,“我”对“他人”对阿河的评述持不作评价的态度;另一面,说到自己对阿河的私人感受时却是不严肃的戏谑之姿态。“我”本不瞩目阿河,但阿河的自然本色之美在“我”面前现身之后,“我觉得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意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个礼拜!”
所谓“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这句话除了说阿河这样美的女子正是我心仪已久的模型之外,恐怕没有它解吧。文中交代了一个细节:在“我”和阿河的一次不期而遇中,阿河的表现是宁静的、娴淑的;而“我”却“窘极了”。“不自主”、“匆忙”、“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赶紧向门外一瞥”等显现出“我”内心中的慌乱、混乱。而“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则是说“我”处在一种“沉浸”的状态之中,难以描述清楚,只有时间之神能够默默记下所有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睛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这完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儿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儿了。”这段文字写出了阿河动人的美,“我”的欣赏却也是见真见性,多少有些戏谑狎怩,甚至轻薄之意味。当然,明敏的读者也不会对此大惊小怪。
后来,韦小姐跑来告诉“我”: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地睡,只翻来覆去地做梦,醒来却又一例茫然。”此段文字表述了两层意思:我的惆怅失望;对阿河命运的悲观猜想。而夜中的梦则指示了“我”真正的牵挂所在。“我”对其中的真实是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愿用文字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无可否认地掉进阿河所织成的大大的迷惑的网中了。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我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麽?他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麽去管!’我说。‘想法子啊!’陆嚷着。‘什麽法子?你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河,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这段简洁的叙事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几个人的简短对话,以及不多的动作语汇,实在够得上一篇心理分析的丰富材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光环真是太多了,在这素朴的描绘中,人们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原形。这就是多少有些令人恶心的众多知识者的嘴脸:自恋、做作、虚伪。他们似乎已习惯了自信,动不动就摆出一付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的架式,却又自恋得要死,只会清谈,“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别人的辛酸不过化成了象牙塔里清谈的材料。更可笑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的自作多情,陶醉在自造的悠然自在里,却从不对自己发问:谁给了自己如此话语的权力呢?
春假再来时,“我”听说了阿河生活故事的结局。“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说什么好呢?愿命运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这一来全完了”表面上表达的是“我”对阿河的失望,纯美的阿河变成了俗气的老板娘,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吧?何况,他们真的如此想吗?其实深层的是表达了自己梦幻的彻底终结吧——一种可能性的终结,倒未必是对阿河人生选择的评价。“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二、有意味的对照
朱自清的《阿河》在有意无意间打开了知识分子心灵的一扇门,可惜的是,朱自清并没有登堂入室。说到底,还是缺乏拷问自我灵魂的真正勇气和直面自我的诚恳之心。面对着青春女性鲜美的肉身,做作的知识者总是龌龊地顾左右而言他。可以用路翎先生的《财主底儿女们》来做一个有意味的对比。小说的第二部描述蒋纯祖在大时代里的生活,他在石桥场的小学校做校长时,“八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叫做李秀珍的十七岁的女学生敲开了他底房门,走到他的房里来,在说话之前便流泪。这个女学生聪明、美丽,蒋纯祖觉得自己常常被她迷惑。蒋纯祖知道她只有一个母亲,很穷苦,生活很艰难。”一句语调平静的陈述句“常常被她迷惑”,要比矫情的知识者的长篇大论来得真诚得多。这个女学生所以来找校长,是因为她的母亲把她的初夜权以两千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少爷。“蒋纯祖看着她,这种目光,万同华(蒋的女同事)觉得可怕。蒋纯祖看穿了李秀珍身上的那件粗糙的蓝布袍子,看见了那第一夜了。”现代文人中实在很难找到笔力如此遒劲的句子吧。面对美丽的李秀珍,蒋纯祖清楚地体会到自己身体里的“猛烈的火焰”。这猛烈的火焰的燃烧使得蒋纯祖“疲乏”,这种疲乏把蒋纯祖从纯粹的人道主义者的行列中驱逐了;然而,路翎就是在此顽强地要求他的蒋纯祖不许转过身去。蒋纯祖和同事商量如何解救可怜的李秀珍。与此同时,毫不留情面的路翎再次开始了心灵的揭破:指出在人们自以为高贵的精神状态里“有着一种朴素的,天真的愚昧,同时有着一种华丽的矫饰。”“所以这些生命,这些自我,就常常迅速地从它们底高贵的世界里跌下来,变成罪恶的。而且,这一切常常是令人难堪的。”高贵与邪恶的转换只在一线一念之间。蒋纯祖们面对李秀珍的可怜命运,最后想出的办法也是他们中有人“娶她”,让人感慨人的想象力怎么总是如此贫弱。然而,倔强的路翎还是揪住蒋纯祖们不放:“蒋纯祖激动,混乱,奇特地觉得欢喜,兴奋地笑了一笑,但同时觉得这件事是再也没有可能了。它本来就没有可能,而且现在那种绝对的热情消逝了。这时万同华姊妹领着李秀珍来,蒋纯祖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的感情是丑恶的。”③在现代中国文人笔下还曾出现过如此诚实的句子吗?这里面的痛苦、仇恨、绝望、自虐的快意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在这样一个曾被无数个矫情的写者描写过的往往是充满着温柔的痛苦的情境中,路翎接着还说出了“色情”和“荒淫”,这是鲁迅式的“自抉心食”。在《财主底儿女们》里汹涌着的不仅是伟大的时代,更汹涌着的是浩瀚的人心世界。与之相比,《阿河》显得是多么地肤浅和做作。“这种力量在蒋纯祖身上特别强烈。情欲表现在微小的动作中,表现在肉体的窥探中,表现在美丽的、壮快的想象中,但他底整个的生活说:这一切是罪恶的。”④简单地说,路翎的小说不是在道德的而是在生命的层面上来思考体味人类的生活。从个体出发,从最深处的情欲开始,因为面对着上帝正义的法则,所以,人觉到自己是“罪”的。朱自清的怯懦阻碍他进入这样的境界。路翎的蒋纯祖让人再次看见了鲁迅《墓谒文》中“自抉心食”一样的对自我的阴冷、刻毒,不给自己留一丝情面:“因为没有美丽的女人激赏他,因为当代的权威从未向他伸手,——他承认这是他底最痛苦的题目——他消沉、冰冷、倦怠。”“于是他(们)开始厌倦了。”“他想,一切是好的,一切是有价值的,但他,假如得不到个人底光荣,便不能承认这些美好和价值;假如得到,那又从根本上就是虚伪的,还是不能看到这些美好和价值。”“这样,他就把一切人都拉到丑恶的泥沼里来了。”⑤路翎借着他的蒋纯祖指证了人类生命、生活丑恶的本质,撕破了一切美妙的伪装,蒋纯祖不能容忍自我欺骗,他同时用睥睨一切的目光审判着人间的自我欺骗,因此,他更无法和身外的世界和解了。而对于路翎来说,这样的无解却让整个的世界和人心在他眼前一片清明。
所以,相比而言,《阿河》让我更注目的不是其中蕴涵的同情和悲悯,而是“我”对阿河的“身体性”的体验。当然,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身体已被染上了各种色彩,身体早已有了不同层次的划分,身体有政治的身体,伦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物质的身体,而似乎原来的那个生物的、人性的身体却离人越来越远。老、孔之时,尚有身体。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愚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愚?”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就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了。朱熹更决绝:“存天理,灭人欲。”虽说朱子对其所言也做了尾注,说饮食夫妻为天理伦常,而五食十色三妻四妾则是人欲。但朱子的决绝声气还是摆明了他禁欲的面目。于是中国文化渐渐成了没有自然肉身的文化,余波绵延到现代不绝如缕。比如郭沫若的《屈原》,一味渲染的便是屈原的政治伦理意识,丝毫不触及个人自然之情怀,而郁达夫《沉沦》的身体性倾诉却遭到许多人的恶骂。在强力的外在环境的压迫下,在身体被专政的时代里,作家们都只好争着做没有身体的人,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用心灵来感应,他们把深度的自我体验藏匿起来。写作因此成了“传声筒”、“留声机”,没有自我、更没有真实的身体细节,写作成了自外于自身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生命的歌唱。朱自清《阿河》中的身体性体验,也许说不上高雅,却别有一种意味在其间。
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阿河》里隐意识的心理描写并没有被作者用来建立认知自我的心灵档案,充其量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宣泄。问题是,《阿河》表现出来的作家本人的自我分裂会衍生出怎样的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比如,这样一个不诚的也即没有真实深情的知识者,如果去担当启蒙者的角色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同为知识者,路翎和朱自清在遇到相似的人生境遇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不同的。可以说,两人都直面了自己的内部世界,都写了自己的体会,不同的是,路翎还有对自己的分析、拷问,以及不留情面的自我揭破。在对自我的“丑”、“恶”揭破的过程中,路翎的蒋纯祖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同时也就抛弃了乐观、高高在上的姿态,走向了自我忏悔。朱自清则到自然的体会为止,完全说不上心灵的自我分析,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高于他笔下人物的位置。一面是私欲的玩味,一面又是不够清洁不够诚恳的温情,而且,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二者之间难以找到像路翎笔下人物的那种完整统一感。蒋纯祖的自我分析拆解了自己,让旁观者看清楚了他的内部的分裂、自我征战,但不是人们通常说的有什麽两个我存在,而是真实的那个我经过挣扎勇敢地站了出来,驱逐了那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假我。蒋纯祖指证了自己的“丑”、“恶”,同时也就保留了自己的“纯”、“真”。也许,蒋纯祖说不上“深情”,但他至少做到了“诚恳”。而在朱自清的《阿河》里,透过文本,读者看见的则是两个分离的“我”:表层的这个对他者充满着理解温情;内面的那个对他者则又是满怀着被遮遮掩掩的粗鄙的欲望。关键是在他们之间你却找不到一个自然的连接点来理解他们间的真实的逻辑关系。一个人对于他的自我来说应该是完整统一的,即便他的内在自我是分裂的、矛盾的、对抗的,在他人看来是不和谐的、不可理喻的,他自己仍然是他自己的整体。一个真实的个体生命都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统一体。当这个个体把自己向整个世界敞开时,它应该是自然的、真实的,观看者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每一条纹理,通过这每一条生命纹理的勘察,观看者对这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不会产生最起码的不真实感、不信任感。而朱自清的问题恰在这里。在《阿河》里,读者既可以看到朱自清的显意识,也可以看到他的隐意识,但是,显意识和隐意识的连接点在哪里呢?朱自清没有很好地找到这个点,读者看见的是一个分裂度很大的作家的自我,对于一个写者来说,无论他向外部的世界展示怎样的自我,这个我不能是一个分裂度很大的我,最起码他应该是自然合情合理的,不能超出人性的理解范围。这个自我可以有很多面,但这许多面应该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我”之上。朱自清的《阿河》不能给读者如此的印象,文本里的“我”给人以内外不统一的印象,这就是我所说的《阿河》中的“我”不如路翎笔下人物完整和谐的意思。
他们面对自我的心态是不同的。路翎是毫不留退路地彻底揭破,朱自清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支支吾吾。说白点,就是朱自清没有路翎诚恳,也许还有自我认知能力的差异。路翎小说中的人物老是和自己过不去,他们内在的自我处处存在着危机、矛盾、自我的搏战,然而,这样的内部混战却构成他们自身真实丰富深邃的存在。路翎笔下的人物很像《圣经》里受难的使徒,自己对自己施行着心灵的苦行,独自把自己整个地承担,虽永不得安宁,却会让自己的心灵有最真实的皈依而不至落入完全的虚无。当年《财主底儿女们》出版时,胡风就断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或者说尤其是向着未来的精神状态),它底产生和成长就愈是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不能不达到所谓‘牵起葫芦根也动’的结果,那麽,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就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了。”⑥当然是这样。没有心灵的描写,就不会有人类真实的历史记录。
三、从拷问心灵的深情度开始
心灵所乐于接近的并不是冰冷的理性,而是火热的感性的深情。在人类的语言里,表达最“深情”的一个字是“爱”,人类一切主动的行为最深层的动因皆是出于爱。爱是链接一切的最可靠最可爱最真实的纽带。“启蒙”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连接自我与社会间所寻找到的让自己感到最自适的一个词,他们中的许多人简直情不自禁地把“启蒙者”当做识别自己的一个徽章,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既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强力推动,也是知识者的自我鼓噪,使得“启蒙”成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后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还成了一些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者拼接中国现代文化版图的基本思路。⑦当然,当历史已成往事,也有少数的质疑之声,但这不多的质疑声也不是从根本上要否定启蒙,只是在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上对启蒙提出进一步的修正思考,这实际上是说人们认识到启蒙对于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需要继续下去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中,新的旧的话题被重新提出。如关于启蒙者的身份的诉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历程;对启蒙者也即现代知识者心路历程的再梳理这样的温故知新又会让后来者发现什麽;以及更具体的问题如“国民性”概念的合理性、普适度如何;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真实关系等等。⑧质疑者并不是要颠覆启蒙话语,也不是要消解知识分子自身。清算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虚妄性,直面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缺陷,这样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先前的许多带有自我迷恋自我陶醉性质的话语描述,因而使重启“启蒙”话题获得了崭新意义。
在此我想通过对朱自清以及其他相似的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写作状况的考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中国现代知识者到底对自己具有怎样的角色意识?对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身份的识别能否不再总是局限于他们的思想层面,而进入他们的人格心理情感层面?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者到底对他们身外的世界有几多深情?鲁迅指证的中国人的瞒和骗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不是真正深情的缺乏?为什麽现代中国的最深刻者鲁迅说到自己的同胞时每每以“隔膜”一词相对?是思想智力上沟通的艰难还是心灵情感上的自私的封闭使然?笼罩在这些问题之上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启蒙应该具有怎样的一个方向?在曾经的方向性的选择里有没有需要重新选择的必需?启蒙曾和启发民智紧紧连在一起,启蒙者们似乎轻易地越过了一个前提,即在他们担当民众的启蒙者之前,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启蒙?
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此种情景让各种式样的仁人志士不自觉地把眼光瞄向了广大的身外世界,满脑子都是宏大的启蒙与救亡,而如何自我启蒙自我拯救却被不经意地放在了一边;在这种错觉里,仁人志士们似乎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来俯瞰他的时代及民众,这样的启蒙从一开始就以社会、国家、民族、时代、革命等等宏大的字眼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人的启蒙,尤其是个人的启蒙。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也即进行人的再造的主题最终被宏大的主题所取代。而且,在人的启蒙上也存在着问题,既往的人的启蒙更多地关注了人的“理智”,而对人的“心智”却关注不够。二十年代时鲁迅说中国人在“昏睡”,可是到了三十年代他才发现中国人是在“装睡”。这样的确认会让鲁迅对自己当年的另一个判断——“中国到处都充满了瞒和骗”更有感触吧。诚如一个论者所言:“鲁迅很早就论定这个民族最缺的就是‘诚与爱’。”“与同时代的启蒙者很不一样,鲁迅一生的着力点是人的灵魂而不是家国天下,是个我的生命叙述而不是社会意识形态。”⑨说清道理启发民智是较容易的,可是,心灵的建设是简单的说理所能解决的么?周作人为何恨恨地说: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新生,必须从知耻开始。摩罗认为中国人要有“耻辱”意识难道没有道理?⑩有羞耻感,才会有真实的自我批判;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你对自我从没有羞耻感,可以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有诚恳之心的人,也不可能是对人、国家、民族有深情的人。一个人深情的程度就是他真实的程度。正是“深情”的过于缺乏,中国的启蒙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还是再一次回到朱自清这里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江浙一带谋生时,朱自清曾有一篇实际见闻的文本实录《温州的踪迹·生命的价格——七毛钱》(1924),文本里的义愤让人感佩,但总让人感觉缺了些什么?缺什么呢?作者在纸面上分析思索推论感慨,但也到此为止,还能如何呢?也许不能如何。我所担心的是中国文人满足于到“书斋”为止的习性:我在书斋里已经表达了我的立场,我则可以无愧而放下了——缺乏真正的深情。我自然希望这只是我个人的瞎想。作者在文末问:“想想看,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这样的疑问让我免不了地担心:作者可别把自己排斥在外啊!这是怎么说呢?让我再举个例吧,还是路翎先生的《财主底儿女们》,小说里写到蒋少祖以“委员”的身份到伤兵医院去探望伤员,看到破衣烂裳,缺手少腿正在死线上挣扎的士兵,“衣冠楚楚”的蒋少祖觉到了“羞愧”、“耻辱”,而且是人类的“耻辱”;他觉得他侮辱了这些可怜可敬的兵士,他感到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的羞愧。“蒋少祖踮着脚走过去。这个呼号的兵开始哭泣,用手挖墙壁。蒋少祖突然想到,既然在人类里面有着这样的绝望而可怖的境遇,那么这种境遇便很可能即刻就落在自己身上。他苦闷地想到,为什麽自己一向没有感到这个。不解决这个为什麽还能生活。”⑪朱自清有这个“不解决这个为什麽还能生活”的意识吗?在他的文本里,他只有这样的心存侥幸的话语:“我们的孩子所以高贵,正因为我们不曾出卖他们,而那个女孩所以低贱,正因为她是被出卖的;这就是她只值七毛钱的缘故了!呀,聪明的真理!”⑫最后一句的自嘲我甚至要说是不够庄重的。是体会自己的聪明和发现所谓的真理重要,还是注目人间的真实悲剧带着自己的深情去思考人的命运人的出路重要呢?路翎的“蒋少祖脸打抖。是的,他死了。是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的,全上海底富户,对他们底为祖国而流血的兄弟们如此残忍!”“蒋少祖悄悄地往外走。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觉得犯罪——他,蒋少祖,穿得这样好,有着一切,从孤立无援的、濒于绝望的、为这个民族流了血的兄弟们身边逃开。”⑬这才是真实的悲悯和深情啊!在悲剧面前,“理”是多么地苍白。
和十七岁的路翎比,朱自清缺少了什么呢?一个人,无论他(她)是做什么的,他(她)的“深情”的程度就是他(她)“真实”的程度。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1928年冬天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时说:“我终身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的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⑭何况,同情还有同情的不同,中国知识者对他者的同情往往不过是有距离的理智的同情,或者确切地说,只是言语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同情。言语上的同情者恐怕也只是旁观者位置上的冷静者吧?没有发自心灵的真实投入,所以我们只会有表面上的火热骨子里的冰冷。这样的知识者来做民众的启蒙者会是怎样呢?恐怕还是难逃鲁迅所说的隔膜吧!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瞿秋白就曾感叹过:在街头活动的政治家们和他们所要发动的民众之间心灵并不相通,因为他们内心的所愿所想各自不同。民众自然目光狭隘功利务实,政治家们则心怀天下,但实际则是要驱使广大的民众来助他们实现囊括天下的雄心,说野心也行。⑮胡适也曾感慨:大众“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够了。”⑯也许胡适太悲观了,不该一概而论,这世上终究还是有一些不计个人得失而献身天下的人,虽然这献身中也会多少含有个人私密的欲愿,但主观上是比较诚恳的,客观上也是有益于人类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胡适的悲观如果不是全部的真实,至少提醒的意义还是在的。而史沫特莱对知识者的指认“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更是说到了根子上,王小波曾很刻薄地描述过一种难看的嘴脸:那些挟自己的专业以自重的家伙,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一点可怜兮兮的知识无限地放大,使之成为包治人间一切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抬上至圣至贤的王座。⑰还可以看看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对知识者富有意味的描述。鲁迅想要告诉人们:神话、传说和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言的叙述。鲁迅的重新叙事使得神话、传说和历史不再是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安排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分别得清清楚楚的“故事”,而是充满了生活的多重性和相对性。哲学思想不能是超越生活过于思辨化、形式化的东西。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充满着冷嘲热讽,尤其是对拥知自重的夫子们,他打定主意要去掉他们身上那些神圣的伪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文章里,鲁迅正面阐发过他对“知识阶级”身份的理解,鲁迅的理解是西方化的,他反对知识者拥知自重自炫,对知识分子的风骨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为任何物欲所引诱、不为任何权势所屈服;还有知识者的使命,也即萨特所提出的“介入”。鲁迅终身都在抨击中国太多的“文字游戏党”,一提起他们,鲁迅简直是怒不可遏。作为知识者,仅仅具有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同时还得让自己记住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真实深情的人。作为启蒙者他是拥有知识的“人”,他对天下的关怀方式当然是从他的专业开始,但在专业的背后,还要有一颗真正悲悯热爱的心灵——只有经过心灵润泽的知识才会真正地温暖人间。
注释
①万梅·特尔·阿米斯:《小说美学》,傅志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②米歇尔·福柯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在我们这儿,很多时候,这样的“梦想”确实是梦想。③④⑤⑪⑬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74—1080、1090、1102—1103、51—53、51—53页。⑥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⑦钱理群等人主编初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李泽厚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都是循此思路而建构。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提出对被翻译的现代性要重新进行论证;林毓生的重读五四;陈平原的重返五四现场;王晓明的《再思录》由古及今对中国知识者心灵历程的探寻;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在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启蒙的问题。⑨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修订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366页。⑩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⑫《朱自清散文全编》,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9、30 页。⑭转引自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后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2页。⑮验证这样的判断并不困难: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里的革命及其革命者;以及老舍的《骆驼祥子》里的车夫祥子和伪革命者阮明之间是在怎样地互动就可明了。⑯转引自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安徽教育出版社。⑰参看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中的《知识分子的不幸》、《积极的结论》、《智慧与国学》、《理想国与哲人王》等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I206
A
1003—0751(2011)03—0215—06
2010—09—15
安徽省教育厅基金项目《文化心理分析背景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写作》(2008JYXM456)的阶段性成果。
张晓东,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阜阳 236041)。
责任编辑:凯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