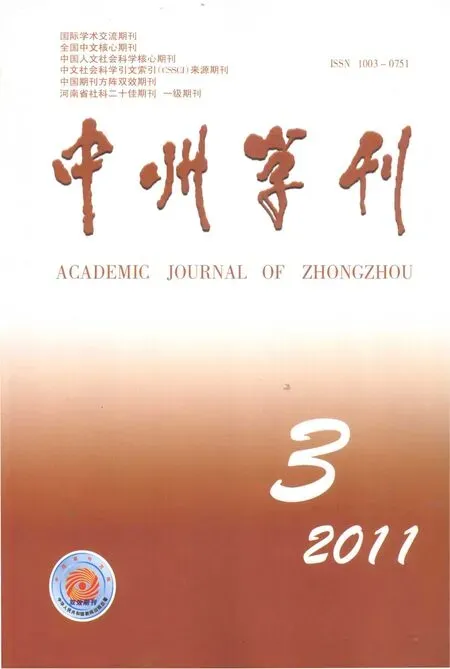制度视野中唐高宗时期诗歌发展之路向
王新荣
制度视野中唐高宗时期诗歌发展之路向
王新荣
与贞观朝相比,唐高宗时期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科举考试重文辞、轻德行等。这些变化与士族体系的解构和庶族士人群体的崛起相表里,大大激发了士子特别是广大下层士子的进取欲望和功名心,从而对一代“浮躁浅露”士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士风在政治境遇不同的文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言之,在上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重文轻德、以文自矜,在下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露才扬己、愤激不平、自媒躁进。士风必然要影响到诗风,并对其时上层文人多重艺术形式的雕琢、下层文人多重言志抒情的诗歌路向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选举制度;浮躁浅露;士风与诗风;诗歌路向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650—683)是唐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是沿着两个不同路向交错发展演进的: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下层文人才高位下,仕进生涯中多漂流辗转之艰辛,故其诗歌多以借他乡山水以抒发心中不平之气为主;以文馆学士为代表的上层文人多生活在宫廷庙堂之内,其诗歌多借奉和应制以炫耀诗才,走的是锻炼诗艺的路子。在唐诗发轫之际,前者赋予其以实质的内容,后者赋予其以精致的形式。两条道路交错发展,共同指向盛唐的诗歌高峰。进一步考察高宗诗坛后我们又发现,两条诗歌发展路向的形成与其时文人命运的穷达密切相关,而文人命运的穷达又与其时选举制度的某些重要变化紧相关连。事实上,某个时期的诗歌风尚若要持久而广泛地产生影响,就必然要以某种制度的形式来保障。本文即旨在从制度的视角来探讨这一时期的两条诗歌发展路向成因及其诗学追求。
选举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贞观朝选举制度以士人德行学识为本,不以文词为贵。太宗尝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张,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矣”;“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①。永徽六年,武则天夺宫成功并开始实际地参预朝政,“帝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着手对贞观政治体制进行解构,科举和选官制度亦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选举制度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科举考试重文辞,轻德行。从本体意义上讲,文辞和德行并非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唐初科举考试中之所以有重德行与文辞之分,根源还在于选举方面士、庶观念的差异。“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③士族子弟重经学,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故其强调德行,强调通经致用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而唐高宗时期,士族观念从制度层面上已开始渐被解构,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显庆《姓氏录》的修订。庶族力量开始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庶族力量以新进进士为主,而其时的进士科考试以文辞为清流仕进之正途,故其时选举观念在文辞、德行上的分野实质上是士、庶政治势力斗争之外显。
进士科加试杂文是科举重文辞的突出表征。进士科加试杂文并制度化始于永隆二年刘思立知贡举时。其实,在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加试杂文即偶有之。如显庆四年,进士试即有《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之题目。唐代科举之法又分常科和制科,制科对文辞的重视尤胜常科。高宗所开制科几乎每科都有关于文学的科目,如乾封二年有“辞赡文华科”等。皇帝求贤的诏书中也经常有对于文学之材的要求,如显庆五年诏文武百官荐举“藻思清华,辞锋秀逸者”④等。新进进士多以文辞取胜自然就形成一股潮流。另外,武后“颇好文史”,为了政治需要,“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奖进”⑤,于是遂促成“国家以吏部为取士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矜于德行”⑥的局面。制举方面,高宗在下诏征召“德行光俗,邦邑崇仰者”的同时,又征召“婆娑乡曲,负才傲俗,为讥议所斥,陷于跅驰之流者”⑦,亦足见其时士人品行已不足为重。
变化之二是科举及第和选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朝23年间共取进士205人,年均9人;而高宗在位33年间取468人。明经科考试及第人数更是十倍于进士,“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⑧。关于制举,《通典·选举》卷三云:“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高宗朝开制科非常频繁,应制人数和门类大大增加,开有“洞晓章程科”、“学综古今科”等⑨,可谓轰轰烈烈,风头直压常科。
进士及第人数的增加自然会导致选官数量的增加。而其时士人入仕还可以通过朝廷扩大流外官的铨选数量等。唐朝每年所放流外出身有千余人甚至二千人,且这些流外出身者每年入流内叙品的数量不逊于科举入仕。显庆三年,黄门侍郎刘祥道上奏:“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入流之数,以三分之论,每二分取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⑩另外,高宗朝的选官范围也逐渐全国化。上元二年,朝廷开“南选”之途,把选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岭南、黔中等蛮荒之地,即为显例。
实际上,选举制度变化的最重要意义是它极大地激发起广大下层士子久被压抑的勃勃欲望和进取心,从而对唐代士人政治理想的转型产生了极强的催化作用。
首先,选举制度的新变使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看到了在门阀士族统治时代不可能看到的致身显贵之机会,使得他们普遍怀有一种朝为寒士,暮登朝堂的急功近利的躁进心态。当其久滞下位时,他们一方面自媒求进,炫耀文采,四处干谒,一方面又不掩饰自己心中怀才不遇的哀怨与愤懑。由此形成一种逞才放浪之风习,以浮华相竞胜,遂形成一代“浮躁浅露”之士风。其次,这种变化还在客观上促进了唐代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转型。传统儒家思想原则上强调每一个士人都必须抛却自己的功名利益而提倡“兼济”和“穷且益坚”,但高宗时期的选举制度大大激发了文人的个人欲望,使得他们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突破了封建名教的缰索。杨炯明言:“丈夫皆有志,会要立功勋”;李峤高呼:“倚天图报国,画地取雄名”。这表明他们的政治理想已由“高远的、无私的‘致君尧舜’和‘济世安民’式”向“近期的、现实的个人功名、利禄式”的转变⑪。
“浮躁浅露”的文人及其诗歌创作活动
据《旧唐书·王勃传》载:“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勮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谓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后果如其言。”这则材料指出当时新兴之文人阶层存在一种“浮躁浅露”的风气则是符合实际的。“浮躁浅露”的时代士风又因文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影响到他们诗歌创作活动重心的差异。
对于上层文人而言,“浮躁浅露”表现为一方面以文自矜、目空一切而实乏吏能,一方面又操守不谨、谄媚阿谀。许敬宗、李义府这两位老资格的弘文馆学士,其操守卑污已书入史书,广为人知,固无须赘言。而薛元超为高宗朝“朝右文宗”,衔匡主之遗命,负荐士之重荷,高宗倚之为心臀,士子奉之若北斗,然亦因交构李义府而遭贬,卒成其人生玷玉之瑕,令后人于唏嘘之余,不能不慨叹其时士风之浇薄。
这类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多限于宫廷应制和馆阁唱和,因为只有这样的创作活动才能给他们提供媚上和逞才的机会。《全唐诗》收有高宗李治的《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诗,刘一之、胡元范、郭正一、任希古、元万顷、裴守真等人均应制作《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这是比较大的一次唱和活动。这些唱和诗多咏帝王家事,词采还是一样的华丽,但内容和格调上却是越发的柔靡,这又恰是文臣“浮躁浅露”的一个绝好注脚。
沉沦下僚、羁縻幕府,甚至流落民间的下层文人的数量要远比上层文馆学士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初唐四杰”外,李峤、宋之问、杜审言、薛华、王公方等大量今天已经不太为我们所知的下层文人群体亦因才高而自负。他们一方面在诗中表现自己的踔厉风发、傲视王公,另一方面在行为上却又不得不时时委屈自己而自媒求进。他们因仕进坎坷而大量作诗,高呼要啸傲烟霞,却又不甘自我埋没,时时因干谒或转任而飘零沉浮于滚滚红尘。他们的浮躁浅露表现为愈久滞下僚愈躁进,愈压抑愈狷介刻薄,终生在个人功名的追求与失落中痛苦地挣扎。
王勃于麟德年间作《上刘右相书》,大言自己:“未尝降身摧气,逡巡与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托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于心耳!实以四海兄弟,齐远契于萧韩;千载风云,托神知于管鲍。不然,则荷裳桂楫,拂衣于东海之东;菌阁松盈,高枕于北山之北。复区区屑屑,践名利之门哉!”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甘心在王府中陪贵介公子们斗鸡走狗。这类文人的诗歌创作活动多集中于干谒和祖饯。在那个时代,下层文人、新进进士、流外入流者若要顺利释褐、选调,离不开高级官员的提携,这就使得其时干谒之风甚炽。高宗时期以文干谒的资料现存较多,《全唐文》中“四杰”及同时文人中有许多“上某某书”式的文章可证。王勃《上从舅侍郎启》中记曾上《宪台诗十首》,《再上皇甫常伯启》记上《乾元殿颂》一首。与干谒诗相比,祖饯赠答诗数量和质量都要高得多。如卢照邻、王勃、杨炯都参加过大量的迎来送往的诗酒活动,创作了大量送别诗,其诗也大多真情婉转、凄恻感人。
两种诗歌路向的斗争与发展
人生际遇和士林风气会对文人的创作活动和创作心态产生重要影响,而不同的创作心态和客观环境又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诗学追求。综观高宗时期的诗坛格局,其基本特征就是两类不同命运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两种诗歌路向的斗争与发展:龙朔新变与对龙朔新变之批判。
高宗时期,以弘文馆学士为代表的上层文人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对贞观朝文馆体制和宫廷文学活动的继承和延续,高宗朝文人以文自矜,游戏于声律偶对而回避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使得诗歌创作在重艺术的路子上变本加厉。龙朔变体即应运而生。
杨炯《王勃集序》指出:“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后世学者多以“龙朔变体”概括这一时期的诗风,又因上官仪“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⑫,地位既高,文名亦盛,“上官体”也就成了龙朔新变诗体的代表。许敬宗、李义府在“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方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薛元超,其奉和诗也是“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而其拔擢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义方、顾徹、孟利贞等入弘文馆,对于龙朔变体的推波助澜才真正使得这一重艺术的诗歌新风得以成为时代潮流,且能够持续发展。
上层文人对于声律、对偶等诗艺的重视还表现在诗格和类书的编撰上。上官仪于高宗朝初年曾著《笔札华梁》一书,其主要内容是探讨诗歌的对偶和声律艺术的。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格著作是元兢的《诗髓脑》。但是元氏比上官仪更明确地提出了四声二元化的原则,对于律诗篇制定型有着奠基作用。高宗朝所编撰类书主要有《文馆词林》、《瑶山玉彩》、《芳林要览》等。这些动辄千卷的“诗歌样本”,为宫廷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贞观朝类书编撰的主要目的在于文学普及,而高宗乃至稍后的武后朝类书的编撰目的,则更多地是从锻炼诗艺的角度出发了。
骆宾王倡言“非敢希声刻鹄,窃誉雕虫”,“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⑬。这一时期的下层文人已没有了贞观文人那样雍容风雅的情怀以咏歌王政。涧底寒松、深谷青苔、江边孤凫是这些人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他们心中都充溢着一股悲愤不平之气。他们要借诗以抒发这股不平之气,这就导致他们的诗歌创作向小雅中的“怨刺”精神靠拢。王勃称自己有“耿介不平之气”,杨炯“心中自不平”,卢照邻明言“仆本多悲泪,沾裳不待猿”。这些人之所以心中多悲愤不平之气,是因为他们“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⑭,“有其志,无其时”,是因为他们身处穷途,心中“事有切而不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⑮。所以在他们看来,诗歌的功能就在于发抒心中郁怏不平之情思,应该借江山以“宣其气”,借琴酒以“泄其情”⑯。正如李峤明确指出的那样:“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所以“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颦之野,斯见不平之人”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的诗歌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泣穷途于白首”、“嗟歧路于他乡”⑱,是哭出来的,是叹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王勃的《别薛华》最具代表性:“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寒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来与往,俱是梦中人。”其情深言浅,悲歌当哭,的确是与龙朔新体大异其趣的。
注释
①《新唐书》卷45。②《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④徐松:《登科记考》。⑤《新唐书》卷45。⑥徐松:《登科记考》。⑦李治:《唐大诏令集》。⑧《通典·选举》卷三。⑨徐松:《登科记考》。⑩刘祥道:《陈铨选六事疏》。⑪程遂营:《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转变》,《史学月刊》1994年6期。⑫《旧唐书·上官仪传》。⑬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⑭王勃:《涧底寒松赋并序》。⑮王勃:《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⑯王勃:《春日孙学士宅宴序》。⑰李嶠:《楚望赋序》。⑱王勃:《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
K242
A
1003—0751(2011)03—0205—03
2011—03—12
王新荣,女,郑州师范学院副研究馆员,图书馆馆长(郑州 450044)。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