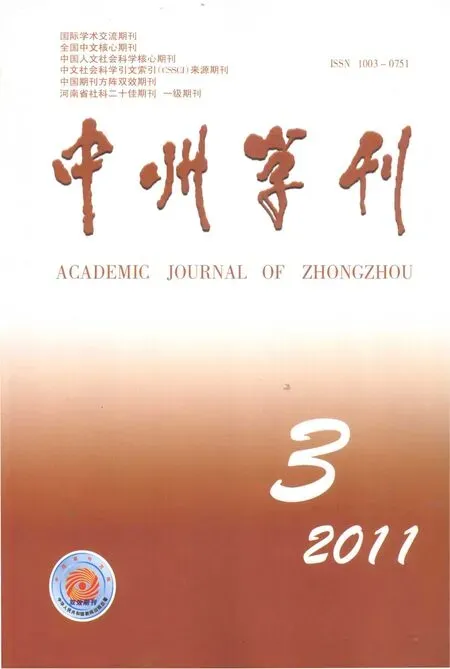秦汉时期河南战略地位探析*
杨 丽
秦汉时期河南战略地位探析*
杨 丽
河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古代一直被称为“天下之中”、“腹心所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得中原者得天下”为世人所熟知。秦至西汉时期,这里是国内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关系天下局势的命门所在,汉武帝称之为“天下冲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内最重要的战略枢纽。东汉时期,河南作为京畿要地,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汉王朝的重心,其重要性和优越性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故而其军事价值和地位达到巅峰。
秦汉时期;河南;中原地区
一、核心区域:河南在秦至西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说来,每个国家(政权)都有自己的核心区域,它是仅次于首都的重要区域。根据不同的构成类型,核心区可分为起源核心区、民族核心区和经济核心区。①起源核心区,是指国家最初的发源地,国家后来的版图都是在此基础上进化而成,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潘塞曾说:“国家的核心区通常是中心或者发源地区,在这个区域中,这个民族产生并且成长”、“国家正是从这个中心区扩展出来,核心地区通常是这个国家原来的位置而且包括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比起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民族在文化上也许更为相近。”②起源核心区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较稠密,资源较其他地区富饶,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民族核心区,是指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所聚居的区域,它既可能与国家起源的核心区相同,也可能相异。但无论如何,这个居于优势地位的民族核心区通常被视为这个国家的象征,如当代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经济核心区,是指在国家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区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美国的五大湖区等。这一区域的特点是,生产能力强、市场潜力大、交通运输便捷。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起码有上述三种核心区域,它们往往存在着区域重复,即某一区域兼有几种核心区的特征。以此分析秦汉时期的河南,可以看出,河南在当时是国内重要的核心区。
首先,三代时,夏的统治者太康、羿、桀都建都于斟鄩,“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③,而“斟鄩”的地望,或说在今巩县西南,或说即偃师二里头,按吴起之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④,斟寻此地,不外乎今洛阳周围。也就是说,早在三代之初,洛阳及其附近区域,就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地区了。商汤建国至盘庚迁殷,国都亦有五次迁徙,分别为嚣、相、耿、庇、奄,其中嚣即为今河南荥阳东北,⑤而殷即是今河南安阳西北。其后,周代兴起,周公辅成王,营洛邑以为东都;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东周时期洛阳更是长期作为周天子都城。据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系辞》中,有一句著名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孔子周游列国不得志时,亦曾感叹:“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⑥可见,无论从政治秩序还是思想文化,河洛地区都是中华民族起源地区的核心区之一。
其次,从民族成分上看,河南位处中原,一直是区都是中华民族起源地区的核心区之一。
华夏族——汉族的聚居区域,尽管先秦时期曾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周边活动,如密县(今新密市)有“狄人”,陆浑县(今嵩县)有“陆浑之戎”,但到了秦汉时期,这里几乎完全是汉族所居之地,先秦时代华夷杂居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从经济上看,河南自三代以来即是国内重要的经济区,《尚书·禹贡》中说豫州“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即其土地良好,出产丰饶。司马迁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⑦汉代的国内粮食主产区,主要在关中平原、成都平原、江汉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便是当时国内的重要粮食产地。刘秀统一天下,先收河北以为基地,后占河南,取其粮草,得其地利,乃成大事。
最后,从文化渊源上看,河南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的文化重地,是德治天下的象征。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以“天命无常”,作《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爽》等敕令,承认“天命”的关键是“德”,得民心者得天命。“周公作洛,不仅为周王朝建立了一个财政经济中心,而且还建立了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之‘中’和影响当时以至后世的文化之‘中’。历史地看,最后一层尤为重要”⑧。秦汉时期,这种周风的遗传仍浸淫良久,洛阳作为德政的象征,深入人心,洛阳乃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之地。⑨元帝时翼奉建议迁都洛阳,就是基于洛阳乃成周德政之代表,希冀西汉能借此重整旗鼓,摆脱不断的天灾人祸。⑩至于东汉初年,刘秀选择洛阳为都,更是受其“柔道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影响,“迁都洛阳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被人效仿,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⑪。此外,秦汉时期河南不仅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国内中心的区域优势,还是国内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
综合看来,河南无论在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抑或交通条件,在秦汉时期都属于国内的核心区域。核心区域对整个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国家的核心区往往不止一个,秦汉时期的河南也只是国内若干个核心区之一。但河南这一核心区,在秦汉时期是国内仅有的能与关中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核心区,在西汉时期,洛阳与长安并称“两京”,不但有迁都洛阳之议,政府在政策、制度上亦有特殊优待;东汉建都洛阳,政府虽以长安、南阳为陪都,却已不再重视关西地方。洛阳无论作为首都还是陪都,其长时间为中央政府所重视,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完全可以认为,河南在秦汉时期是国内最重要的核心区之一。
二、“天下冲阨”:作为战略枢纽的秦汉河南
自秦至西汉,河南的战略形势多有相似。汉武帝在评价洛阳时说:“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⑫另一处记载为:“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⑬其实,早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就曾评价洛阳地区是“天下劲兵处”⑭,为此将封于附近的韩王信(时封颍川)徙封代。无论是“天下冲阨”、“天下咽喉”还是“天下劲兵处”,所传达的信息都一致:西汉的最高统治者将这一地区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枢纽。
战略枢纽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合力构造的,就军事地理而言,战略枢纽是能改变一定区域内攻防双方胜负条件的某个地点或者某一块区划。战略枢纽的级别高低随着其能影响的地域范围大小而变化,其影响的区域越大,战略枢纽的级别就越高,其军事价值也就越大。在中国古代的国内战争中,一般而言,当国内呈现东西对抗之势时,控制国内战争形势的战略枢纽往往出现在豫西——河东区域;当国内出现南北对抗之态时,荆襄、淮南两地则多是战略枢纽。⑮形成左右天下格局的高等级的战略枢纽的原因,宋杰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和几大经济区并存的局面有关。古代中国通常呈现关中、关东、江南等经济区域,这些大的经济区为产生割据势力(政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数个割据势力依靠经济区而起时,往往各经济区的交接边缘便是割据势力的交汇处,容易产生长期而持久的战争,也就导致了产生拉锯战的战略要地。二是和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一般说来,开阔的大平原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容易出现大会战而不会出现长期的持久战。而弱势的一方要长期维系对抗的局面,必须凭借山河水网等险峻的自然地理条件来作为天然屏障。三是与水陆交通干线有关。中国古代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战略枢纽,在国内并非是一条绵延的防守线或广阔的作战区域,通常呈点状分布,范围相当有限。但这些枢纽几乎都是当时国内水陆交通的主干道的结合处,能够有力地阻塞对手大规模的行军和后勤运输。四是与军事装备和作战方式有关。古代中国的战争,在宋以前,几乎以冷兵器为主,春秋以后车战减少,战国以后城垒增加,使得在冷兵器条件下的城池攻防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地处水陆交通枢纽的高大城池,极易形成战略枢纽。这种局面在南宋末年火药、火器大规模用于城池攻坚后才发生变化。⑯
某一区域的军事地理及其作用,主要在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中得以体现。能否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某一特定地区是否能成为战略枢纽;而战争的规模、特定地区对战争的影响力,决定着这一战略枢纽的等级。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西汉时期河南郡的战略价值,可以看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地理环境和基本经济区看,河南位于关东、关中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冀朝鼎指出:“虽然西汉着重发展关中,而东汉则更多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河内,但是,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这一基本经济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供应基地和政权所在地。”⑰其实在这个大的基本经济区内部,又分为关中(即泾渭流域)、山东(汾水、黄河中下游流域)、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几大经济区,如前所述,关中与关东是国内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区,二者基本以黄河(壶口——风陵渡段)、崤山为界,正好在河南、山西一带交汇,这里自然易形成分别控制几大经济区的势力的冲突。
其次,从战略布局的角度看,河南在西汉时期的国内战争中,始终是觊觎天下的武装集团所努力谋划、夺取的目标,并且曾多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国内形势明显呈东西分野时,河南地处战略要冲的地位就更加明显地显现了。秦汉时期,河南地区始终是国内战争中的焦点。总体而言,河南的战略枢纽地位反映在战争中,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河南是关中政权防御的核心,要保长安,必先保洛阳。秦以丞相李斯子李由守卫三川,西汉初年刘帮派灌婴屯驻荥阳,七国之乱时窦婴以大军屯荥阳以备不测,周亚夫兵至洛阳、荥阳后以为“荥阳以东无复忧者”,都可见以关中为基本经济区的中央政府,在面对关东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敌对势力时,河南区域是其首要的防御目标,亦是中央政权重要的防务基地。第二,对于试图入关取天下的关东势力,河南是其进攻的首要目标。刘邦与项羽分兵后,首先试图由荥阳而攻巩、洛,不胜而被迫南走颍川、南阳,其间,还北上孟津烧绝河津,破坏赵将司马卬南渡黄河,可见,刘邦自己将河南视为攻取关中的首要通道,自己力量尚不足攻占时也不让其他势力染指这一地区;项羽河北大捷后西入关中,径直奔河南而来,一举入关,迫使刘邦卑躬屈膝赴宴鸿门;英布起兵反汉,薛公认为英布如果“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吴楚七国之乱,吴少将桓将军劝吴王疾驰入洛阳,据武库、敖仓,则“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武帝时刘安谋反,亦以“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为取胜之策。如此众多的军事谋划、实践无一例外地说明,关东势力只要进占河南,就能把握住关中中央政权之命门,既占据了有利的军事地理形势,还能“示天下以形势”,制造出舆论影响,因为洛阳的归属本身就是关中中央政权是否完整的标志。一旦河南区域失陷,关中便无险可守。第三,在关东与关中势力相对平衡之时,占据河南区域的军事力量的政治态度,对双方的力量对比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吕后死后,齐王刘襄以讨伐诸吕为名起兵杀奔长安,灌婴在荥阳的军队既东阻刘襄进兵关中,又西制关中诸吕,使其不敢轻易妄动,很好地策应了周勃等人在长安的行动。新莽末年,王莽派驻洛阳的大军在昆阳为绿林军聚歼,新莽便大势已去;更始都关中,刘秀自河北攻朱鲔于洛阳,朱鲔降刘秀后,不但更始帝失掉左右臂膀,刘秀之帝业,亦从此定下。
再次,河南“天下之中”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水陆交通体系,决定了作为交通枢纽的河洛地区,对行军及运输有重要的意义。河南是秦汉时期国内通达力最强的交通枢纽:东至齐鲁,有黄河、济水可利用;西至关中,豫西通道是最便捷的出入关中之路;北上赵、代,南下吴、楚,是先秦以来的南北大道(略与今京广铁路、焦柳铁路同向),并可利用汝水、淮水等河流。陆路交通,河洛地区是关东与关中出入的瓶颈,是关中军队是否能够顺利出兵的关键,“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即是此谓。水路交通,黄河、济水、鸿沟等汇集于荥阳,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和转运中心。如前所述,关中地区每年要从黄淮地区漕运大量的粮食,荥阳则是漕运的中转站,战时谁控制了这一地区,不但能就近使用敖仓中的大量存粮,还控制住了关中粮食供给的节点,特别是对关东势力而言,控制住了河南,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切断关中地区的粮草供应,大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势。
最后,从自然地理上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雒”,河南是一个典型的四塞之地,拥有多处可以凭险据守的关隘和城池。在秦代至西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常被人为地划分为关中与关东两区域,这一时期,关中被作为国内最重要的核心区,而关东则有广阔的土地和物产,往往能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或能与中央抗衡。关中的中央政府要维护国家统一,关东的地方势力觊觎长安的皇位,二者的冲突是长期存在的,在二者势力结合部的河南,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占据之后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兼之其在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军事后勤上都有特殊的可资利用的条件,自然成为国内冲突中的焦点。论者评价:“在战国、秦、西汉时期,洛阳虽然不是都城所在地,但一直是政治、军事、经济重镇,称得上是关系天下安危的枢纽所在,其地位之特殊,远非一般区域性名城大邑所可比拟。”⑱
三、京畿要地:东汉河南军事作用的增强
东汉时期,洛阳成了帝都,河南成了京畿要地。东汉定都洛阳的战略选择,从对外战争的方面看,是较为成功的。洛阳因其先天的地理优势,远离边境地区,不容易遭受到边地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直接攻击。洛阳位居四塞之地,缓急之时尚有可依靠的天险如黄河、函谷可守,没有出现西汉时期长安随时处于匈奴骑兵一日一夜可到达之危险境地,即使在汉羌战争中出现过敌军威胁洛阳的局面,也能依险据守并在很短时间内(从朱宠设防孟津到任尚击破羌军于上党,不过两个月)清除深入之羌军,事后又能不断增加外围的军事力量,羌人深入之范围,一次比一次小,国都安全基本无虞。
从政治地位和军事价值看,东汉时期的河南是首都所在之地,远较秦至西汉时期战略地位高。军事地理学中将一国的政治中心作为当然的战略要地,首都是国家的象征之一,首都不仅在政治上是国家的中心,在军事上亦受到重点的防御。一旦首都受到威胁,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⑲东汉时期的河南虽不是国内战争中的攻防枢纽,却是首要防区。
到东汉末年,随着黄巾起义爆发,洛阳地区再次成为国内冲突的焦点。先是洛阳周边的南阳、颍川成了政府军与黄巾军的主战场,灵帝设洛阳八关,以护卫首都安全。以后董卓进京把持朝政,关东地区联军讨卓,董卓见关东军阀声势浩大,急忙迁都长安,而孙坚、朱儁等人先后在洛阳附近与董卓混战。但不久,曹操劫持东归的汉献帝迁都许,洛阳附近地区因被董卓焚毁,再以后,关东军阀混战,国内的主要矛盾冲突,先是曹操与袁绍之间,后是曹操与刘备、孙权间,虽然关西的军阀如韩遂、马超等先后试图挑战曹操,但都以失败告终,可见这时国内的主要斗争已是关东军阀内部的冲突了,关西地方,已不足以影响天下大局了。这之后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对峙形势主要表现为南北对立,魏蜀的对峙前线在汉中、祁山,魏吴间的核心冲突区域已在淮南一带,河南地区便远离烽烟了。
注释
①②王恩涌主编《政治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9页。③《史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87页。④《史记》卷六五《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6页。⑤《史记》“嚣”作“隞”,《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均作“嚣”。参阅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228—233页。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第700—715页。⑥《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942页。⑦《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2—3263页。⑧刘家和:《说洛阳为“天下之中”》,《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⑨《汉书》卷四三《娄敬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19、2120页。⑩《汉书》卷七五《翼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8页。⑪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⑫《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诸先生补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115页。⑬《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3209 页。⑭《史记》卷九三《韩信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3页。⑮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⑯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⑰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页。⑱孙家洲、贾希良:《不为都畿,亦为重地——论洛阳在战国、秦、西汉时期的特殊地位》,《历史教学》1995年第3期。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主编《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军事地理学分册》“战略要点”条,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K232
A
1003—0751(2011)03—0191—04
2011—02—10
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中原经济区”在中国历史上战略地位研究》(2010BS062)。
杨丽,女,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1)。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