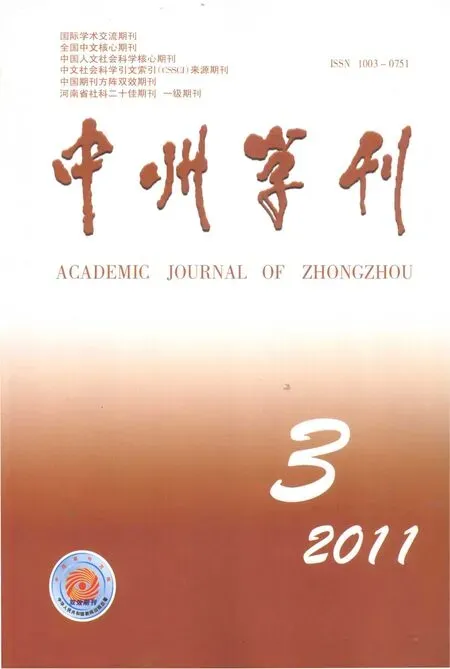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一个中心”与“三种主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出发
刘 威
“一个中心”与“三种主义”*
——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出发
刘 威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支配下,中国社工界在一种西方与本土的二元对立语境中设想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亦在西方先进与本土落后的两相对比中表达与国际接轨的愿景,更是在现代专业标准与传统助人惯习的优胜劣汰中择定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行业标准。中国社会工作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多种助人系统并存的悖论实际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接、矛盾和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化”。只有坚持实践本位,在选择、融合与超越之中突破“一个中心”和“三种主义”的桎梏,才能避免抽象理念化和意识形态化建构的误导,真正建立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并具有鲜明自主性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
本土化;现代性;西方中心;专业至上;本土资源
现今是一个“化”的时代。在西方专业取向和本土资源取向针锋相对的话语导向下,作为一种科学助人的职业和专业,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汇入这一“化”的历史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工服务队伍迅速壮大,专业教育蓬勃发展,西方理论陆续译介。在此背景之下,一个由政府推动的社工共同体正在形成。时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已相当强盛,但蓬勃发展的表象无法掩饰如下事实:流行于中国社工界的核心概念、基本假设、实务方法大多源于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提出的。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社会工作的强势,更暴露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①所有的话语表达或遗忘自我,或盲从西方,或固步自封。正因如此,本文试图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本土资源取向和西方专业取向的对立格局之外,寻找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三条道路”。
一、“一个中心”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代性隐喻
站在本土立场审视本土化的过程,我们发现,社工本土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拿来主义,它在文化碰撞、调适与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西方—本土、现代—传统的双向互动关系。社工本土化的初衷意在借鉴西方社工理论和实践的先进经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并且本土化概念的原始意义也在突出本土社会的主体位置之余,强调社工“西学东渐”的适应性调整和转型。据此,不少学者乐观地以为,社工本土化是外来社工同本土社工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和进程与二者之间的亲和性②有关。
然而,如果进一步挖掘社工本土化的隐含前提,不难发现,上述如此丰富且一厢情愿的理论推演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其一,认为西方社工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经验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借鉴意义,中国社工的发展趋势将与之接轨,因而必须在中国施行西方先进的社工理念和模式,以推动中国社工的建设与发展;其二,认为专业社工虽然基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基础,但与中国文化具有相融性和通约性,故在呼吁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时,仍驻足于这些优良传统与西方社工价值理念的相通和对接③。所以,尽管因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专业成长的使命,中国社工界适时提出了本土化的问题及初步设想,但其主张实质上都建立在对西方社工理念认同的基础之上,希冀以西方为参照来重构中国社工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构想仍是基于西方中心的思维。放眼中国社工发展的现实情形,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这种固定而僵化的思维方式已经生长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如果我们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投入一种深度的现代性眼光,那么,无论是西方与本土的非此即彼,还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以及这种二元格局所呈现的思维定势,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生长和移植过程中的常态。一方面,现代性内在地预设了社会工作二元对立的分裂特质。社会工作诞生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它在现代对传统的激烈反叛中,辅助解决由现代性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福利谱系,现代性的延续亦借助社会工作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以温情脉脉的话语和专业权威的姿态关涉现代性主题中的个体与自由,试图运用现代性的“对象化”思维和“甜蜜理性”解决现代性问题。社会工作在自身的专业知识里构筑自身的案主和关于案主的话语体系,使案主被人类自我意识作为“人”而成为“他人”④。在现代性标定的正常与越轨、自我与他者、同类与异端的二元对立之中,社会工作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彼此不同而又分门别类的案主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案主是整个现代性的客体化和对象化,而社会工作指涉案主、围绕案主、服务案主的过程不过是利用案主而显示自身,在“助人之时束缚人”⑤。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是案主,而是所有人都在对于案主的限定中定义了自身。
总之,社会工作是现代性的一个隐喻。现代性通过现代向传统的挥手作别而宣告了社会工作的诞生,并且通过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他人”来“制造案主”。因而,社会工作不仅是社会的对象化,而且是人的对象化。在现代性的生长、扩张和危机中,社会工作内在地养成了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正常与越轨的二元对立品格。正是从这个角度,社会工作因其对现代性的内在皈依而构筑了自身的专业知识,亦不可避免地构筑了自我的生存困境。
在现代性语境中,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性的移植和散布过程,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正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来界定的。同样的,现代性的界定所依赖的是它的对立面——传统性和非主流性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浸染之下,本土化演变为对西方社工理论架构的操作化。我们不由自主地在一种西方与本土的二元对立语境中设想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亦在西方先进与本土落后的两相对比中表达与国际接轨的愿景,更是在现代专业标准与传统助人惯习的优胜劣汰中择定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行业标准。我们在弱势群体权利频频受损而毫无话语权的当下,却强调个体主义取向的案主自觉原则;在总体社会急剧紧张而亟待结构性调整的时候,却倡导专业技术取向的微观个案工作;在社会公众尚未充分认识和接纳社会工作的形势下,却追求过度的专业规范标准和过高的职业准入门槛;在社会矛盾爆发而急需社会工作介入的关口,却鲜见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踪影和运作空间。在中西并存的悖论实际中,中国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国情”就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但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却迫使我们不得不斩断与传统救助方法的内在联系,在学习、模仿和接轨的过程中,促成传统社会救助向现代社会工作的顺利转型,亦即用西方社会工作的“洋玩意”“化”本土社会救助的“土办法”。
纵观历史,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基于此,我们要在一种悖论情境中认识中国,厘清传统与现代社会并存和相互作用、卡里斯玛与现代理性并立和彼此影响、身份关系与契约制度并置和互相嵌入等悖论现象。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凭借以西方为中心的社工价值理念和实践模式,来理解一个长期在多元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下的社会及其面临的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一些实务人员或用“家庭结构疗法”来帮助家庭功能失调的矛盾夫妇,或用“认知行为疗法”来帮助社会功能紊乱的失足青年,或用“社会学习疗法”来帮助沟通交往困难的问题儿童,给予我们的只是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的感觉。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工作最突出的问题不在于单向的整合和趋同,不是单向的“化”,而是如何面对多种系统并存的悖论实际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接、矛盾和互动。着眼历史和现实,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西方社会工作与本土助人方法的融合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要超越西方中心的思维和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
二、“三种主义”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习惯性误识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社工界养成了三种本土化的习惯思维。我们在专业与业余的互为比较之中自觉选择了专业至上主义,为此,我们积极引进各种专业理论和实务技巧,却对本土性社会工作的传统价值置若罔闻;我们在西方进步与本土落后的优胜劣汰之中盲目偏向于西方中心主义,为此,我们积极在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契合专业社会工作的现代因子去与西方对接、呼应;我们在政府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之中构筑起社会中心主义,为此,我们迷恋社工机构民间化、社工运作社会化、社工助人志愿化的图景,却未曾认真评估政府的天然职责和历史作用。
1.专业至上主义与社会工作的殖民化
自中国恢复社工专业教育以来,从最初引入西方专业社工理论方法,重建社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到最近社工教育体系迅速扩张,各地纷纷筹建社工职业资格和注册制度,已经跨越2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阶段,专业化构成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线索。中国社工界在推进本土化的进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迷信专业、崇尚专业的“专业至上主义”倾向。专业至上主义是以专业建成作为本土化的终极价值信仰及其行动者的根本准则的,并不顾及社会发展和专业养成的阶段性特征⑧。在专业至上主义的内力驱使之下,社工研究者们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引进各种专业理论和实务技巧,统编各类专业教材和参考资料。但是,在研究领域,卷帙浩繁的各种社工书籍对西方专业知识和实务技巧津津乐道,却鲜有专门探讨本土性社工和社工本土化的;在理论层面,汗牛充栋的各类社工理论不约而同地“舶来”自西方、港台,却罕见本土助人手段方法被提炼、理论化的;在教育领域,西方地道的社工理论和实务方法垄断了高等教育课堂,却被专业学生束之高阁而无用武之地;在实务领域,超常规发展的社工专业教育培养了大量科班出身的社工师,却客观上既难以补充进入福利机构,主观上又极不愿意进入福利机构。
事实上,在我们移植、崇尚和迷信专业之时,西方社会内部早已开始反思专业主义的功过是非。20世纪3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为专业团体逐渐提供了相应的合法性地位和权利,专业团体亦给福利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建设性意见和科学化战略。专业化过程呈现的是专业群体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依附于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从而分享权力和利益。专业社工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吁求中发芽生根,在问题丛生的社会语境中走向前台,在矛盾重重的国家治理中不断拓展。它怀着提供服务、解决问题、助人自助的崇高理想,在辅助国家建设、促进良性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凭借专业操作、业内督导和同行评估,争取自身的专业地位、权威和利益⑨。专业社工以专门知识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和形象,却树起了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天然屏障。目前,极端专业化的弊端日益显现,诸如侵害案主利益、忽视服务效率、只对上级督导负责而不顾公众和服务对象等,已经引起学界反思。
从现代性角度来说,专业至上主义对社会工作的自我殖民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当前社工界受到文化殖民霸权的侵蚀和西方中心思维的驱使,对西方专业社工一味迎合而缺少应有的反思批判态度,对本土助人方法熟视无睹而误以为“拿来”西方社工就等同于社工本土化了,甚至用西方专业社工“化”本土助人方法,根本忽视了异族文化之间的“水土不服”,从而使中国社工发展具有强烈的“自我殖民化”色彩。
2.本土资源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内卷化
在中国社工界,专业至上主义者奉西方社工理论和实务经验为圭臬,反而将本土助人方法视为“他者”和反面对照。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中国仅仅是一个边缘性陪衬和被动接受者。这类倾向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拥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这一思路的极端化激起了相反的主张,即本土资源主义倾向。本土资源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价值和助人文化具有可供开发利用的丰富资源,并且这些本土性助人资源与社工专业价值观具有相通和兼容之处。基于此,在本土化过程中,为了在工作模式、实务方法与技巧层面上增强本土助人方法与现代专业社工的亲和程度,必须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的积极因素。唯如此,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专业社会工作方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其本质而言,本土资源主义在中西二元框架中从一个极端滑落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不同意对中国助人文化“另眼相看”,相反主张中西助人文化“一脉相承”。这是社工本土化的又一明显误识。
本土资源主义有三种表现:其一,“平等”的对接态度。孙立亚、王春霞、倪勇等强调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社工价值的某些等同或近似之处,尤其是传统家国理想、民本思想、孝道观念、仁爱品质等积极因素与社工价值观十分一致,可以作为现代社工的思想动力和伦理基础而被运用到操作过程之中。其二,“自主”的调适取向。王思斌、易钢、田毅鹏等认为本土文化的优良因子可以调适和改变西方社工理念及其价值观。郭伟和甚至指出,先秦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伦理、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西方发达的社工价值理念,可作为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基本构件。其三,“理性”的诠释姿态。还有一些学者将西方社工理论模型和实务经验运用到处理本土案主问题之中,并且利用中国本土的经验案例来诠释和印证西方社工理论和技术的普适性和合法性。无论是接轨心态、调适取向,还是诠释姿态,它们都是建基于对西方社工理念的无条件认同之上,理所当然地将西方视作价值标准和参照框架,强调西方社工价值理念与哲学基础的普适性和借鉴意义。
如果总结和提炼社工本土理论和思想资源是为了迎合西方社工范式,那么这种总结和提炼就仅仅是一种知识的重复生产和数量的简单累积,它不但无助于社工本土化,而且还会导致社工发展的内卷化,出现一种“有数量”而“无质量”、“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目前国内社工研究在传统助人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仍然流于经验性总结而缺乏学术性反思和理论化提炼。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对西方社工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反思,勇于批评其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与文化殖民主义影响。与此同时,应尝试依据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和工作经验,提出超越西方假设的中国社工理论。进而,中国需要经历一个“范式转移”过程,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来重构社会工作的运用原则和操作理念。只有在这一理想目标的引领下,才有可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客观地探讨社会工作的西方价值基础的局限性,并切实地带着批判和理解的眼光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⑩。此外,社工本土化亦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实务来诠释和印证西方的社工理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用中国的现实和案例来证伪国外的相关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工理论,避免理论和实务的断层。
3.社会中心主义与社会工作的民粹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公民社会何以必需、何以可能”的问题,各界展开了持续论争,对公民社会的理念和经验之于当代中国的适切性已基本达成共识,公民社会也越来越被视为开启新一轮“和谐”、“民主”之门的密钥。对社工发展目标和路径等问题的思考也汇入这一“社会共识”之中,流露出对公民自由的绝对遵从、公民权利的绝对尊重、公民参与的绝对倚赖,并对“志愿化社工”、“民间化社工”、“机构化社工”的未来走向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众多研究总结了中国社工发展具有行政权力主导、公众认同式微、社会参与淡漠等特点,分析了阻碍社工进一步发展的文化与制度性因素等,提出构建现代社工的价值基础和实务体系、完善社工行业准入和执业资格制度、培育社工人才队伍和就业机会等政策性建议⑪。
从社会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看,当代中国涉及社工救助的思考基本是循着以下思路隐性展开的:在对公民社会怀揣美好期待、认定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个“好东西”的价值预设以及社会工作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只能由社会来办的理论预设的前提下,对社工发展的公民社会基础加以清理,然后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境遇下审视“‘社工社会化’究竟何以必需”的问题,最后对中国“‘社工社会化’何以可能”做出详尽的解答,并努力寻求并择定一款适合中国社会的“社工社会化”模式。当然,这样的逻辑很少在公众讨论的文本和话语中显现,但却以种种“心照不宣”的方式潜在地引导着思考社工本土化的思维逻辑。
笔者认为,在上述这些思考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思维定势,即社工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只能由“社会”承办,对市民社会、公民精神、志愿参与的信赖使“社会”被无限放大。反过来,政府主导被视为社工发展水平低、社工组织缺乏公信力、专业社工尚无用武之地的体制性根源。从社工现存问题及困境的性质、类型和特征来看,社会中心主义者在寻找原因和追究责任之时,都不约而同地树起“政府主导”的靶子,大家“群起而攻之”,似乎只有“政府退出、民间主导、公民参与”才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唯一出路。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国家的强势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才能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社会工作才走出了一条“低社会参与下的高效发展”之路。这一高效发展模式利用特定的组织机制和政府的强势动员,敦促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实施助人活动和志愿服务。一方面,现有民政工作体系延续了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依靠党和政府的威信以及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吸引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形式具有巨大的刚性处理问题和集中汲取资源的能力,从而比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社工组织或机构具有更强的组织动员与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这在历次突发灾难的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三、“实践本位”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自主性实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不应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类型转变成另一个类型,而应认作是一种持久的并存、拉锯和互动以及生产新型模式的混合。“正是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悖论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化、理念化、绝对化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实践过程本身。”⑫我们需要从悖论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框架和实务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社工本土化的实践内核,就是现代性话语的生成与“非现代性的发现”这一交互强化过程。所以,如何在选择、融合和超越之中,突破“一个中心”和“三种主义”的桎梏,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和实践本位的社工自主性,成为一个应时而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不能坚持“以一种理论推翻另一种理论”、“以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以一种主义压倒另一种主义”,亦不能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感性情绪的宣泄。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悖论现象和实践过程,理解和解释社工发展的矛盾逻辑,关注社工发展之中的悖论元素如何共存、并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在此,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颇具启发意义:他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要求探索实践的逻辑,由此提炼出崭新的解释模式和理论方法。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和意识形态化建构的误导,真正建立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并具有鲜明自主性的社工本土化模式。
1.用“反思”引导发展,以“反思性实践”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本土化
反思性被视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内核和实践品质。回望西方社工专业的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它也曾受到工具理性主义、极端专业主义、治疗目标主义等倾向的长期困扰。正是在一种回应社会需要和响应民众呼声的反思性实践中,西方社工在助人过程中认真检视自身的专业使命和职业轨迹,重新回归社工追求人类公平和正义目标的主题。在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处境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穷尽一切领域并回应和解决所有社会难题。相反,每一个理论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脉络、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特定的问题⑬。因此,培育反思性实践特质,是社工专业跨越文化隔阂和国族边界、超越理论局限和视角藩篱的必要之举。具体而言,在“拿来”西方社工理论和方法而本土“化”之时,强调批判性吸收和选择性借鉴;在提炼本土助人传统和方法而专业“化”之时,强调自主性表达和创造性思考;在理顺社工的政社互动关系而社会“化”之时,强调政府责任担当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机统一。
面对流派复杂和种类纷繁的理论范式和实务模式,中国社会工作要在理论移植和经验借鉴中不失自我品性,在服务提供和问题解决中提升自身品位,关键在于坚持反思性实践和实践性反思的统一。无论是争议颇多的心理动力理论、认知行为理论、危机干预理论、叙事治疗理论,还是局限明显的生态视角、灵性视角、赋权视角和优势视角,都是在不断的反思性实践中成长丰富起来的,也是在持续的实践性反思中发展完善起来的。现实和问题总是杂乱无章的,社会工作者和案主身处的环境并不能以固有理论所期望的方式呈现,因而强调实践中反思和反思中实践就成为社工助人活动的重要准则,所有的社会工作者都应成为生活真知、理论反思的主动实践者,而非经验指引或理论支配的被动执行者。
2.让专业回归“生活”,以“生活性实践”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本土化
笔者反思和清理专业主义倾向,并不是一概否定专业知识的作用和专业服务的效果,也不是完全无视专业人员的权威和专业职业的特性。然而,笔者确实反对专业知识对草根智慧的轻蔑,反对专业权威对弱势案主的操纵,反对专业技术对助人过程的控制。众所周知,专业社会工作原本发端于普通人的日常助人活动,它借助于实证科学和形式逻辑将零散、杂糅的帮扶常识升华为系统、标准的专业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企图将助人行为剥离社会生活场景的专业化尝试都是违反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生长逻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抑或本土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贴近人性的帮助,而不是人为地设置专业藩篱。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抑或本土化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展开,其基本向度乃是朝向真实的个人的。在流变性、风险性、偶然性日益显现的当下社会,标准化、板块化、固定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指标越来越难以适应急剧变动的社会需要和案主需求。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理应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场景中,以一种可被常人理解的方式参与日常生活生产⑭。一方面,通过丰富多元的助人活动把专业知识当做一种生活话语,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体系之中,成为启发和建构崭新生活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压迫和矮化服务对象的专家话语。当专业知识回到生活当中,成为一种常人可以使用的话语时,它才由服务于专业管理的权威工具转变为服务于百姓生活的常人方法。另一方面,社工从业人员应该走出自己的职业围城和专业场景,深入百姓的社区生活、提供自然的生活帮助,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以一种生活性实践对专业知识进行生活化处理。基于此,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社工本土化(专业化)的当务之急不在于设置过高的职业准入门槛和过硬的专业执行准则,而在于深入社会实践生活当中。在社会公众认同式微和难以接纳的情况下,无论是过高的准入门槛还是过度的专业限制,无异于社会工作的自我封闭和束缚。因而,应明确社会工作的职业和位置,让社工专业人员走向社区、学校、医院、福利机构、工青妇群团组织,让他们在实践助人中获得社会性认同,在生活土壤中凝练本土性知识。
3.用“建构”促成融合,以“建构性实践”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本土化
从引进、移植到扎根的三个阶段是社工本土化的必经之路。在此之中,“建构性”是贯穿本土化始终的基本特征,也是决定社会工作能否扎根的深层因素。在移植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迈出了一条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出场路径,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国家利益本位、行政逻辑主导的民政社会工作;个体权利本位、专业逻辑主导的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关系本位、实用逻辑主导的草根社会工作。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制度的建构和转型必须面临三种价值取向的挑战和碰撞。具体而言,政府大力推动的社会工作发展必须优先服务于社会稳定需要和社会建设大局,因而中国社会工作不是直接建立在基于个体利益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之上,而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我们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长期发展,应将政府权力主导、国家利益至上的隐性逻辑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引入分析框架之中⑮。正是在如此不可动摇而又如影随形的隐性逻辑支配之下,我们主张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立场,即专业社工、民政社工和草根社工互相学习、彼此建构的渐进演化。一切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依归,正视差异、相互理解、寻求共同点、加强合作,成为这一渐进性演化的基本原则。⑯坚持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实现三种救助资源的有机融合,既要充分发挥本土的非专业和半专业救助资源的有效作用,又要大力培育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我们还需要三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学者群体和实际工作者的密切配合,避免错位性期待和强制性合作。
注释
①王绍光:《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页。②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③⑩刘华丽:《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再探讨》,《社会》2004年第12期。④⑤惠永照、郭景萍:《社会工作的现代性意义与困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⑥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⑦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⑧卫小将等:《我国社会工作的“绞溢”病象及其诊治的可能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⑨⑭郭伟和:《迈向社会建构性的专业化方向——关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道路的反思》,《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⑪李迎生等:《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⑫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⑬黄耀明:《社会工作理论发展模式及其基本特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⑮马志强:《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⑯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C916
A
1003—0751(2011)03—0120—05
2010—12—02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2009JJD720010);“985工程”创新研究计划项目《都市新社会运动研究:主流理论的局限与中国经验的嵌入》(20101009)。
刘威,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海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