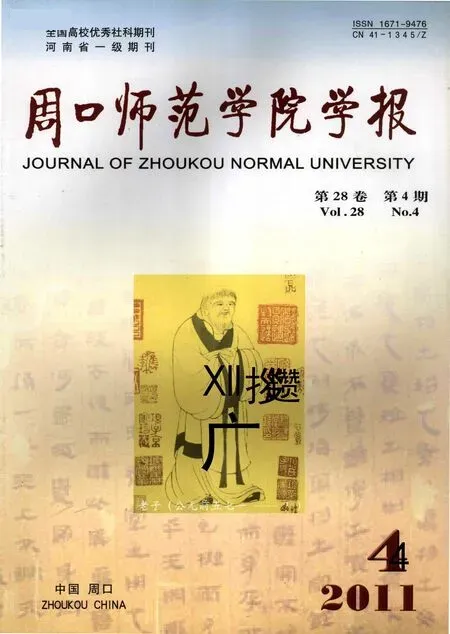民间信仰的圈层体系与村庄社会功能整合——基于豫中沟村的田野调查
刘 涛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15)
一、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缘起及进路
(一)研究缘起及进路
本研究主要缘于农村社会内部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村庄生活趋于私密化,农村公共生活空间逐渐萎缩,农民精神空虚问题明显,以至于村庄内部的低俗文化兴盛。二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制度性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市场对村庄影响增强,农民流动速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原子化村庄”与“无公德”个人增多,农民的合作能力减弱,村落共同体渐趋解体。这两种变化给村庄治理及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有效挖掘村庄内部的民间资源以促进乡村社会的整合,就成为了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在治理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构造的治理模式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尤其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复苏,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
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高度集权体制下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个体化生产方式回归。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了乡土社会的资源再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生产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乡土社会相对多元的生存需求,乡土社会开始寻求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那些被压制的、被国家权力斥责为“迷信”的民间传统被看做是符合生存法则和心理需要的精神传统,通过乡土权威的运作被复兴[1]。研究者意识到,民间信仰“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2],他们通过探讨神庙祭祀组织与基层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及神庙祭祀仪式对不同群体权利、义务关系和村社规则、秩序的表达,来说明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与运行秩序。
民间信仰与宗教有着较大的区别,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3]。它在某些层面和宗教非常接近,实质又不是宗教,民间信仰是与当地的地方性知识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包含着当地农民的生活、生产中的各种习惯、规范,地方性极强。民间信仰的这些特征决定其具有内在的整合功能和地方性特征,这些特点让民间信仰可以接纳更为多元的个体,群体构筑的关系中又存在一个“差序”性质的圈层结构,在不同圈层内部,其功能又存在着形式和实质的差异。
笔者对沟村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对村落内不同的人群研究,发现民间信仰活动对村落社区的凝聚、整合作用不仅仅表现为对权力场域中相互关系的建构或强化,还表现为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仪式、文化活动来传达情感,强化群体记忆,达成群体团结。因此,本文将尝试以沟村的田野经验为基础,从沟村农民信仰的情感整合、文化网络基础构建等功能视角来审视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村庄逻辑,传达出民间信仰与国家“隐喻”的相异层面。
(二)村庄基本概况
在地理位置上,沟村位于河南省中部的嵩山东麓,隶属于新密市,多山地,地势崎岖不平,这与中原的平坦地势差异较大。粮食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矿产资源丰富,当地有较多的小型煤矿企业。沟村是多姓杂居村,宗族基本解体,但是村民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相对较强,大家族内部基本都会续族谱,尤其是“村内的村外人”也相当重视族谱。沟村的历史不是很长,与多数中原村落族谱的记载一样,沟村由明末清初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所构成。
在不同地域的乡村社会中,农民理性化、村庄原子化特征都在逐渐呈现,导致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上难以达成一致,村级治理问题走向恶化,而沟村则与之相反。沟村的文化活动较为频繁,农民在这些互动当中增加了感情;他们能够经常性地交流,传达生活中的感触。这种密切的交往让他们在生产中也能够合作起来,保证基本公共品的供给,村庄内经常自发地组织村内道路与沟渠的维修。沟村村民能够互助的重要原因是村民对“关帝”的信仰,这也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的关键。沟村的民间信仰是如何兴起、发展并且演变至今?其在沟村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对当前乡村发展有着如何的启示?笔者将根据沟村的田野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沟村民间信仰的复苏与圈层结构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民间信仰在历次破除封建迷信及各种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出现复兴的热潮,尤其是90年代后,在民间精英的运作下,借助国家政策的遗留空间,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路径,使乡村庙宇得到复兴,信仰人数有增加的趋势,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
(一)沟村民间信仰复苏与国家治理技术的变迁
村庄的信仰复苏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变动有关,在这个宏观的结构中,个人努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村庄的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刘富春 (1950年生),经历坎坷,略懂中医,能够治病救人,被称为“神婆”。儿时父母就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她自小就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从而成为了虔诚的信徒,据称其“从小就能梦见神奇之事,并且经常变成现实,与神有缘”。她小时家境不好,得重病,一直烧香信佛,祈祷病能痊愈。但是“文革”时期破“四旧”,关公庙内的佛像被砸,国家不允许村民信这些“迷信”的东西,不然就会被批斗。而刘富春在家私自供奉观音被批斗,她说,“其实像我一样的人很多,他们也是私下偷偷供奉,当时让我下跪认错,我又没有犯错,供奉观音是神托梦让我这样做的,我没有犯错,所以我不跪,反对我信神的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也确实如此,批斗我的那个人不久就得病去世”。事情虽较为偶然,但是却坚定了她的信仰,“托梦”也成为她寄托行动的一种程式。为重建关帝庙,刘富春于1994年在家里召集了沟村的多名老人及“信神”者召开关于重建庙宇的会议。刘富春说:“关爷托梦给我说要回这里来住,要我们抓紧修庙,我也不敢耽误时间,不然恐又降灾。”于是大家纷纷响应,筹钱修庙。当时各家都不富裕,主要的资金都是由刘富春筹集。她也把所有积蓄都投到寺庙的修建上。庙修建完后一直风调雨顺,信仰的村民越来越多。
到2009年有2/3的村民开始拜关公、观音等“民间神灵”,临近村的村民也经常在初一、十五来村烧香祈祷。在村民的思想认知中,拜神不仅可以免除灾难,而且有助于疾病的痊愈。由于刘富春略懂中医,所以她有时会给得病不重的人开些中药,她认为“得病也需要吃药,拜神仅是会让病好得快些罢了”。她也为病人举行各种仪式,仪式多是神秘的, “神婆”通过与高层神灵进行对话来为病人驱逐疾病,病人也通过冥想来解除痛苦。这个过程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虽然没有什么奇异的景象,病人却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松弛,她在帮助病人举行驱“病”仪式后,会开一些简单的中药,由此,病人很快好转。这些故事层层传递,成为一种凝聚村民的重要力量,信仰在话语符号中一遍遍传达、规范与重申,家庭、村落到村落之间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网络,民间信仰也成为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慰藉。
在当代民间信仰活动复兴的过程中,各种民间信仰不能被传统官方宗教的分类体系包容时,民众最常见的规避方法之一就是“戴帽子”,即把地方信仰的杂神或各种小庙小祀在形式上纳入已经被国家承认的宗教,如佛教或道教的体系之内,有时还会找一位被认可的主神如“观音”之类供奉,而实际祭祀的则仍是人们心目中认为更灵验的杂神[1]。如沟村关帝庙的侧屋内有着近百位神像,只有这样才能遇到各种事情时都能逢凶化吉、左右逢源。众多的“神灵”承载了人间所有美好的愿望,如治病消灾、祈福禳祸、求子延寿等。在信仰体系上,民间宗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与民俗信奉相融合的多神崇拜体系,这种信仰模式恰好迎合了乡土社会的实用理性需求,唯“灵”论或多神、“全神”的信仰体系,普遍见之于乡村社会。
无论是“托梦”之说,还是对“诸神”的信仰,并不全是“迷信”的再生,而是农民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寻找自身安神立命基础的希冀与诉求,这种诉求与国家治理技术的变动不无相关。分田到户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那些被压制的、被国家权力斥责为“迷信”的民间传统被看做是符合生存法则和心理需要的精神传统,通过乡土权威的运作而复兴。“文革”结束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等宏大的政治话语中,村民的自主意识增强,同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强制性有所缓和,宗教管理政策有所松动,从而为民间信仰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农业税费的取消使乡村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化背景下,农业生产与生活中的风险增多了,农民越来越无助,同时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愈加空虚,难以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归宿,农民价值上的失序为民间信仰的复苏提供了空间。同时,在当前沟村的信仰中,信仰者把当前存在的诸种社会弊病,如官吏腐败、道德沦落等现象编成戏曲进行批评、讽刺,对村庄积极分子的孝道与和睦的典型进行传颂。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村民的要求,有利于维护乡村既有的文化格局,因而容易获得默许与认同,这亦是民间宗教在基层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二)理解沟村民间信仰的圈层结构
在沟村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横向关系上的以民间精英为中心的、富有弹性的“差”,也建立了以“神灵”信仰、祖先崇拜为基础的纵向关系上的刚性等级化的“序”。这种明显的“差序”关系的维系主要依赖与“神灵”的远近关系,使上尊下卑的等级差异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通过圈层内部的伦理规范、奖惩机制等规则来实现。
刘富春年长且有威望,由于她的努力,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协作团体,不仅在庙会的活动中达成一致,而且能够在很多公共事务中合作,以她为中心构成了村庄信仰的圈层结构。刘培养了很多弟子,都是虔诚的信仰者,他们成为活动和仪式中的主要成员。刘敏是其中的骨干,主要的活动都是由她来联络。她称“自从信神以来,自己也经常做梦,神有时在梦里给你指引道路,那么你就会消灾。丈夫以前得重病,难以治愈,后来我虔诚拜佛,现在丈夫的病已基本痊愈”。像刘敏这样的信徒有13人,处于圈层结构的核心,是刘富春亲传的弟子,他们在各种活动中都非常积极,这些精英在信仰的宣传、组织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让这个以民间信仰为主轴编织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不断往外扩散。
处于圈层结构中间位置的是一般的信徒,他们主要是在精英分子的指引下活动,刘富春说“这些人很难被神附身,也不会梦到神,所以他们要虔诚地信佛,只有这样才能消灾避难”。这些人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由此他们多会孝顺老人,帮助弱小。最外围的信仰者则有着多重的想法,他们中有些人认为:“这些事情可能不存在,现在做什么事都不容易,都有风险,去拜拜神,至少心理会好过些!……再说,到底有没有神,谁也说不清楚,万一真的有呢?”这是“人们想从一个未必可知的世界中求得可知世界中不可求得之物的手段”[4]。同时,这些处于圈层外围的人因为在家实在无事可做,参加活动的同时也是为了愉悦精神。他们其中很多人有特长,参加了庙里的文艺队,节庆日庙会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演出,村民都会积极参与其中,活跃了村里的气氛。村里的婚丧嫁娶有时也会请他们去唱戏,尤其是丧葬是必须请他们的,而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用于庙里开支;由于庙里的文化活动开展得较好,周围村庄的村民都会来参加,越来越多的人在合作行动中达成一致。村委有时会借助他们的力量举行一些简单的文化活动,因为民间信仰具有较强整合功能而逐步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这让民间信仰系统得以维系和拓展。
虽然在这个带有“差序”性质的圈层结构内没有费老提出的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内容,但是因为其中充满着对“神”的信仰与敬畏,由此形成了很多有利于村庄共同体维系的积极因素,让长幼有序、邻里互助等横向社会结构及乡村中的“伦常”道德、父子关系也可以维持。这使圈层结构内部人们的关系是人伦的而非实利的,让不断走向原子化的松散村民之间有了新的维系纽带,并在村庄建设中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型塑与村庄功能系统的整合
日常生活是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意义之源,只有把民间信仰、鬼神崇拜置放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才可以发现农民实现“本体性安全”及其生命价值延续的组织形式,可以准确解读背后的“符码”并找到有效的操作性解释框架。
(一)民间信仰的意义延伸与情感整合
1990年以来,沟村的庙宇重建,各种仪式活动开始恢复,在仪式中人们相互传颂着积极的信念,孝亲顺长的价值取向及鬼神观念在祭祀、修谱活动以及丧葬仪式中都有体现。这种价值取向也让村民在短暂的生命中重新找回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让活着的人可以相互尊重与帮助,逝去的人可以与子孙以精神、“梦”相互沟通,避免灾难的发生,子孙通过各种仪式与祭祀保证逝者佑护他们的生活。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找寻安身立命的基础,村民们相信人只有尊老爱幼、相互扶助才能生活得美好,才可以得到神灵的佑护,不至于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玩偶。
庙里的活动较为经常,有定期的仪式活动,村民每天都会烧香,生病的时候也会去刘富春家里请教,这种信仰已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香火、佛像、对联等一系列元素都成了与神相联系的符号,在全村村民集体参加的仪式上,人们共同的心境和注意力的节奏性同步将会让这些平日里常见的文化符号唤醒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村民相互尊重,相互珍视。尤其是在丧礼中,村民必须要请庙里来举行仪式,祈祷老人在地下能够安眠。唱戏班所传达的符号让大家庭成员体验到宗教般的神圣,感觉到家族的团结,人们的生活也会充满着能量和激情,不断地在往复循环的时空中凸显着集体氛围的重要性,进而将这种集体感融入文化符号并铭刻到记忆之中。
沟村村民对祖先的崇拜与敬畏让成年的村民对村庄、对集体充满了认同与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共同体中甘心付出,承担责任。这不能简单认为是信仰的复苏与历史压抑的重返,而更像是列纳德所揭示的“庙宇的再生不只是传统主义者对政治腐化、社会衰变及道德衰败所做出的反抗;更是从历史记忆中汲取的表达新价值观的创造及其对现在的言说”[5]。换言之,这种价值取向所体现的权威感和道德正义感并不仅是传统的复苏、历史的记忆,也是对改变的认可和对一种美好生活的渴望。在现实与渴望中,以神灵信仰强化了彼此的感情依恋与村庄认同,共同的信仰与祭祀、丧礼等系列活动使得村庄成员的集体情感不断凝聚,社会关联不断增强。这种信仰不仅让村民的记忆链条得以延伸,村民的历史感增强,同时也对村庄的认同及其地方感强化,让日益疏离的集体主义回归,人们对村庄生活的预期更为长远。人们对未知的神灵的敬畏,让村民害怕被由信仰构建的团体抛弃,村庄舆论也在这种结构中重新发挥作用,不孝顺老人的村民会被排斥,遭到排斥的后果就是自己难以再参加集体活动,会给自己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更为可怕的是有被神灵惩罚的危险。
沟村的民间信仰底蕴深厚,且有精英分子的积极宣传,构成了较为坚实的情感机制。情感机制中包含的认同、排斥内容承担着国家退出后的整合作用,村庄内部虽然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下降,但是民间信仰赋予了村庄很强的道德力量、公共权威,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动员能力,这保证了村庄内部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
(二)村庄社会“文化网络关系”的重构及其功能
这种“民间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反映的是社会底层百姓的思想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下层百姓的利益诉求。诸如民间宗教经常采取为人治病的模式,提倡教友之间互相帮忙、有福共享、有难共当的观念,这可以为他们提供暂时的避风港。民间信仰倡导的这些理念在整合分散的小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让农民的生产、生活具备了社会心理基础。
传统的乡村社会虽然皇权不下县,但是国家通过地方士绅来治理乡村,并且以仪式构建的权威来威慑民间,基层社会通过对帝国信仰的复制,生成了民间的各种神灵信仰,通过文化与政治上的双重效果编织成有利于乡村发展的“权力文化网络关系”,民间信仰也成为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纽带。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对民间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庙宇被毁,民间宗教活动更是被明令禁止。随着中国踏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轨道上,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乡村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关系”解体,国家通过党的政治权威和组织体系,以革命伦理来建设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农村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高度集权体制下的生产方式解体,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个体化生产方式回归,基层社会的去组织化现象明显。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交换、理性化等原则日益削弱着党所建设的新道德,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又极力催生乡村构建新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社会文化基础。
不断兴起的民间信仰究竟是对旧传统的回复还是新文化的重生?沟村的民间信仰复苏证明这些并不是传统仪式的重复,而是同当下的社会秩序与状态紧密结合构成的新的生存价值观,并为改变沟村的社会面貌和持续地提供社会控制的新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村庄公共生活中人们的预期更为长远,合作能力更强。沟村在村外工作的“第三种力量”①在村庄治理中,存在着明显的两种力量。第一种是来自国家的,这种力量在人民公社时期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力量;第二种是源于村庄自身的,在推行村民自治后,这种力量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其实,除这两种力量外,还有一种力量易于被人们所忽视,即村里出去的,在外面出人头地的能人(村民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切,他们构成了村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也经常回村参加庙里举行的仪式,以求得家庭的平安,他们也因为心系村庄而时常投资于村庄公益事业。尤其是涉及村庄的道路修建等公共事务,处于信仰结构中心位置的精英就会积极动员村民筹资,让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得以开展,他们不断从村庄外部吸取资源,增强村庄的凝聚力。村里的“第三种力量”凭借着历史经验来确认他们拥有当地的身份,并通过这些表征来诠释本地共同体的含义。
四、结论
取消农业税以来,随着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和治理能力的下降,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公共品供给等矛盾日益凸显,乡村治理出现了新的问题。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乡村消费主义的逻辑盛行,村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感,曾经温馨的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当乡村社会被快速地纳入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时,其在文化、经济与政治基础上又难以与之相适应,分散的农民缺少整合的力量导致乡村社会走向了衰败,而诸如民间信仰等内生的力量可以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的整合功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抑制民间信仰中的不合理元素,有效利用民间信仰中的情感濡化、文化整合功能等合理成分,增强村民之间的友情、亲情等情谊感觉,重建和强化村庄的公共性,培养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公共精神,是现代国家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1]王志清.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J].吉首大学学报,2008(2):79-83.
[2]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87.
[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2-313.
[5]Leonard,Pamela.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a Sichuan Village[M].England: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