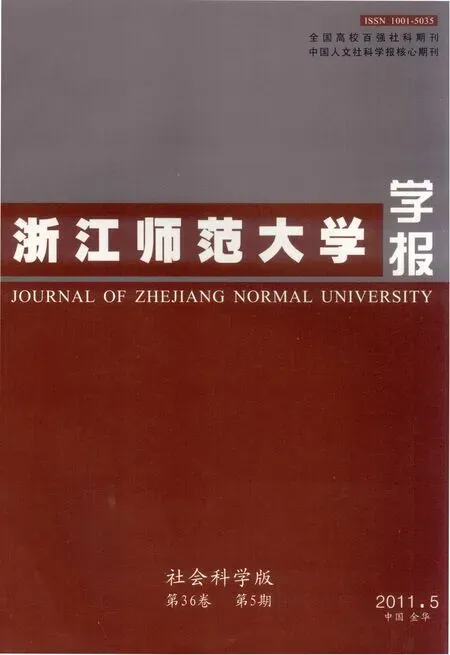办刊实践与品格凝练:以《文讯》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廖 斌
(武夷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优秀杂志都有“文化身份”或“品格”,它们作为精神产品,肩负传播、弘扬文化的重任,在实践中因办刊宗旨的逐步落实,慢慢凝练出特色和风格。资深编辑、文评家林建法说:“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以后,我想到了一个杂志的‘文化身份’问题。现在大家比较多关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实一个杂志也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个身份决定了杂志以什么样的姿态置身于文学活动之中,以什么样的学术理想参与学术生态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以及这个杂志作为中介如何来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以此观之,杂志应当承担的引领作用远远没有能够发挥好。”[1]纵观文学期刊史,1930 年代“海派”期刊小报的市民文化;台湾《中外文学》、《现代文学》的“同仁”、“学院”性质;“潜在写作”而赋予的“民间”属性;《收获》等所标举的“纯文学”、“审美性”而获得的高雅、精致文化的赞誉;新中国《文艺报》、《人民文学》居于文学场域顶层,统领全国文艺生产而获得的政治权威属性等,都是文化品格的表现。本质说,期刊编辑过程即作者的文化创造、编者的文化选择及读者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作者、编者、读者的关系即文化制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面对全球化浪潮、市场利益驱动与大众文化冲击,只有传承优质文化,打造良好品格,塑造独特风格,才能吸引读者文化视线,突显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魅力,这是期刊最根本的定位。
一
《文讯》由国民党文工会创办于1983年,是“近20年来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对两岸文学交流及台湾文坛的良性发展有重要作用,期间历经威权体制到多元开放、合并到独立、党办到民营的艰辛,忝为世界华文学界重镇。它的发展浓缩了台湾文学传媒的嬗递和当代文学筚路蓝缕的拼搏历程。办刊28年,型塑清新的形象,凝练出匡扶时弊、感时忧国、入世济世、敬重人伦、重情信义、助人为乐、担当道义、勇挑责任、和谐为贵的文化品格;学术上兼容并包,体现出“老中青皆尊,各流派并重”,[2]重道德教化,重教育、文学的群治,倡文运,重视文学与整个社会的互动等多面向。作为台湾文坛最重要的杂志之一,2003年国民党宣布停止经费挹注时,“文讯震撼”数见于报章,咸谓台湾社会价值抉择的一个课题,学者陈芳明指出:“《文讯》所放射出的意义,所代表的理想,不但属于国民党,也属于整个社会,撑起了台湾社会的文化象征,这样说,绝无丝毫夸张。”[3]因此,《文讯》蔚为台湾高文化品格的期刊。
期刊编辑学有“编者运作理论”(editor-operation theory),与“读者接受理论”呈辩证关系。理论上说,杂志和市场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读者接受程度越高,杂志越受欢迎,出版行销越好,但这只是市场表相。深层看,还存在转换者机制(transmitter mechanism)问题,亦即被动的读者之所以接受某种期刊、某类作品,其实来自出版者(包括杂志及副刊编辑)的“鼓励”。所以,《文讯》后面隐藏的“编辑群体”实际上赋予了刊物以活泼泼的生命力,期刊就是一个生命综合体,融汇编辑和主事者的思想情感、光荣梦想、文化心理乃至世界观、价值观,这些要素,反之又对《文讯》的品牌铸造、文化实力与品格塑造居功至伟。一句话,刊物的品格是编辑思想传承、精神文化、个性理念、兴趣爱好、人格意志的外化,编辑是活跃而稳定的决定因素,他们在文学与文化建设上扮演启蒙者、引领者、范导者、薪传者,对台湾文坛融入深厚的人文关怀。
首先,从编辑宗旨看,《文讯》确立文化品格的第一面向:为文学立命,为文学而文学,拯救文学于困厄的深厚情怀。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文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念为文学掌灯,它的惨淡经营、默默坚守、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的执着,自有悲壮动人的一面,更催生文学人发愤图强的信念。封德屏总编辑说:“不可否认,经营的辛苦,让我们有时不免涌现一种心酸凄凉。在文学阅读式微的今天,‘独立自主’谈何容易!为了这些可爱、可敬的作家,为了支持《文讯》屡渡险滩的众多前辈、好友,我们许了诺、发了愿,也必将努力去实现。”[4]这段话正是艰苦创业历程的真实写照。台湾是“全世界杂志竞争最激烈的地区”,[5]“有发展趋于成熟的杂志出版业,每年超过40 000种新书上市,出版近5 000种杂志;加上进口的外文杂志,总品项超过9 000种,是一个活泼而热闹的杂志社会,更是一个竞争激烈且成熟拥挤的商业市场。……几乎只要有一种社会兴趣的存在,就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杂志类型”,[6]“到1997 年,台湾注册杂志有5 600 种”,[7]其数量十分惊人。在种类分布上,财经类以超过第二位数百种的优势稳居首位,其后是教育文化类、宗教类、社会类。政论类杂志影响下降,党外杂志风光不再,纯文艺类杂志数量骤减,副刊渐趋八卦娱乐化,博客、论坛及休闲杂志成为阅读新宠,台湾的杂志业进入白热化竞争。向阳指出:“这十年来,文学杂志不增反缩,文学出版社更是备受市场打击,大型连锁书店每月提供的所谓‘文学类排行榜’成为对文学最无情的嘲讽和最可悲的笑话,‘纯文学’已停,‘大地’不在,‘洪范’、‘尔雅’余音袅袅,‘九歌’易调,七○年代的‘五小’盛景日薄。我们看到的,《联合文学》、《中外文学》、《文学台湾》等纯文学杂志艰难苦撑,继续前进,而历史悠久的《台湾文艺》最近又传出面临停刊的讯息,显然,文学杂志并未因为副刊走向大众化而开拓岀更大的纯文学阅读市场。”[8]但是《文讯》不管如何艰难,对文学永不放弃。陈昌明教授任职台湾文学馆期间曾想动支5千万元新台币收购《文讯》典藏的图书资料,以充实文学馆。时值2003年,《文讯》处于最困苦时期,但封德屏婉拒这份请求。感佩之余文学馆请《文讯》帮助实施文学专案,虽经费不多,却也有所助益,而《文讯》回报的是精彩丰富的产品,“如《台湾现当代作家评论资料目录》等文学史料,至今都是台湾文学馆引以为傲的成果,对台湾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9]《文讯》民营后,第一年的经费百分之五十依赖募款,而后逐年降低外援比例。2006、2007年外缘只剩下百分之十,2008年开始做到百分百自负盈亏。尽管拮据,缘于为文学立命,《文讯》“不放弃以往对文艺界的服务,继续举办一些能启发文学心灵的有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与市场营利无关,往往是觉得最重要非做不可的”。[10]因此,在经营压力与工作重负下,《文讯》同仁仍披荆斩棘,努力向前,在“艺术的道路时空”(巴赫金语)中,与台湾文学同源同质,同步发展,在众多杂志“屡扑屡起,旋起旋灭”的市场博弈中,以精进勇猛的进取精神、富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尊老爱幼的人伦情愫,超越党派意识形态,团结各方作家学者,凝聚文坛认同,赢得广泛支持称道,被誉为“台湾最宝贵的文化资产”,[11]这是对它为文学写史的褒扬,更是对其坚持为文学、文化立命的礼赞。
其次,从社会责任看,《文讯》展现了为人生而文学,相信文学、文化的社会功用,阐扬文化教化,载道明德的面向,这体现了《文讯》的多元思考。台湾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斗争、论辩随之而来,浮躁的浪潮一袭又一袭打来;功利主义弥漫于政坛、文坛,消费社会蚕食和改变着文学的性质,但“《文讯》却仍能抱朴守一、坚持文学品质、文化本位,坚持多元、包容的立场和宽阔的视野,……无疑是观察台湾社会的心性、定力、精神、气质的重要指标”。[12]夏志清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乃从清末迄今的“感时忧国”,多流露道德使命感和民族意识,耽于社会谴责及人道关怀。《文讯》虽迟至1980年代面世,却赓续“感时忧国”传统,强调文学、文化的社会参与和人道关怀,它在发刊词和“编辑室报告”中屡屡自我期许:
我们希望能在文艺界与社会大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推动文化建设的文艺界,包括作家和读者尽一份棉薄。[13]
执行这一份刊物的编辑,在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上面,特别注意古今的接合以及中外的汇通,凡此种种努力,也无非是以和为尚,导偏于正。[14]
从“人文关怀”栏目也应可具体明白我们的关怀。[15]
在跨世纪之际,我们有信心再起风云;在两岸的变局中,坚守可大可久的人道与人文之关怀;在整个世纪有关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超越并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在独统的激辩中,维持一贯沉稳、清明的唱音……[16]
更着重在文化现实的关切与探索上面,我们希望能掌握文化脉动,参与当前文化的创造与论述之活动,提供文化界一个好的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不断探索文化发展上的台湾经验,提供创造完美“文化中国”理想的基础,更愿藉此呼吁国人增进文化素养,培养艺术趣味,提升生活品质,稳定社会秩序。[17]
28年来,《文讯》以天下为己任,以期刊为“文化公共论域”,从文学跨越到大文化层面,对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建设、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批评锋芒表现得特出而顽强,充分发挥组织、策划和论域发声功能,凝聚大批学者专家研析探究,透过专题策划、文化短评、专题采访、座谈讨论等多种方式,指摘社会积弊,痛批恶质文化,建言文化建设,反省文化体制,有效地将不同声音集结为公共论域的智慧,向当局和文化机构建言献策。基于《文讯》的“亲和力”,众多的文坛人士、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诸如傅佩荣、张双英、林谷芳、张错、董崇选、南方朔、阎振瀛、吕正惠、郑贞铭、龚鹏程、高柏园、蒋震、叶海烟、余玉照、陈慧桦、古蒙仁等都是学界一时之选。他们从不同面向,比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社区文化与文化“生活化”、文化教育与薪传、文化交流与移植、文学与文化建设等,对文化建设、复兴开出了“良方”,在众声喧哗的台湾社会找到可资讨论的空间,他们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增值了《文讯》的声音,形塑了民间知识分子清新的形象,构筑了文学杂志少有的参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公共论域,对当代台湾贡献颇多。苏其康教授说:“‘人文关怀’绝不是一个空的口号,而是落实在《文讯》的各种文章和书写中,……许多建议不是作壁上观的书斋之见,而是务实性的针砭并能够剑及履及,是有价值的文化评论。”[18]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敢为人先”、“铁肩担道义”的价值立场,淋漓尽致地表征了《文讯》及周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台湾传播学者须文蔚指出,“在文艺刊物上鲜少见到文化政策的专题,文化公共论域的阙如,更显得《文讯》杂志25年来进行过的20个文化政策专题,以及9个特别企划,共计253篇文章,显得异常珍贵。”[19]
再次,从服务作家学者看,《文讯》确立文化品格的第三面向:敬重人伦,构建和谐有序的优质文艺伦理。李瑞腾总编较早提出“文艺伦理”的概念,意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文学活动在文学场域的延伸——诸如世代、文人集团、审美霸权之间的颃颉,报刊杂志、文学流派、社团之间的竞争,都可纳入文艺伦理的框架考察。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台湾社会矛盾丛生,文艺伦理备受扭曲,文学论争裹挟蓝绿矛盾,世代演递缠绕人际纠葛,文艺评论内藏族群之争,而文坛前辈逐渐被遗忘。在此观照下,《文讯》始终甘当桥梁、人梯,倾力重构文坛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和谐有序、团结协作的人际伦理。首先是文坛里“扶危济困”、“仁爱和谐”。多年来,《文讯》除了向读者介绍资深作家、文坛新锐,还以实际行动关怀处于困顿处境的老作家、学者。在物质、精神上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郑明娳教授说得好:“《文讯》一直具体而微地做着本来应该由当局来主导的工作。就以照顾作家来说,长年来,《文讯》挖掘年轻作家、鼓励成长作家、照抚年老作家,可是因为人力不足、资源匮乏,只能靠着机遇点击式努力,无法大布局地计划、主动且全面地放手去做。就结果而论,当局和《文讯》照顾的作家可能一样多。……而《文讯》照顾的总是鳏寡孤独或者穷愁潦倒的作家,不论人或者事,连新闻价值都没有,所以一直默默无闻。”[20]早在党营时代,《文讯》就形成传统:探访老作家。“今年(1997年5月)五四文艺节,特别举办了五四文艺节探望作家活动,表达我们对文艺的关怀,对作家的敬意,藉着探访,致赠慰问金和礼物,对曾经奉献心力的文艺创作或文艺行政工作的前辈给予温暖与关怀。……我们拜访了梅逊、黄得时、闻见思、陈纪滢、郭晋秀、李牧、陈火泉等作家,希望这个温暖的行动,能够年年持续下去。”[21]对于远在南部的作家,则想方设法代为转达,如委托《明道文艺》的陈宪仁去探访。黎湘萍十分恰切地归纳了《文讯》的品格:“尊老爱幼”、“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尊老”,指《文讯》坚持为作家、学者服务。首推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重阳文艺雅集,这个公益的、纯粹赔钱的活动迄今举办22届。封德屏总编辑说:“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让许多遗漏的作家及作品重现光芒,关怀贫病、弱势作家,努力地想为他们争取一些资源。杜甫当年‘安得广厦千万间,尽庇天下寒士俱开颜’的恢弘理想不敢企及,但唯有此时,能深刻体会其中的焦虑与无奈。”[22]“像这样一个年年以资深作家为主的活动,申请经费的困难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这些享受果实的后生晚辈,理应对他们表示敬意。”[23]雅集甚至衍生为办刊外的重要内容:间或性的慰问、探访;转达问候、查找联络、穿梭斡旋、看望文友、出版纪念专辑甚至接济作家。比如:为女作家严友梅转达书信给作家王书川夫妇、看望重病卧床的作家刘枋、为刚过世的作家尹雪曼播发新闻稿、组织纪念专辑等。第270期说:“我们得到许多作家的信任及协助,建立了编辑与作家良好的友谊。……我们接到於梨华女士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写给作者的信,“他们多年未联络,特写了一封问候老友的信,请我们转交”。[23]“尊老”更见诸精耕细作的编辑作业,它为海内外文坛提供老一辈作家、学者的近况。如第266期打破刊期安排,集中报道幼儿诗拓荒者薛林,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后隐逸多年的许希哲,中研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作家黄克全,学者周策纵等学人作家。2010年第8期专文追思刚辞世的作家商禽、韩国学者许世旭。“看到《文讯》仍坚持不懈地关爱着老作家的晚年,看到李瑞腾教授对琦君执晚辈礼,真是感动。不独如此,对于一般作家,《文讯》也是如此,2005年1月有‘李潼纪念特辑’,《文讯》对因癌症去世的李潼(1953-2004)的怀念,从那些质朴真诚的文章,到为李潼编写作年表,真令人动容。”[12]所谓“爱幼”,即不遗余力奖掖青年,提携文坛后进。学界声名鹊起的须文蔚、杨佳娴、陈建忠、胡衍南等60、70后学人,多受《文讯》培养。《文讯》的编辑团队均是崭露头角的新世代;在专案执行小组里,尽为学有所成的硕博生;青年文学会议殿堂里,更是“青春的盛会、文学的飨宴”。台湾文学研究的新世代就在《文讯》的思想濡染和活动、工作里成长,薪传了文学智慧,继承了良好的文艺伦理。
最后,从文化传承看,《文讯》品格浓缩了忠于理想、勇于担当、坚持操守、奉献社会、践重然诺等儒家文化精髓。与大陆文艺期刊政策不明朗的生存样态相比,台湾完全是“市场化”运作,按照布迪厄“输者为赢”的颠倒经济学逻辑,在“有限生产次场”“为生产者而生产”。因此,《文讯》脱离党营后只能自力更生。老作家毕璞说:“《文讯》可说是一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刊物,财力、人力都极度欠缺,经费相当困难,其中甘苦,我感同身受,……《文讯》的灵魂人物封德屏女士以她过人的毅力、惊人的热忱,奉献了她的青春,牺牲了家庭生活,无怨无悔地把全副心力灌注在这份刊物上,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般去养育、培植,使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慢慢成长、茁壮;终于25年有成,它开花结果,绿叶成荫,以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赢得了无数掌声,受到海内外关心与爱好文学或从事文字工作的读者们的喝彩。”[24]《文讯》的惨淡经营,和28 年的顽强执守,正是儒家思想谱系中践重然诺、恪守文学理想、为文化建设而入世济世的奉献精神。它的主事者李瑞腾、封德屏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和打拼精神,使这份杂志在困难中生存,在转型中发展,在拼搏中崛起,台湾文坛对此有很高评价。苏其康说:“《文讯》已成为台湾文学界甚至文化界的聚焦,……而且早就是台湾文学界最讨人喜欢最尽心尽力的义工。”[25]28年来,《文讯》想有所作为的无外乎两个关键词:文化、文学,但在政党主宰下,经费不足,差点数度停刊,因此艺文界总是担心这个体质蕤弱的“小孤女”半路夭折。它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靠的就是克难攻艰和对事业的忠诚,对纯文学办刊的坚持。即使遭逢困顿,依然反对商业文化的趋附、逢迎、恶俗,永葆文学操守,对文学人的尊重、提携,坚持超越党派,兼容各派;即使面临停刊,也不改其志,表现了九死未悔的担当。封德屏说:“有些朋友建议改版,重生后的《文讯》是不是焦点放在畅销作家、流行话题上,不要尽作一些‘不合时宜’的主题。但什么是合时宜的话题呢?历史铺陈、智慧薪传是持续累积,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我们不可能把过去切断或者遗忘。”[26]就这样,《文讯》不屈不挠地守护着文学这方净土。台湾学者高柏园说:“《文讯》同仁坚守理想,从不拿理想宰制他人。……它耐心守候所有的飘逸与风华,在默默中享受最平凡的伟大。”[27]
总之,在文学的细节处、立身安命的大节处,《文讯》执着表现出“仁爱”、“济世”、“执中”等精神气质;在穷与达、常与变、创新与怀旧间自觉扛鼎,它兼济文坛的胸怀未尝懈怠。一份刊物品质精良,乃在于专业的水准和高度;但既得到专业的赞誉,又得到文坛交相称颂,由衷喜爱、尊敬,那一定是文化基因与品格在起作用。
二
台湾新文学发展迄今60余年,赏鉴众多文学期刊的品格,惯有为文学而文学者,如《纯文学》。《纯文学》由林海音于1967年元月创办,它以文学创作、翻译、名家作品选录为主,内容亦“兼容并蓄,不分党派”,是台湾早期、中期及新生代作家的重要发源地,自林海音、余光中、琦君到张系国、朱西宁、白先勇等,均有承前启后之重。林海音在“联副主编”时期,在“密不透风的文艺体制下,……大胆提拔新锐,什么稿子都敢登,在1963年刊出了一篇有问题的文字,遂鞠躬下台”。[28]但是,无论《纯文学》,还是其他刊物如《文坛》、《作品》,坚持办刊理想,坚持纯文学立场,更多是编辑的职业需要和本能,少了《文讯》的艰难转型及屡次涉险的经历,和当今在大众文化围剿和市场白热化竞争的特殊情境下的自觉意识与勇于担当,从而也少了悲壮与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敢决绝;也有淑世情怀者,如《明道文艺》,它在总编陈宪仁的经营下,大胆刊用新人、尊重前辈作家,企划性高,又贴合社会脉动;通过举办学生文学奖、挖掘校园新人、积极参与社会、对作家学人的生老病死表现尊荣敬意、推动两岸文学文化交流,30年来,“呈现了温厚、深沉的温度和厚度,……创出温暖、深厚的文学环境,这是《明道文艺》一路走来,最动人的淑世理想,一种安静地在晦暗中为文学种梦的文化角力。”[29]但与《文讯》相比,《明道文艺》有“明道学园”这样全台知名的私人教育集团的雄厚财力,加之“台湾文坛影响深远的文学推手”、明道中学创校校长、著名教育家汪广平的支持,使得《明道文艺》被誉为“台湾作家的摇篮、台湾文坛的源头活水”;[30]还有以“小众拥抱大众”者,如《联合文学》,创办27年来,被称为“敏锐精准的时代风向标”,融典雅/前卫于一体。它“横跨到艺术领域或次文化,从音乐、流行歌曲到卡拉丝,从华文戏剧节到柏林影展……逐一网罗涵纳”,它充满活力,除杂志、丛书,且有小说新人奖、巡回文艺营、研讨座谈等接力举办,彰显了动静兼备、互助互利的行事风格,渐成“华文杂志的翘楚、19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传媒之一”。[31]然而,《联合文学》的业绩除了历任编辑痖弦、高大鹏、丘彦明、马森、郑愁予、郑树森、初安民、许悔之等人的努力,企业化的行销与对流行议题的介入也成就了它经典/时尚的文化品格,而其身后庞大的联合报系更是可资倚重的靠山。因此,《文讯》与上述同侪相比,各有千秋,却更具精气神与深厚的文化气质。它独树一帜的品格,是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由党营转型民办、电子媒介诞生、市场化冲击、编辑群体的理想信仰、办刊宗旨以及《文讯》独特的身份、经历中打拼、孕育出来的,可以学习,却无法复制。
与大陆文学期刊相比,《文讯》也给予很好启迪。最近,颇具知名度的《上海文学》遭遇困难,主编赵丽宏表示,《上海文学》的收益主要有三,一是刊物本身收益,二是政府提供一定资助,三是靠社会资金赞助。虽然《上海文学》有五位数的发行量,但成本远高于支出,靠刊物的行销根本养活不了编辑部。而为了坚持纯文学刊物的品位和格调,“我们不会改变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不会登广告文学,不会降低杂志的品质。”[32]业内人士认为,在纯文学尚未从困境中摆脱的当今,由国家养几份纯文学杂志,保留几块文学的阵地非常必要,因为一旦全部放开,纯文学蜂拥转向商业,到时覆水难收。但问题是,纯文学杂志也应像《文讯》,多想摆脱困境的办法,多树立几个品牌,多涵养文化品格,坐等“被养”,只能给人留下抨击的口实。
学者李海舰指出,“学术期刊要有‘文化’,一是企业文化,包括办刊宗旨、办刊使命、目标导向、理念定位、论文取向、编辑模式、编辑考评、运作思路;二是职业文化,即编者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学术大师视野,要有为人作嫁精神,要有注重细节习惯;三是产品文化,即期刊要打上杂志社的烙印。”[33]显然,《文讯》早已构筑了自己的文化,“为人民服务”(陈建忠)、“文学荷光者”(隐地)、“文坛小魔瓶”(白灵)、“文学信使”(李敏勇)、“重要视窗”(刘俊)、“文学界的宝”(林澄枝)、“人少志气大”(宋雅姿)、“救风尘”(陈柏青)等等,都是对《文讯》品格的中肯评价。《文讯》前20年为党营刊物,为何它能够摆脱党派色彩,办出另类风格,它的突破凭借什么?作为台湾文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值得从中找寻镜鉴。一是非营利的因素,无经费短缺之掣肘。早期的《文讯》坦承:“基本上,这不是一个营利的刊物,它的非市场化取向,使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能够完全站在文学的立场,采取学术的方法统摄过去的文学现象与成就。”[34]可见,文化既要产业化,必要时又需不计投入加以扶持。二是党营时代,早期主管的宽容、开明和后期国民党不管不顾,少了政治干预,可以为“艺术而艺术”。《文讯》创办人、原总编辑孙起明回忆说:“周应龙主任包容年轻人的强悍无礼,信任年轻人的见解主张,放手让我们去发挥,从不过问编辑计划,从不事先审稿,使我们几个人……不考虑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也不管党的文艺政策,决心走文学的路。不做传声筒,不做指导者。……从创刊之处起,我就决心走一条坚持文化价值、尊重文人发声的路,……我们不分党派、地域、省籍、男女,来稿欢迎‘文以载道’,也欢迎‘文学的归文学’。”因此,《文讯》走过的道路,为台湾文学期刊史展示了跳脱政治文化,“深刻、诚实地与知识分子对话,甚至辩论,以学问服人,赢得尊敬”[35]的努力。三是主事者的视野和胸怀,决定了以文学为本位。《文讯》“能在台湾这样的政治挂帅社会中受到重视和信赖,原因甚多,但主要应在于编辑群的努力,和主事者的高度自制,他们……不党不私,忠实纪录了每个年代的文坛脉动”,[36]而且“不为政党、文学流派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机器掌控,这是李瑞腾主编时就成形的模式,在封德屏主编后更加确定”。[37]四是民营后少了政治考量,坚定了它的超越与兼容。《文讯》在市场与文学间力求平衡,企业化、团队化、项目化管理引进期刊生产,从产品包装、宣传到品牌的经营,从形到质都发生改变;产品意识强化,商品性质突显,合作意识、经营意识不断加强,如举办研讨会、座谈会、资料展、重阳雅集、设置文学奖等,对自身大力宣传,营销意识高涨。这些手段提升了生产力和竞争力;注重与同行、学者作家等的联系;逐渐由纯粹党营,不考虑赢利的封闭办刊走向开门、开源、开放、开拓、开明办刊。
今天的《文讯》初步实现了自立且凝练了文化品格,增殖了“象征资本”,树立了品牌和形象,凝聚了文坛认同,增加了知名度与美誉度;而办刊的精良又涵养和反哺了品牌的价值。但是,《文讯》要实现由“好看”到“好刊”,从“名刊”到“强刊”的跨越,必须运势乘势,践行大道,坚持走“文讯式”的特色发展之路,坚持在办刊实践中锤炼品格强硬体质,以文化软实力奠定做大做强的基础。文化立刊,大道行之;文化强刊,大势趋之。资深编辑家、诗人痖弦说:“《文讯》早已摆脱前人的窠臼,以不同的思维、现代传播的理念创造出文艺杂志的新形象,……俨然成为华文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刊物。”[38]
[1]林建法.序:批评的转型[C]//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文学批评.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1.
[2]朱双一.老中青皆尊,各流派并重[N].台湾日报,2002-06-03(9).
[3]陈芳明.在捻灭理想之前[N].联合报,2003-01-08(12).
[4]封德屏.独立七周年记[J].文讯,2009(12):1.
[5]辛广伟.台湾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6.
[6]黄蓓伶.探究台湾杂志的核心优势与未来走向[J].全国新书资讯月刊,2007(9):19.
[7]邵培仁.大众传媒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12.
[8]南松山.从传播的角度谈文学的生死[J].联合文学,2003(7):90.
[9]陈昌明.困境求生:敬专业的文学团队[J].文讯,2008(7):73.
[10]封德屏.编辑室报告[J]. 文讯,2010(1):1.
[11]陈信元.期待台湾文学的新地标[N].联合报,2002-05-24(12).
[12]黎湘萍.汉语文学史中的《文讯》[J].文讯,2008(7):105.
[13]孙起明.编者的话[J].文讯,1983(7):1.
[14]李瑞腾.编辑室报告[J]. 文讯,1985(4):1.
[15]李瑞腾.编辑室报告[J]. 文讯,1989(2):1.
[16]编者.编辑室报告[J].文讯,1997(7):1.
[17]编者.编辑室报告[J].文讯,1989(2):1.
[18]苏其康.文讯的文化关怀[J].文讯,2008(7):18.
[19]须文蔚.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健全[J].文讯,2008(7):26.
[20]郑明娳.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文讯》[J].文讯,2008(7):79.
[21]编者.编辑室报告[J]. 文讯,1997(6):1.
[22]封德屏.编辑室报告[J].文讯,2008(1):1.
[23]封德屏.编辑室报告[J].文讯,2007(7):1.
[24]毕璞.一个老朋友的祝福[J].文讯,2008(7):69.
[25]苏其康.抢救台湾文学,抢救文讯[N].联合报,2003-01-06(12).
[26]封德屏.编辑室报告[J].文讯,2004(2):1.
[27]高柏园.支持文讯就是支持文学[J].文讯,2008(7):65.
[28]应凤凰.50年代台湾文学论集[C].台北:春晖出版社,2007:205.
[29]黄秋芳.《明道文艺》的淑世角力[J].文讯,2003(7):93.
[30]汪广平.伯苓之后又一人[N].语文报,2009-10-31(15).
[31]陆尧:经典与时尚[J]. 文讯,2003(7):99.
[32]纯文学杂志走到十字路口?从《萌芽》转制说开去[EB/OL].[2011-01-11].http://www.thmz.com/col23/col60/2011/01/2011-01-11881748_2.html.
[33]李海舰.理论顶天,实践立地:《中国工业经济》期刊发展战略探索[J].中国工业经济,2008(4):67.
[34]李瑞腾.编辑室报告[J].文讯,1985(8):1.
[35]孙起明.回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J].文讯,2008(7):162-163.
[36]向阳.台湾文学的鲜活见证[J].全国新书信息月刊,2003(1):4-5.
[37]向阳.一个文学公共论域的形成[J].文讯,2008(7):4.
[38]痖弦.拥抱我们的《文讯》[J].文讯,2008(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