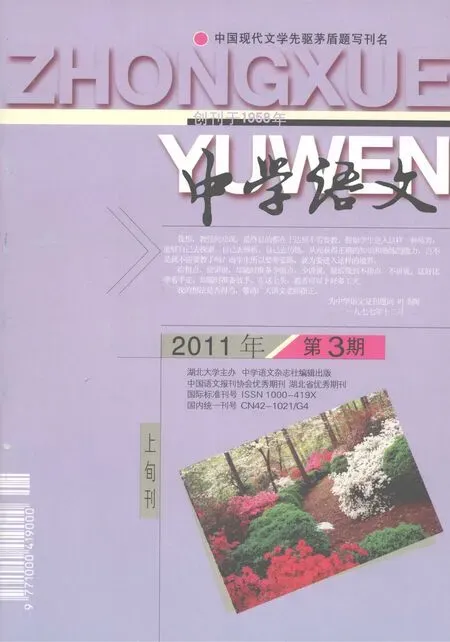触景生情与景为情设
张至真
景和情是一对连体兄弟,无法分割。情景相生,景由情美,情由景出,美学家说,自然中的景,一经人们的认识,就打上了情感的烙印,成了第二自然。王夫子《姜斋诗话》卷上云:“‘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之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这“心中”的是“情”,“目中”的是“景”,“所怀”的情与“景相迎”,才是作者表达所在。文学上写景即是为了表达心中之情,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常言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们自可坦露心肺,尽情表述心中的爱与恨,但真正的高明者却常常是“情至不堪处,付诸流水,以不尽而尽之,”将满腔的情暗藏于眼前的景中,让人感悟深思。因此嗥啕大哭者能示其悲;怀抱柳树、黯然饮泣者也能恸其人。
刘熙载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章是感情的倾诉,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功能,主要得益于作品能把作者心中的哀乐情感传达出来,去感染读者,影响读者,产生共鸣,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激起内心深处情感的浪花。直抒胸臆,衷情决堤,故动人心魄;曲径通幽,欲说还休,缠绵悱恻,亦情愫蕴藉。触景生情,如“杨柳岸晓风残月”、“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感人千古。现代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景,那情,那轮夕阳,那群雨燕,描绘的是自然之景,其中吞吐的不正是作者的款款深情?让读者去感知母爱的伟大、生命的可贵,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意识和责任感。
静静的小桥、幽幽的流水、春天飘落的丝丝斜雨,江南风韵凸现,何尝不是岁月的流痕、飘逸的心灵感触?“雪里红梅半枝开”,“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又何尝不是心中块垒的渲泄?
这里所讲的景物,不仅仅是第一自然,更是加上了人的意识的第二自然。《歌德谈话录》中说:“我深深了解,自然往往展示出一种可望而不可攀的魅力,但是我并不认为自然的一切表现都是美的。自然的意图固然总是好的,但是使自然能完全显现出来的条件却不尽是好的,”如橡树,“它须和风雨搏斗上万年才能长得健壮,在成年时它的姿势就会令人惊赞了”。而艺术家能从更多的层面来处理自然的美景。“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歌德是真正的艺术大师,更是文学大师,他用浅近的语言表述了艺术的真谛。同样,现代画家李可染先生在《漫谈山水画》中说:“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解图,不用说,它当然要求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与情要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科学的一面,画花、画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自己就不曾成功,当然感动不了别人。”
真正的艺术家正是自觉地驾驭自然,齐白石倡导的“师法自然”即是此理,并且真正的艺术家还懂得驱遣自然为主题服务,因情设景就是方法之一。
高中语文教材中选的《孔雀东南飞》和《药》,都写到了坟场的景象,但《孔雀东南飞》中的坟场并不能使人产生凄凉的情感,而《药》中华大妈与夏四奶奶上坟的地方却使人无限酸楚,倍感凄凉。笔者突出奇想,如果将两文中的景象调换,会是怎样的结果呢?读者一定会说荒唐,但《药》中的坟场就不能有松柏和鸳鸯,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坟场就不能有槐树和乌鸦?但这样安排的结果恰恰就出现了读者审美中的逆转,情感表述中的滑稽。
在艺术创作中,高明者无不根据情感的需要而创设相应的景物。同样,在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笔下的荷塘,其中就没有废纸、垃圾、癞蛤蟆?但它们的出现就是败笔。在茅盾的《风景谈》中那星星峡外的戈壁滩上难道就没有一丛红柳、一棵胡杨?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寂静”?但文本中不能去表现,即使有,都必须略去,只有这样,才符合朱自清所表现的月下荷塘的清幽之美,才能让茅盾在文本中为征服沙漠的 “人的伟大”而张本。作为艺术审美的对象,它必须表现出极致,才能更好地表情达意,为主题服务,感染读者,达到审美的娱悦。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精辟地阐明了写景为表情达意服务的内涵:“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确是至理至性之言。
中学语文教学,指导学生的鉴赏及写作,也应参透其道理,否则对自然的描述就会坠入自然主义的泥潭,而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会有偏差。如学生作文描写家乡的美景,写了宽畅的马路,写了新农村的别墅,也写了小河流水及青石板的小桥,构建起江南水乡的风貌,但文中出现的桥边的枯柳,桥脚下红绿的塑料袋垃圾。确实这是他眼中的实景,如果放在另一场合,表现人们素质的有待提高,表现和谐中的噪音,那是点睛的细节,但放在歌颂家乡美景的主题中就不和谐了,学生不知材料的取舍就破坏了文章的整体感。为什么不能写写那枯树根上发出的新柳,桥脚下几个懂事的孩子在捡拾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呢?在生活中这些现象都是客观的、真实的。那才是高于生活的文学的真实。
鲁迅先生在《药》中为夏瑜坟上凭空加上去一个花环,哪怕鲁迅认为当时的黑暗社会是“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但仍给作品涂上“若干亮色”,给后来者以希望。经典作品的魅力就在此,而提升学生的鉴赏力、实践性不正可资借鉴吗?
无论触景生情,还是因情设景,只要有自己的认识就能寻找出其中的规律,从而指导自己的实践和体验,达到创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