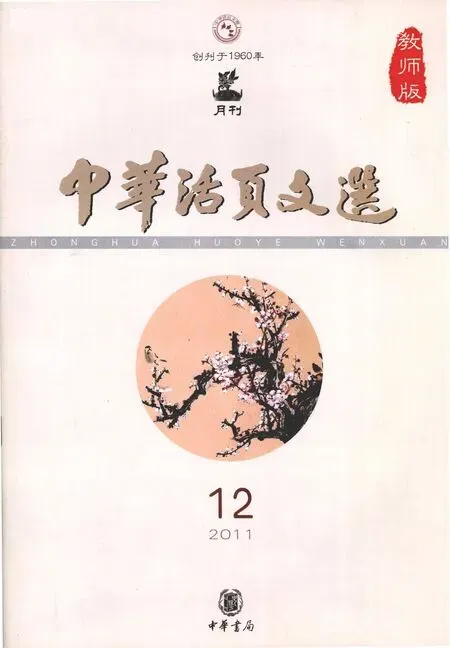叹惋那些被损毁的灵魂——简析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
■ 刘 琴(安徽省蚌埠市第二十六中学)
白先勇说:“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徜徉在白先勇小说的字里行间,认识了他塑造的许多不同境遇、不同年龄的女性形象。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钱夫人(《游园惊梦》)、黄凤仪(《谪仙怨》)、金大奶奶(《金大奶奶》)、玉卿嫂(《玉卿嫂》)、李彤(《谪仙记》)、娟娟(《孤恋花》)……作者的笔锋透过时代的变幻与动荡,透过人世的黑暗与冷酷,透过人物生活的起伏与不定,运用细腻、含蓄、深沉的文字,描写并剖析她们辗转挣扎最终身心毁灭的悲剧历程,突出表现了各阶层女性灵魂深处的痛楚与伤感,哀叹惋惜她们悲剧的命运。历史渊源、传统因袭、时代背景的共同影响,让身经战乱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白先勇选择了对乱世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思考。下面就以他笔下的几位女性为例,简析她们被损毁的形象。
朱青,原是一个纯情、羞怯的女孩,在南京与飞行员郭热烈相爱结婚。不久内战爆发,郭随空军调离。朱青整天失魂落魄,痴痴等待。得知郭不幸身亡时,“在床上病了许久”。病愈之后来到台湾的朱青简直判若两人,“没有半点羞态”,与青年军官打情骂俏,即使情人小顾死了,她依然无动于衷地打麻将、哼小曲、往脚趾甲上涂寇丹。战乱和人世的沧桑损害了朱青的感情,让她变得麻木不仁。南京时的朱青清纯、羞赧、学生味十足;台湾时的朱青却是一个浪荡的歌女。她的纯情、羞赧早已被俗艳、放荡所取代。就如她自己说的“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一个鲜活纯净的灵魂毁灭了。这种毁灭是与时代悲剧、社会悲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女主人公看似消极的人生观念的转变中,小说向人们昭示了人生无奈又悲凉的现实。
金大班,作为舞女依靠给男人提供性服务来维持自己生活。她只有不拿身体换钱,才有可能获得人的尊严。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后又在台北夜巴黎呼风唤雨的舞厅大班金兆丽,即将从良告别自己作为舞女的生涯,嫁给橡胶场老板陈发荣“做老板娘”,回归正常的家庭模式。金兆丽之所以愿意嫁给陈发荣,不是因为真的爱他,而是自己年老色衰,已经无力操持这个行当了。金兆丽从良的实质就是从寄生于多个男人转向寄生于一个男人,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陈发荣与旧上海滩一掷千金的富豪相比所显示的家资寒微,时刻提醒她年华不再,只能像过期的商品一样降价处理。这从良的结局从根本上宣告了女性通过嫁人获取尊严地位的失败。透过从良这一模式我们深刻地体悟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到一份人的尊严,其道路是何等艰难!金兆丽在“风月场里打了二十年的滚”,横了心堕落到底,“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她也曾有过真情,但为生存所迫,她辜负了爱人,也心甘情愿出卖自己,出卖那被损害的灵魂,沦落至心死的深渊。
余丽卿,曾经是“师长夫人”,随着民国历史的重新改写,师长早已被“砍了头”,她也流落到了水源紧缺、妓女充斥的自由港——香港。时过境迁,生存的重压使余丽卿接受了一个吸鸦片的男人,和他厮混在一起。她说“我没有将来”“我也没有过去”,昔日那个用过勤务兵的师长夫人“已经死了”。对过去辉煌的彻底忘却和在现实“欢乐”中的绝望沉沦,构成了余丽卿生存心理和生存准则的基本内容,使她能麻木身心,在“眼前这一刻”的苟活中浑浑噩噩地度日。灵魂早已毁灭,成了一个苟且偷生的行尸走肉。
钱夫人,才艺超群的蓝田玉嫁给了长她40岁的钱鹏志将军做填房夫人,为了“钱将军夫人”的身份和自己微贱的出身,处处小心,如履薄冰,为了维持这来之不易的名份,在钱将军身后孤寂清凉地打发漫长的余生。《游园惊梦》从钱夫人坐计程车到窦公馆参加聚会开始,一步步深入她的内心,突出她的潜意识,把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富贵荣华,只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可见钱夫人所经历的心灵磨难。时世变迁,身价大降,她只能坐计程车了,那“新的高楼大厦”与她内心的冷落与失意,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她的身份和荣耀是损害毁灭了青春、情爱、天伦之乐这些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换取的。小说以钱夫人的落魄暗示好景不长、人生如梦的无奈与虚幻。
金大奶奶,第一次婚姻损毁了她的青春,第二次婚姻毁灭了她的性命。她三十出头了,又经过第一次婚姻失意的历练,按说,她该对生活有所领悟。但她还是迷失在追求爱情的路上,金大“满面的潇洒神态”和“一嘴巴的油腔滑调”使她昏了头,错误地嫁了。金大先生把“田产首饰”拿到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她不是骂就是打”。她的亲戚和以前的佣人也趋炎附势,参与了对她的虐待。最后,金大奶奶服毒,死在金大先生讨小妾的喜宴上。她的灵魂随性命毁灭在人性的荒原中。
玉卿嫂,有着冰清玉洁的外貌性格。做少奶奶时,丈夫不上进,她无力劝阻;家道败落,她无力改变;婆婆苛责,她无力申辩。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对于一切的变故都只能默默承受。因此,当她遇到庆生时,萌生了强烈的控制欲,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对庆生的控制上,试图通过控制庆生获得安全感。对庆生的爱炽烈专一,为其倾尽所有。她认为自己付出了爱,就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庆生必须服从自己。试图在庆生面前扮演强势的角色,这恰恰反映了玉卿嫂内心的虚弱和处境的可怜。她渴望的,不是片刻的鱼水之欢,而是终身的归宿和依靠。在庆生移情别恋后,她灵魂中残存的人性也随之灰飞烟灭。她狂暴地手刃庆生,然后自杀。这个美丽而变态的女人以毁灭生命的方式为这场畸形的爱作幕。爱情的失败,婆家的阴冷,让她在痛不欲生的煎熬中,走向毁灭。小说以她的生命惨剧启迪读者,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不能为爱情迷失了自我,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意识。
李彤,刚到美国时,家世显赫,心高气傲,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曾经显赫的家世,随着太平轮的淹没而沦落。原本热情、奔放、豪爽的性格变得扭曲,她用狂放、孤傲来麻痹自己,舔食自己流血的伤口,但终究无法与命运抗争,表面的放荡并不能掩饰内心的痛苦和空虚。她的心底依然焦灼凄苦,她选择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最终在异国投水自杀,毁灭自己。李彤的人生悲剧有着时代背景,改变李彤一生的父母双亡事件正是缘于国内战事的爆发。作者用强有力的笔触,透过她欢乐的表面写出了她内心深层的精神痛苦,逐步地展现了她精神崩溃的过程。她放荡不羁,如风一般地自由来去,却在友人的“悲—闹—悲”中愈发显得空洞寂寥。在她天涯羁旅、远离母体文化的“疲惫”躯壳里,负载着苦痛的、没有归宿的灵魂,毁灭是她必然的结局。
娟娟,先后成为父亲和柯老雄发泄性欲的工具,遭受非人的蹂躏。从里到外、从始至终都浸泡在悲剧的苦水中。她时时面对的是疯子母亲和流氓父亲,年仅十五岁就被父亲强奸怀了孕。为逃离父亲的辱骂和邻居的白眼,娟娟弃家而去沦为歌女,最后不堪凌辱,杀死了凶残狠毒的柯老雄。人性的凉风在精神的荒原上无情地吹向瑟瑟发抖的“孤恋花”,日夜损毁她的肉体和精神。“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有疯癫母亲先天遗留的罪孽,有被父亲强奸堕胎的后天罪孽,而她身上所背负的最大的罪孽恐怕要属五宝那要报仇的灵魂。父权和男权共同损毁了她的灵与肉,她的灵与肉只能在男权社会的践踏下辗转悲啼。
白先勇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虽然出身不同、身份地位不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她们都曾经风华绝代、艳倾一方。尹雪艳“总也不老”“像一尊观世音”;金大班“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地高耸在头顶上”,又金碧辉煌地挂满了一身;李彤“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玉卿嫂长得“好爽净,好标致”……然而时世弄人,人事无常,她们最终都难逃悲凉的命运结局。这些女子犹如朵朵失水的鲜花,挣扎飘转于无情、残酷的乱世之中,最终的悲剧结局便是“美”的毁灭。当她们在异化了的强大社会环境中处心积虑、全力挣扎,只为肉体与灵魂保存、维系在一起,却最终得到身心双重毁灭的人生形式时,读者便受到了强有力的灵魂震撼,情不自禁地叹惋这人间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的毁灭更能抵达人们灵魂的最深处,引发人们对生命本真的思考——自强自立才是女性生存之道,依附男性只能带给她们最终的毁灭。
白先勇说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中的痛楚变成文字。”翻开白先勇的每一部小说,我们都能感到作家无奈、悲凉、叹惋繁华不再的悲悯情怀。他的小说以独特的痛楚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