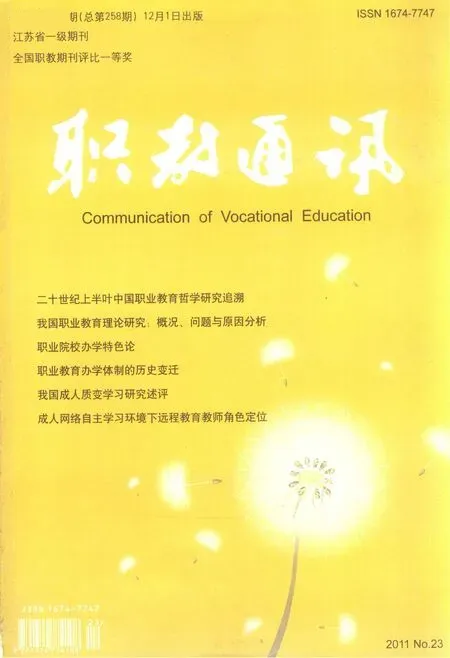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追溯
陈鹏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天津南开300072)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追溯
陈鹏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天津南开300072)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在探索职业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主要意蕴指向个体的、社会的、职业的以及教育的不同哲学取向,萌生出民生主义、生利主义以及大职业教育主义职业教育思潮,呈现出多重取向的糅合、不同思潮的交叉、救国情结的渗透以及西方理念的融入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单一取向的独立、不同思潮之间的明晰、教育本身的发展以及本土时代的流变等方面的困惑。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追溯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随着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在二三十年代,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大批职业教育学者包括庄泽宣、邹恩润、何清儒、潘文安、杨鄂联、杨卫玉、陶行知等纷纷著书立说,为早期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贡献了一笔不可磨灭的宝贵财富。更为可喜的是,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萌芽,渗透了不同的哲学研究取向,产生了若干职业教育思潮。对早期职业教育哲学蕴意的考察与分析,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状态,亦为当今职业教育理论尤其是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基本取向的意蕴
研究的不同取向可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它是基于对职业教育“为了什么”的基础性研究,为职业教育的本真意义作了原初性规定。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在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中,意蕴了哲学问题上所探讨的基本取向问题。
(一)个体取向
人之个体,是哲学上亘古不变的核心话题,而对于个体的关心与维护,则是哲学上一直努力的方向。个体存在于世上,一方面要生存,一方面要发展。然而,面对贫瘠与残酷的大自然以及复杂的人类社会,个体的力量往往又是脆弱的。清末民初,战争频繁,政治更迭,百业凋敝,整个社会可谓是民不聊生。为了捍卫特殊环境下的普通民众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广大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在探讨职业教育的本质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其“为个体性”的一面。
针对清末民初大批毕业生失业、“求一饭之地而不可得”的严重现象,黄炎培认为,“补救之法,惟有全力提倡职业教育”[1],足可以看出其对职业教育解决个体生存之保障的功力抱有坚强的信心和信念。邹恩润进一步指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的长处……藉以求适当之生活”[2],这也就赋予职业教育作为个体谋生之手段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也有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庄泽宣认为,职业教育可以“使人人获得适当的职业,并成社会健全分子”[3];潘文安则认为,职业教育可以使得“人人一方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4],二者在强调职业教育指向“人人”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其促进个体完美发展的重要职责。对此,何清儒亦给出了自已的理由,认为“完满”的“职业生活”是个体“完满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职业教育要为个体“美满职业生活”负责。[5]中华职教社作为重要的学术团体,则综合了职业教育的在促进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双重个体性功能,将“为个人谋生之准备”、“谋个性之发展”[6]共同作为职业教育目的的重要方面加以规定。这都充分凸显了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将职业教育视为维护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坚定取向,规定职业教育应为个体基本生活来源的供给以及美满生活的满足承担重要的职责。
(二)社会取向
任何教育除了个体指向之外,还有维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职业教育同样如此。社会的发展大到国家、民族的繁荣,具体到经济各领域的发展。在清末民初之国势日损、百业枯槁的特殊国难时期,职业教育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工商百业的复兴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应负有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为此,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者打着“教育救国”的旗号,走向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探索之道。
中华职教社在承认职业教育服务个体性的同时,还强调要“为个人服务社会”和“为国家和社会增进生产力”做准备[6],并进一步总结到,职业教育“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就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7]可见,其对于职业教育之社会取向的深刻性认识。在“毕业生失业”、“工商衰落”、“农村崩溃”种种社会困厄之下,杨卫玉认为,职业教育可以作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对症发乐的良方”。[8]王达三同样从社会取向视角论述了特殊国难之下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之处,指出“教育是维系于社会本身之上,社会生病——即国家有难”,就要实施特殊时期的特种的“救国教育”,以使“社会整体日臻健全而进化”,这一特种教育就是“职业教育”。[9]而职业教育要完成其为“社会整体”之“健全”的服务功能,就要坚定其“以经济为中心”[1]、“为国家及社会增加生产力”[3]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将“富民政策”取径于“职业教育”[10]的救国路径。熊子蓉则更加明确地从社会视角提出了我国实施职业教育的三原则,即应顾及“民族复兴之条件”、“社会经济标准之提高,国民财富分配之合理化”、以及“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国民经济适应能力”。[11]从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复兴的社会救济之道,不仅包含经济标准的深度提高、国民财富的横向平衡,也包含了促进国民经济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能力,这就进一步拓展了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丰富内涵。
(三)职业取向
职业教育研究的职业取向,基于职业教育源于社会分工即职业的产生这一原发性动因。在“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古代,根本不需要有职业性的教育存在,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各种职业产生了,这就需要围绕职业的需求对个体展开相应的教育,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工商等行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学校的教育却培养不出符合职业需求的合格人才,这就激起了有关学者对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研究。
“职业教育,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施教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12]这同样是黄炎培先生给予我们的答案,他表明“职业”是职业教育的最终归宿,“教育”只是通向职业的手段或途径,并强调了职业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要以“职业”为极端的关注,应围绕职业而展开相应活动。朱元善进一步指出,职业教育就是“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13],这同样赋予了职业教育之为“选择职业”、“增进能率”而服务的“职业性”职责。有学者还围绕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在其与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上作了深入的分析。何清儒认为,职业成功的因素不仅限于“技能”和“知识”方面,与技术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还应将“人格的修养”、“性情的陶冶”、“习惯的改变”、“心理的调剂”和“服务道德的养成”[14]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以使受教育者成为职业中的“成功者”而不是“机械”。邹恩润认为,与普通教育“增进一般的智慧”的智慧不同,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造成有智慧之特别职业生产者”[15],这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指向具体的职业,具有职业的定向性。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职业教育的定义和本质的规定中,还是从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区别之论述中,都明显地看出早期职业教育研究的职业性取向。
(四)教育取向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固然具有教育性或育人性的一面。因此,职业教育不仅仅限于职业训练的一面,还需要从广义教育学的角度追寻其教育性的真谛。师徒制同样可以产生职业训练的效果,但而后却被系统的职业教育所取代了,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缺乏后者所蕴含的育人性因素。用美国职业教育学者希尔(Hill)的话说,就是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注意“职业训练”,另一方面要“顾到受教育者”。对此的研究,同样没有逃脱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学者的视线。
杨卫玉在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做出重新估计时指出,“职业教育的价值绝不仅为狭义的功利主义与生产主义”,除了应“随时代之环境和需求”而变外,还要顾及其“不以时代而变更”之教育“共同最大之目标”,即于“自由教育,文化教育,人格教育,乃至公民教育,无不包含其中”。[8]对于上述看法,邹恩润在阐述职业教育的目的时同样给予充分认可,他认为,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首先应具备所有教育的共同目标,即使学生“在智力、意志、感情各方面,成为完全有用的人物”、“将来能以之应用于职业而自谋生活,同时,能进而协助社会与国家之幸福”。[2]可见,这种以智力、意志、情感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教育、文化教育、人格教育或者公民教育是职业教育在开展职业训练之前和之中必须具有和遵循的,因为它们一方面为个体的职业训练起着基础性的基奠作用,另一方面,为个体日后享受完满的职业生活做准备,以便为大众、为社会、为国家谋得福利。对职业教育之教育性取向的孜孜追求,表明了早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就开始规避职业教育之狭义功利性的畸形发展态势,这对当时乃至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都算得上一个不菲的贡献。
二、主要思潮的萌生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部分职业教育学者在探讨职业教育基本问题时,还催生了几个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进而形成了相应的职业教育思潮。
(一)民生主义职业教育思潮
民生主义职业教育思潮,源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救国政策。面对当时复杂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我国出现了民穷财尽的严重社会现象,毕业生失业,人民无能自立。为使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抱着对劳动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根本的民生问题的关怀,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基本纲领,并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其主要内容。可见,“民生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解决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之个体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一基本理念出发,一些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将其延伸和应用到了职业教育的领域。潘文安认为,“民生主义是解决人民经济的主义,职业教育是解决人民生活的教育[4],杨鄂联指出,“民生主义包含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为“达民生主义之一种方法,亦一种工具”。[16]从二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与民生主义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可以这样说,民生主义是一种理念的渗透和指引,而职业教育是为实现这一理念性目标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对于蕴含民生主义理念的职业教育应达到的宗旨,潘文安、杨卫玉给出了相似的回答,“使人人一方得到生活的供给和乐趣,一方尽他对群的义务”[4]、“使人人以其个性,准备一技之长,从事于人民生活,社会生存,国家生计,群众生命的生产事业”[8],其中的“人人”、“生活”、“生存”、“生计”、乃至“生命”等都充分表明了职业教育所孜孜追求的“民生性”。邹恩润、杨鄂联则从理想的职业教育目标和范围的层面分析了平民主义即民生主义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教育不仅要追求纵向的升学准备教育,还要为广大的受“经济压迫”或“天资所限”等“无力升学”者提供横向的教育,以“为大多数人群谋福利”,这就需要平民主义的职业教育“以济其穷”。[17]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具体职业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广大辍学、失业者“一技之能”谋生手段的基本需要,从而满足普通个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之民生问题的需要。
(二)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潮
与民生主义强调“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不同,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潮更侧重于职业及其教育的“生利性”。以“生利”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思想源于二十世纪初在欧美盛行一时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效率职业教育思想,当时的美国职业教育学者史尼登(Snedden)就认为“凡是有预备生利的功效的教育,都可以叫职业教育”。同一时期的中国,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社会现状异常糟糕,职业教育救国被提上日程,此时,陶行知提出了“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然而它却超越了欧美狭义的经济功效性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陶行知认为,“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18]可见,陶行知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中的“生利”的对象是“人民群体”,生利的主体是“工商百业”,生利的途径是“教育”即职业教育。在陶行知这里,生利的涵义已经超越了前述的“民生主义”之“平民个体性”以及“效率职业教育”之“经济性”的“生利”所在,它将这种“生利”扩充于社会百业以及整个人民群体的诸多范畴。此外,陶行知还驳斥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生活主义和衣食主义两种较为偏激的职业教育观,认为生活主义职业教育过于宽泛,职业只是生活的一方面,职业教育只是教育的一种;而衣食主义职业教育则过于狭隘,只停留在解决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上。因此,必须坚持所谓的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在此基础上,陶行知还探讨了职业学校的教师、设备以及课程的安排和实施原则。从本质上来说,陶行知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利”,但这种“利”兼顾了“人”、“物”和“事”,集个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于一体,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救国主义教育思想。
(三)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潮
随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以及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从1918年至1926年的8年间,职业教育机构数增加了2倍多。然而好景不长,到二十年代末,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又迅速沉寂,职业教育机构合并的合并、撤销的撤销,到192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存157所。究其主要原因就是职业教育没有加强与社会的主动联系,失去了发展的生命力。面对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严重困厄,黄炎培先生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
在总结过去几年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黄炎培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只从职业学校下功夫”、“只从教育界做工夫”、“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都“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积极地说来,“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9]从其论述中不难发现,职业教育不仅只有一种模式,应实现办学形式的灵活化;职业教育也不只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除了职业学校外,还应有其他非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形式。作为一种教育形式,需要与其他的教育形式加强衔接与沟通;作为一种面向职业的活动,需要与各种形式的职业界加强交流;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需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当中。这就是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大”之所在。按照上述推理,可以对其做进一步具体的解释。首先,职业教育机构应包括职业学校和各种非职业学校等机构形式;其次,职业教育应具有所有教育之共同的大目标,即要顾及学生智力、情感和意志等基础能力的培养;再次,教育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和“极端的信仰”;最后,职业教育应根据不同地方的需求和特点设置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课程与教学也要加强与社会活动的联系,以实现真正的实用效果。
三、若干特点的呈现及其反思
中国早期职业教育研究在孕育哲学取向与萌生哲学思潮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若干特点,这些研究的特点一方面体现出最初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
(一)多重取向的糅合与单一取向的独立
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呈现出了多元取向的职业教育研究态势,有以“关心和维护”“人人”为核心理念的个体取向,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为旨意的社会取向,有以“联络职业”、“信仰职业”为目的的职业取向,以及以“共同最大之目标”为基础的教育取向。多元取向职业教育观的并存,体现了中国早期职业教育学者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与灵活性。然而,这种多元的研究取向往往在同一研究者身上糅合并存,难以凸显某一取向的主导地位。以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而言,其在强调职业教育个体性的同时,也注重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并竭力提倡职业教育与职业以及其他教育的联系性。这一方面说明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哲学本身的建构,因为研究取向的独立是哲学研究所遵循的最为重要的原则,不同的研究取向要取得共同的突破性进展,唯独需要相互激烈的争鸣与冲突。
(二)不同思潮的交叉与彼此之间的明晰
如前所述,中国早期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同样萌生了不同的职业教育哲学思潮,主要有以“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为指向的民生主义,有以“利”于“人”、“物”、“事”为目的的生利主义,有“联络”和“沟通”“全社会”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不同职业教育哲学思潮的产生体现了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建立哲学流派意识的主动与自觉,对于今天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然而,在笔者的分析与论述中,也发现它们存在有部分的交叉与重叠,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民生主义的“为民性”与生利主义中的“利人性”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之处,其同时也是大职业教育主义中所提倡的沟通“全社会”中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对其产生的共同影响,但也同样体现出不符合哲学派别的发展趋向和规律,因为不同职业教育哲学流派的林立和独立,也需要建立独特的、牢固的核心理论体系。
(三)救国情结的渗透与教育本身的发展
不同职业教育研究取向和哲学思潮皆是历史驱动所果,因此,它们都烙有深深的历史史实的痕迹。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军阀的纷争以及国共的争斗,产生了一系列严酷的社会现实问题,民族与国家危在旦夕,刚有起色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停滞,毕业生失业严重,农民愚穷弱私。面对冷酷的社会现实,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学者在蕴意哲学思想的同时都伴随着深厚的“教育救国”情结,“个人谋生”、“服务社会”、“联络职业”、“公民教育”以及“民生”、“生利”、“沟通全社会”都无不渗透着浓浓的爱国、救国情结,这是历史与时代赋予每一位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是个体作为国家主人翁存在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本身的发展。当然,我们仍需注意,对于教育的研究乃至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更要超越历史,要尊重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实现教育研究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基本原则。
(四)西方理念的融入与本土时代的流变
在对职业教育研究取向以及思潮的梳理中,笔者不时地提到,中国早期职业教育学者在研究中有借鉴西方研究思想的某些倾向。如生利主义思潮是源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效率论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潮是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事实证明,不仅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有沿用西方理念的痕迹,就是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甚至“职业教育”一词都是从西方舶来的。西方的舶来品或许在特殊国难的情形之下能解暂时的燃眉之急,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国家毕竟有自己的历史与社会发展模式,时过境迁,适于一时并非适于一世。特定的职业教育思潮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一时繁荣而一时兴起与发展,然而到建国后随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职业教育”被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技术教育”所代替,兴盛一时的职业教育思潮也随之消退,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有人重新忆起。
[1]黄炎培.抱一日记[A].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52,188.
[2]邹恩润.职业教育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0.
[3]庄泽宣.职业教育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3,5.
[4]潘文安.职业教育ABC[M].上海:世界书局,1929:15.[5]何清儒.职业教育的哲学[J].教育研究,1934(51):1.
[6]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A].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16.
[7]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什么[J].教育与职业,1930(4):3-6.
[8]杨卫玉.职业教育价值之新估计[J].教育与职业,1935(2):109-111.
[9]王达三.特种教育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36(10):791-799.
[10]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二)[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32.
[11]熊子蓉.我国需要何种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35,(2):87-91.
[12]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J].教育与职业,1923(41):1-3.
[13]朱元善.职业教育真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29.
[14]何清儒.职业教育与人的教育[J].教育与职业,1933(149):679.
[15]邹恩润.职业教育之鹄的[J].教育与职业,1923(42):1-3.
[16]杨鄂联.民生主义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27(86):335-337.
[17]邹恩润.理想的职业教育目标[J].教育与职业,1925(68):561-563.
[18]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A].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161.
[19]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A].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31,432.
Retrospect on the Research about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the First-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hen Peng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In the first-half of the 20th Century,while the the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as being explored by the scholars engage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at time in China,different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including individual,social,vocational and educational were embodied;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s includ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inciple,making profit,and gr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ere born;and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multi-orientations mixing,different thoughts overlapping,rescue-nation feeling permeating and western ideas being drew were also appeared.However,some puzzles still exist,including single-orientation independent,different thoughts distinct,education as it self developing and domestic era evolving.
the first-half of the 20th century;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the research;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陈鹏,男,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G710
A
1674-7747(2011)23-0001-05
[责任编辑 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