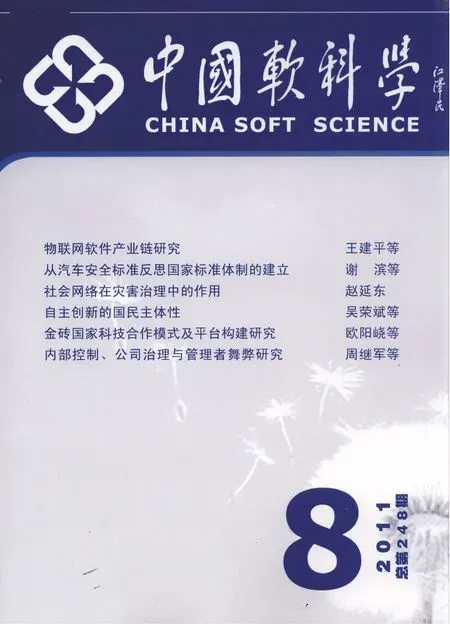市场统一基本制度之构造与实施
郑鹏程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市场统一基本制度之构造与实施
郑鹏程1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稀缺资源只有在统一市场才可获致最优配置,大国中政治性分权与经济性统一的制度悖论必将产生市场分割问题,财政联邦制、司法调节等难以解决此种顽疾。自由流动规则、竞争规则是克服市场分割、维护市场统一之基本规范。中央应从战略高度重视两类规则之构造,在宪法中增设自由流动条款;扩大竞争规则适用于政府行为的范围。
市场分割;市场统一;自由流动规则;竞争规则;行政调解
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稀缺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获致最优配置,因此,建立并维护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区域性国际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就成为各个国家、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乃至全球性经济组织努力奋斗之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以来,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实现国内市场统一,促进各类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成为中央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过30多年的持续改革,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整体考察,国内市场尚未获致真正统一。抛开两岸四地间的各种贸易壁垒不说,单就内陆市场而论,商品、人员、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还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有经济学家曾经测算,中国的国内贸易壁垒远远高于国际贸易壁垒。而在金融危机或市场疲软等经济不景气时期,地区壁垒与市场分割往往更为突出和严重。市场分割的危害极其广泛且深远,用美国联邦党人的话来说,它会成为国家“不和与冲突的重要原因”,“会助长无休止的仇恨”[1]。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时刻警觉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问题。本文试图就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构建既能保障地方自主权又能防止、规制地方保护主义,使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统一市场)实现有机平衡的制度进行探讨。虽然论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用法律手段规制地方保护主义,但一方面,规制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市场统一,倡导维护市场统一比主张打击地方保护主义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损害市场统一比判断其是否构成地方保护主义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论题定为市场统一基本制度之构建与实施。
一、市场分割:政治性分权与经济性统一制度悖论的必然产物
对于任何大国或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建立或维护内部统一市场之努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与阻碍内部市场统一的各类保护主义势力和行为作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自1824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第一起地方保护主义案件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开始,美国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斗争历史已有180余年,迄今仍未停止①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鄂乃德与赫基马固体废物案中就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作出裁决,参见:United Haulers Association,Inc.,et al.v.Oneida-Herkimer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uthority et.,Decided April 30,No.05-1345.2007.。欧洲人为了建立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奋斗了50余年,虽然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成员国相互间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或指控从未间断。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之后,国际社会就致力于“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达到“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目的,但迄今为止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者WTO所取得的成绩与其所标明的宗旨相比,差距甚远,而且目前每一种削除贸易壁垒的新的尝试和努力都遇到了重重困难。自墨西哥坎昆会议无疾而终之后,新的一轮WTO多哈多边贸易谈判毫无进展。而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多哈谈判雪上加霜,前景更加黯淡。
市场统一任务之所以长期和艰巨,源于市场统一进程中作为个体利益的成员利益与作为整体利益的共同体利益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冲突。任何经济共同体都是由若干成员如主权国家、主权州或地方政府组成的。在一个经济共同体中,构成该共同体的成员一方面必须依据条约或法律的规定承担维护共同体市场统一(共同体利益)的义务,另一方面必须增进其辖区内选民或居民的福利,对其辖区内选民或居民的利益(成员利益)负责。
从长远来看,共同体利益与成员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为,不管一个经济共同体是国家,还是区域性国际组织,抑或是WTO这样的国际组织,其统一内部市场,实现资源帕累托最优配置的目的,都必须通过其成员及其成员所辖区域内居民在开放市场中的公平竞争才能实现。没有共同体成员及其成员所辖区域内居民这些独立利益主体的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从此角度考察,成员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考察,共同体市场范围越广阔,市场统一的程度越高,共同体所掌控的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可能性或者说共同体成员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成员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机会也会越多。共同体利益与其成员利益的这种一致性,为作为独立个体的成员加入各种经济共同体提供了激励。
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借助其成员之手来实现这一机制,内在地、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通过各成员利益之最大化才能实现,所以,不管一个共同体对统一其内部市场的愿望多么强烈,它首先得承认并在法律上尽力保护其成员及其成员所辖范围内各类机构的独立利益(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主体地位。在一个统一的市场内,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共同体各成员之间必须为其辖区范围内各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居民或企业)争取有利的交易条件而展开竞争,这也正是共同体所期望的。不过,共同体成员所采取的竞争方法和手段与其居民或企业所采用的竞争方法和手段根本不同。企业最常用的竞争手段是价格,即通过优质低价策略争取市场份额。而共同体成员,不管是享有主权的成员,抑或是不享主权的成员,一般不直接购买或销售产品(服务),所以,价格不是其主要的竞争手段,共同体成员最常用的竞争手段,是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即经由制度降低本辖区范围内各利益主体的交易成本或增加辖区范围外各利益主体的交易成本,以此保护、提升其辖区范围内居民或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我们称之为制度竞争。制度竞争,特别是与经济交易活动密切相关的制度的竞争常常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效应,即对他人带来不能用市场交易衡量的不利影响[2]。例如,如果一个地区的税收优惠措施只给予本地企业而不给外地企业,则外地企业在本地的市场竞争会受到经营成本高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从市场统一的角度考察,构成了市场壁垒。所以,只要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各种成员利益,成员利益就必定会与共同体利益发生冲突。
不管是在疆域上,还是在人口上,中国都是一个大国,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既没有市场观念,也不承认作为政治共同体组成部分之各级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主体地位。虽然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强调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3]。但这种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上升为法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大国通常有的市场分割问题。基于对不承认地方利益、不承认市场经济的教训的切身体悟,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不但承认了地方利益的合法性、接受了市场观念,而且将地方利益、市场经济理念写入了宪法。1982年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应有职权划分”的规定及1993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将我国的经济推向了快速发展轨道。目前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但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告诫我们,不能再回到原来大一统的集权主义时代。作为现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实行联邦制的大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适当的政治性分权,以促进地方竞争,可能成为将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选择方向。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同于美国的州政府,更不同于欧盟的成员国,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属于主权单位,但是有地方竞争,就必须承认地方利益,而有地方利益,就必然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即使中央政府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也不能为了根除附在地方利益之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将作为市场统一发动机之一的地方利益根除。因此,如何在承认并保护地方利益、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前提下,防止市场分割、维护市场统一,成了中央政府的一大难题,也成为中国学术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二、市场统一观评介
学术界对市场分割问题的关注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为止所提出的克服市场分割、整合国内市场的主要观点有分权观、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观、司法调节观等。
(一)分权观
分权观也称为“财政联邦主义”,主要是经济学界提出的观点。许多经济学者指出,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是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之结果,是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刺激了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以邻为壑”[4]。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的促进市场统一的具体对策是完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5],实行“经济性分权”[6],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换取地方政府放弃地方保护行为”[7]。而分税制的完善,首先必须解决事权与财权不清的问题,认为“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以及管理权限,使事权划分与支出相一致并和财力相适应”是“建立完善、规范、责权明晰的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8],政府间事权划分应遵循效率性、公平性和经济稳定性三个基本原则,“凡是关于国家整体利益、全局利益的事务……应由中央处理;凡是关于地方局部利益和地方自主性、地方自主发展的事务归地方处理”[9]。
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对于构建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将其作为规制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国内市场的主要措施则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很难界定,而这正是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条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只需要做三件事:界定产权、保障交易安全、解决私人纷争。然而,这种理论已经不适合于混合市场经济时代的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已经结成了彼此不可分离的联盟,在这种联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10],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获得合理界定,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即使解决了事权与财权的划分难题,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能得到有效规制,因为,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并不否定分权,而是强化分权、规范分权。强化分权可能导致“一个严重的悖论”,即“当中央权威被削弱之后,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变成'掠夺之手'而不是'帮助之手'”,进而使市场更难统一。此外,“在一个存在具有文化、民族差异的国家,如果政治和(或)经济分权程度过大,那么地方政治家就很可能选择分裂主义政策……如果中央既无财力收买分立主义倾向的地方,又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很可能帮助本地企业逃避中央税赋和管理来发展本地经济,进而削弱中央维护法律秩序、征税和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福利”[11]。
(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改革观
部分经济学者运用博弈理论,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对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行了诠释[12],认为当下中央政府建立的考核机制导致市场难以统一。这些学者指出,自1980年代初开始,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由纯政治指标转变为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地方GDP的增长,不同地区的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竞争,而且也在“官场”上为政治晋升而竞争。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镇),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因为只有少数人可获提升,一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所以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官场”竞争的逻辑,深刻地改变由官员所主导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和内容: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处于政治晋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员不愿意合作却愿意支持“恶性”竞争的基本原因[13]。基于这种认识,这些学者建议,市场整合必须改革传统的政绩考核机制,淡化GDP指标、强调绿色GDP概念或“根据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或在相同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14]。
如果说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对市场整合有积极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首先,只要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机制,则不管其考核的标准或内容是什么,不管是纯粹的经济增长,还是绿色GDP,抑或是社会、文化发展等其他指标,都同样会导致市场分割,因为现实中有些市场封锁行为就是以保护本地生态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为借口的。
第二,即使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也可能不会有所减少。从比较的角度看,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譬如美国并未建立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机制,也不存在前述学者所说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博弈问题,但这些国家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很突出。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只对极少数人有激励作用,只能保障极少数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目前政制下中央政府用以稳定维系地方与中央关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推荐、委派、任命主要干部担任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并由其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旨意,以确保地方与中央步调一致。但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挑战。根据现有的制度安排,地方行政长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显然,中央推荐、委派与地方选举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另外,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那些流动较强的地方官员,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流动性不强。他们与地方利益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强烈的地方利益面前,中央政府的代理人难以确保中央政府的政令统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政令不统一的真实写照。
第四,虽然该观点所揭示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与地方政府GDP指标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但他们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所揭示出的这种关系的性质即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的结论经不起经验检验,有学者通过经验数据研究得出了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官员升迁“负相关的计量结果”[11]。
(三)司法调节观
与经济学界的观点不一样,政治学、法学界的学者主张通过司法方式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立法、行政方式化解或消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冲突“不见得有效”,而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通过裁决个别纠纷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措施经常涉及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可以抵制地方用各种措施损害全国性市场的统一”。“如果能为合法的私人利益提供有效的救济”,则“在千百万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中,在众多法院司法过程中,在无数的案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审查,使得所有法院都成为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守护者”[15]。有学者还主张设计出一套包括撤销地方政府违法行为、变更地方保护行为的内容、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施加惩罚性赔偿责任、追究地方政府决策者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等在内的法律责任体系,以抵消地方保护行为实施者和受益者从这些行为中所获得的利益[16],进而达到维护市场统一的目的。
确实,从法理层面分析,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卡,大凡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得到有效解决的纠纷,最终都希望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获致解决。所以,理论上,司法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市场统一的最有效手段,实践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如美国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制就是经由司法审查实现的。然而,一旦回到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司法方式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并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情。“因为我国的法院系统是高度地方化的,法院不能在判决中宣布地方性法规的无效,不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不指望从法院获得救济,目前我国的法院也不能提供这种救济”[15]。显然,寄希望于一个本身就有缺陷、就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的制度去遏止另一种制度弊端,不仅缺乏逻辑自恰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会产生危害,即将原本有一点独立品格的司法机关拉入“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泥潭。
其次,对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提出诉讼,以人们能够发现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即容易举证为前提条件。但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隐性措施,往往是只做不说,故意拖延等。行政措施公开性不强、透明度不高,证据难以获得,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功能的发挥。
第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遏制主要靠私人当事人的力量,靠“千百万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不是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对抗来实现的。那么,是否有“千百万人”关注自身利益的人愿意“挺身而出”,就成为司法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是否有效的关键性因素。根据欧、美的经验,凡对政府提出诉讼的,都不能从政府手中获得损害赔偿(因为这将威胁到政府的财政而影响其公共服务能力),只能获得禁令救济。易言之,提出这种诉讼的私人当事人并不能从这种诉讼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实惠,甚至可能会因提出诉讼而遭受财、物、时间方面的损失。显然,这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公益诉讼。
第四,禁令救济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其所属官员都不是严厉的救济措施,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违法行为人对法律的尊重。如果当事人不遵守禁令(在我国可能较为普遍,如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而又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则这种救济措施也是没有很大用处的。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涉及财税法(分税制)、行政法(公务员制度)、诉讼法三个法律层面,除司法规制观直接指向市场分割行为之外,其他两种观点虽然主观上具有标本兼治、彻底根除地方保护主义之目的,但事实上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制只具有间接意义。所以,目前学术界对规制地方保护主义措施的研究仍然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三、市场统一基本制度之反思和重构
理论上,具有中立、开放品格的竞争法律制度是维护市场统一最直接、最有效的因而是最理想的制度,因为,竞争法是市场经济之基本法,它以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为其主要价值诉求。而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才能实现,市场分割毫无疑问损害了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进而违反了竞争法律制度,所以,竞争法律制度可以而且应当对市场分割行为进行规制。我国目前主要是依靠竞争规则来维护市场统一。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已废除),以“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和第30条对地区封锁作了禁止性规定。2001年,国务院又专门颁发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第303号令),对地区封锁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细化。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也对如何规制地方保护主义作了明确规定。上述四个法律文件,尽管颁布的具体时间背景不同,但对那些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特别是地区封锁行为都构成了有力威慑。不过,从经验层面考察,这些规则在维护市场统一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上述四个法律文件都没有明确将保障自由竞争、维护市场统一作为其立法目的;其次,这些法律文件主要适用于商品(包括服务)流动,没有涉及人员、资本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第三,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只限于政府的作为,而不规制不作为。正是由于立法存在前述缺陷,诸多国内贸易壁垒特别是人才流动壁垒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消除。所以,要使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全国市场获致真正统一,有必要重构市场统一基本规则。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欧美用以维护市场统一的基本制度有自由流动规则(free movement rule)和竞争规则(competition rule)。其中前者以禁止各成员制定妨碍共同体内部市场统一的歧视性措施,如对共同体内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的流动施加数量限制或征税为已任,后者则侧重于规制政府机关或市场主体限制竞争、分割市场的行为。这两类规则往往并存于一个共同体的同一部法律文件尤其是宪法性文件之中,但实践上各有侧重。美国主要依靠自由流动规则即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中的“隐性商业条款”(dormant commerce clause)保护市场统一,其竞争规则虽然也在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商业条款是竞争规则的法源,故商业条款是美国规制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法律依据[17]。而欧洲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欧共体条约》第一编、第三编中的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规则也在统一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欧共体的市场统一主要是通过其竞争规则即《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82条、第86条来推动的。美国学者格伯尔曾经指出,在欧洲,竞争法是“规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核心手段”,是欧洲一体化过程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一体化和让人们对欧洲制度产生信心的'发动机'”[18]。竞争规则之所以在欧共体市场一体化过程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竞争规则所具有的中立、开放品格,赢得了成员国的尊重和服从[19]。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维护市场统一的成功经验,重构市场统一基本制度。
(一)在宪法中增加自由流动条款
自由流动条款,是用以保障商品、人员、资本、服务在共同体内部市场能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则。商品、人员、劳务、资本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的基本含义一是自由,二是公平,因此,竞争得以展开的首要条件就是商品、人员、资本、服务能够自由流动。只有商品和其他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其效用才能被最大化,市场实现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才能实现。另外,商品、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动本身也是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虽然多数人特别是经济学者将市场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最理想机制,但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目标绝对不只限于经济增长,它还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政治自由等多重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市场机制对高速经济增长和全面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已经得到广泛、正确的承认,但如果“仅仅在衍生的意义上理解市场机制的地位”,则“是一种错误”,“交换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是重要的,但与交换自由—词句、物品、礼物—的直接意义相比,它只是次要的”[20]。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动因或近期目标也许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但伴随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对自由价值的认知和关注将超越其工具性意义,而逐渐转向于尊重自由的目的性价值,并最终转换成为法律上的诉求。
1.自由流动规则的地位。自由流动规则应当在宪法性文件中加以规定,这是各经济共同体较为一致的做法。欧共体中的自由流动规则规定于《欧共体条约》第三部分“共同体政策”的第一编“商品的自由流动”和第三编“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中,而美国关于自由流动的规则即“商业条款”规定于联邦宪法第1款第8款之中。除美国、欧共体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土耳其也在其宪法中(1982年宪法第167条第2段)制定了自由流动规则: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提供并改善正当的运转正常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信贷与货币市场,并为了实现该目的,避免市场中出现实质的或契约性的卡特尔协议与垄断[21]。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建立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关键是应该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明确写入维护国内统一大市场,即维护国家内部的产品、劳务、人员和资本四大自由流通”[7]。之所以要将自由流动规则作为宪法规则加以规定,一方面是因为自由流动规则所保护的自由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只有将商品、资本、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上升为宪法权利,才有可能对分割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进行有力规制。基于此,本文建议将宪法第15条第3款修改为:“国家保障商品、人员、服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我国自由流动规则缺位这一缺陷,另一方面也可为竞争规则的有效实施提供宪法保障。
2.自由流动规则的基本内容。自由流动规则的核心内容,即禁止地方政府限制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妨碍市场统一。这里所说的“地方政府”,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各类地方机构,也包括特别行政区。目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虽然在政治上已回归祖国,但在经济上,两岸三地尚未形成统一市场。譬如,内地居民不管是去港澳,还是去台湾旅游,都必须缴纳相关费用,办理证件。所以,应考虑通过自由流动规则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市场建成全国统一市场。这里所说的“限制”,既包括直接禁止,如交通封锁,也包括间接限制,如对外地商品、人员、服务或资本施加额外的税收负担、收取额外费用,或给本地商品、人员、服务或资本以税收优惠等,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地方政府实施的公开的、直接的、有形的限制逐渐越少,而暗中的、间接的、无形的限制却在不断增加。自由流动规则的内容必须体现这种变化。
自由流动规则包括商品自由流动规则、服务自由流动规则、人员自由流动规则、资本自由流动规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虽然同属于自由流动规则体系,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和交叉,但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商品的自由流动,一般通过竞争规则来保障,而服务的自由流动,有些可由竞争规则来保障,有些可以由资本流动自由规则来保障,可能还有一些需要专门的服务自由流动规则来保障,所以,在服务领域,会较多地出现法规竞合的现象。资本的自由流动,主要是通过银行法、证券法、投资法等法律制度来保障实现。目前,在商品、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方面,我国都制定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当然,这些法律制度还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这里要特别强调制定人员自由流动规则的重要性。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员的自由流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每年有近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劳动力在源源不断地自由流动。其它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等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至少在10%以上,而我国的人口迁移率只有4.99%[22],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人才流动方面,我国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有一项调查表明,在42种地方保护形式中,阻碍人才流动是最为严重的保护形式[23]。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定价和优化配置,需要以人口的迁徙自由来保证。农村与城市之间巨大贫富差距的缩小必须以迁徙自由来保障[24]。因此,修改《公务员法》、《就业促进法》,制定保障人才自由流动的规则,既是完善促进市场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必不可少的举措。
3.自由流动规则的例外。正如同自由本身将受到限制一样,商品、人员、服务、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在一个共同体内部,还有其他一些价值如公共安全与秩序等比自由更为重要,所以商品、人员、服务、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必须受到限制,譬如在发生重大疾病如SARS、禽流感这类疫情时,政府可以对商品、人员等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在国际货币收支严重失衡时,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必须受到限制。这就是自由流动规则的例外。为了防止自由流动例外规则的泛化,立法必须明确列举自由流动规则的例外情形,如(1)基于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需要;(2)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3)基于维护公序良俗和文化的需要,等等。同时对自由流动例外规则的适用也应施加诸如比例原则等原则性限制。
(二)竞争规则
如前所述,在统一市场方面,竞争规则在不同共同体内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欧洲市场统一的过程中,竞争规则起着核心作用,所以,不管是原来的成员,还是新加入的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欧共体竞争规则,即《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约束。美国维护市场统一的主要法律规则是宪法中的隐性商业条款,大部分破坏市场统一的地方保护主义案件都是根据隐性商业条款来处理的。美国的竞争规则—反垄断法根据隐性商业条款制定,虽然在规制地方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我国尚未在宪法中明确制定自由流动条款,因此,目前维护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的任务主要由竞争规则来承担。由于实务部门、学术界对竞争法规制政府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没有达成高度一致,所以,目前关于规制地区封锁、市场分割行为的竞争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需要进一步完善。
1.扩大竞争规则适用于政府行为的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都适用于政府行为,不过两法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反垄断法》所规定的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两者虽然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别,但其共性都只约束行政权力,而对立法权与司法权没有约束,另外两者都只禁止行政作为,而不禁止行政不作为。这种过窄的规定不利于对政府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全面规制。因为,有些限制性规定是由立法机关特别是地方性立法机关作出的决策,如果法律只禁止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而不禁止地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则难以发挥其规制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另外,在企业等市场主体限制、排除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时,如果地方政府不主动制止这种排除行为,则虽然这种行为是由企业作出来的,但其效果与政府的行为一样,所以,竞争规则应当扩大到规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即如果政府不主动,或在接到举报之后不采取措施,则视同违反了国家的竞争规则。
2.明确判断政府行为违反竞争规则的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促进或保护公共利益,政府对竞争进行限制是经常发生的,但并非所有的对竞争的限制都构成违法。究竟哪些行为损害市场统一,哪些行为对市场统一没有损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一个判断的标准。考察域外经验,在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损害市场统一方面,一般有两种方法:平衡分析法和歧视分析法。平衡分析法,也称为不当负担法,就是对限制竞争的法令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法令所创造的公共利益大于其限制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则该法令是合法的,反之则是非法的。由于平衡测试法所要考虑的因素过于灵活,在实践中难以把握,所以很少被人使用。所谓歧视分析法,就是将政府行为对本地和外地企业的影响进行比较,如果政府行为给外地企业增加了额外负担,或为本地企业给予外地企业不能享受的优惠,这种行为就是歧视性行为。虽然歧视分析法所运用的基本手段也是比较,但这种比较分析涉及两个不同的客观存在的空间,即本地与外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国务院第303号令与《反垄断法》中有许多禁止歧视的规定,但并未将歧视作为判断政府行为违反竞争规则的核心标准,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当然,歧视标准的可操作性也是相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规避法律的制裁,所以,在运用歧视分析法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表面,如立法文本,还要深入分析政府行为的目的与结果,即要将歧视审查标准深入至目的歧视与结果歧视层面。
3.建立政府行为豁免适用竞争规则的制度。在对地方政府适用竞争规则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建立地方政府垄断豁免制度。美国反垄断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州行为主义(state action doctrine),即对州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原则上不适用反垄断法。欧共体竞争法中也有国家行为抗辩制度。州行为主义、国家行为抗辩制度的法理依据是主权原则。而对不享有主权的政府机关,如美国的地方政府、欧盟成员国的某些管制机构,则不能享受反垄断法的豁免。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主权由中央政府享有,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包括省级人民政府在内从来就不属于主权单位,即使是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其享有的自治权也是有限的,所以,从主权理论角度考虑,断无豁免地方政府的理由。
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领土比欧盟要广阔,人口比欧盟要多,而且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社会风俗习惯都有很大差异。从政治学上分析,这样的大国应当实施联邦制,因为联邦制不仅更容易满足地方自治的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进而推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提高地方公共产品质量与效率、推动市场化改革过程[25]。然而,我国并不具备建立联邦制的历史、文化条件,有限的几次建立联邦制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为了调动单一政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都赋予了地方政府自主权,并在立法上予以保障。如《预算法》承认各级地方政府有自己独立的预算,《立法法》第63、64、66条明确规定,省级(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税收征管法》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价格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地方定价目录。现实中,大量服务性的收费标准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既然中央政府在政策上与法律上承认了地方政府属于独立的利益主体,那么,对于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即使具有歧视性,也应予以容忍。
第一,市场参与者例外。这里不妨先举一个具体的事例,媒体间或批露,某某市政府出台文件,凡是动用本级财政购买公务用车,必须购买本地企业产生的汽车,或凡是本市所属单位的公务接待用餐,必须购买本地企业生产的白酒,媒体往往将此作为负面新闻地方保护主义案件予以报道。学界对此亦多持批评态度,认为此类文件对于外地的竞争者来说不公平。单从公平竞争层面来评价,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难发现,此时的地方政府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名消费者,他有权决定购买谁的商品,旁人不得强迫和干涉,即使消费者主体是政府也一样,此即消费者的选择权。再换一个角度考虑,地方财政本来大多源于本地企业的税收,原本就是为了促进地方公共利益的,地方政府用来自本地企业的税收形成的财政,去购买本地企业的产品,增进本地的公共利益,符合市场经济中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所以,如果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作出了优先购买本地商品的决定,那么它可以同私人消费者一样不受竞争规则的限制,这在国外叫做市场参与者例外规则。市场参与者例外,只适用于政府自身作为市场参与者之情形,如果政府通过政令的形式要求别人用他们自己的钱购买其指定的商品,如要求市民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的防盗门、强迫购买其指定的企业的香烟,这种情形不能叫做市场参与,而叫做市场规制。在市场规制情形下,如果其规制目的、规制行为或规制结果具有歧视性,则不能豁免适用竞争规则。显然,在适用市场参与者例外规则时,分清政府何时是市场参与者,何时是市场规制者十分重要。
第二,国有经济例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大的难点就在它的核心部门—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26]。此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实践难题。一方面,现行宪法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又往往成为市场条块分割的重要动因,成为行业腐败的重要根源。实践与理论的这种反差似乎表明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但理性地反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悖论。两者的有机结合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就是竞争法律制度的合理运用。首先,对于那些竞争性的国有经济(工程机械、房地产、汽车制造等),国家能够退出的应当尽可能退出,如果不能退出,就必须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地适用竞争规则。其次,那些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行业的国有经济,往往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即具有不可竞争性,对于这类国有经济,法律可以允许其采取某些限制竞争行为,豁免适用竞争规则。不过种豁免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此类限制性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这种授权并不一定是法律强迫国有经济一定要从事某种限制竞争行为,只要法律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可以采取某种限制行为即可。即使这种法律是某些企业或利益集团寻租立法的结果,该条件也算得以满足。第二,必取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机关对国有经济的这种行为进行主动监督。所谓主动监督是监督管理机构采取了积极的作为行为,被动、依申请的、或不作为的监督,不能算符合该标准。第三,此类国有企业的财务必须透明。包括高管工资,国家补贴等。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国有经济才能获得豁免。《反垄断法》第7条关于“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的规定与反垄断法中的其他规范并不协调,因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反对垄断、促进竞争,而不是反对竞争、保护垄断。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也很少有国家在反垄断法中明确表示保护国有经营者,因为这种规定不仅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反倒使人觉得立法者在有意偏袒国有企业,甚至是在为国有企业滥用其垄断行为提供某种借口。为了消除社会各界对《反垄断法》第7条的误解,有必要将该条修改为国有企业适用除外条款。
四、实施市场统一基本规则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有力实施,则不过是供人观赏的“花瓶”。然而,在实践层面上,法律规则的实施往往比规则的制定更为困难。特别是,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直接以地方政府的规制行为为规制对象,因而这种规制的实施更是难上加难。究竟怎样才能使市场统一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学术界曾经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笔者基本赞同,在此不再赘述,但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要用战略眼光看实施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重要意义
稳定维护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平衡,对于巩固和稳定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对于大国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政制下,维护地方政府积极性与中央权威之间平衡的杠杆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事,即由中央向地方委派、指派地方行政长官来保障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二是财政,即中央政府通过掌握财权来控制事权。这两种手段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中央的权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经济不能实现持续发展,中央财力减弱时,中央政府调控地方的能力也可能会随之削弱。所以,虽然控制人权与财权是维护中央权威,进而统一市场的重要手段,但仍不是长久可靠的手段。市场统一基本规则具有稳定平衡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功能,是加强中央政府影响力和权威的新举措。通过市场统一规则的实施,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将地方政府间的纷争纳入法治轨道,提高中央政府依法解决地方政府间纷争的能力,而且通过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树立了中央政府依法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权威。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地方政府人权、事权、财权等逐步扩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建立新的加强自身权威的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无疑具有战略意义。另外,在台湾与大陆难以就统一事项达成政治性一致的情况下,客观、中立、开放、具有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功能的市场统一基本规则,对于促进两岸统一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基于此种分析,中央政府对市场统一规则基本作用的认识,不能再停留在市场规制手段这一层面上,而应当有更长远、更深刻的认识,应高度重视市场统一规则实施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市场统一规则之最高实施机构应当具有唯一性
市场统一基本规则最高实施机构的唯一性,是由该类规则所欲达致的目标决定的。不管是自由流动规则,还是竞争规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禁止市场分割、促进市场统一。市场统一,客观上要求由同一个机构对市场统一基本规则进行解释和适用,否则很有可能政出多门,产生新的市场分割即部门分割问题。所以,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执行权在性质上是不可分的。现行立法显然不符合唯一性要求。国务院颁布的第303号令所确定的执法机关有近10个,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所确定的“上级机关”也不是唯一的。多头执法局面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立法当局没有认识到市场统一基本规则之最高实施机构的唯一性要求,或者虽然认识到了,但不愿意触动现有的利益结构,其中,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要真正建立两岸四地统一市场,就必须下定决心在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实施方面解决多头执法问题,建立统一的执法机构。凭空设想出一个新的执法机构在实务部门的专家看起来可能是幼稚可笑的。顺着立法机关关于分步解决反垄断执法机关设置问题的立法思路,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市场统一规则的实施可能较为合适,毕竟其地位要高于地方政府(反垄断委员会的主任由一名副总理兼任)。不过目前的反垄断委员会在性质上只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难以真正担当实施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重任,所以,必须对反垄断委员会进行重大变革。其中有两点变革必须首先予以保证:第一,反垄断委员会由非常设的议事协调机构改为常设的行政机构;第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授予或委托反垄断委员会审查规范性文件并宣布违反市场统一规则的规范性文件无效之权力。
(三)温和执法应成为市场统一规则之实施基调
市场分割的成因与动机较为复杂,无论是其主观态度,还是客观结果,在伦理上难以找出太多的责难理由。对抗式的纠纷解决方式,过于严厉的法律责任,不仅不利于地区封锁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激化其他矛盾,损害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所以,市场统一规制之实施应以温和为基调。温和执法要求:
第一,不主动审查违反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抽象行政行为。违反市场统一基本规则之行为可以分为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两类。如果对市场统一基本规则的违反只停留在文件上,而没有得到实施,那么,这种违反只具有抽象行为意义,并不会对市场产生实际上的损害后果。所以,对此类行为,执法机关不必理会,这一方面可以节省办案经费,另一方面也可避免不必要的对立。
第二,处理纷争以行政调解或行政劝告为主。对市场统一规则的违反如果已经从抽象行为层面转化为具体行为层面,并有确定的受害人,则应当应受害人(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请求,对具体行为与抽象行为进行审查,受害人只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投诉,执法机关应主动对抽象行为进行审查。对于受害人与违法者之间的纷争如营业损害或财产损害纠纷或其他纠纷,应以调解为主。对于抽象违法行为,以行政劝告为主。行政调解或行政劝告,不仅有传统“集体本位”文化的支持,也契合现代和谐社会理念,还可以克服执行难问题。
第三,法律责任以发布同意令为主,辅之以禁令。目前立法规定的责任形式有“责令改正”,或给“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有人指出,这种责任形式不足以对违法行为人构成威慑,因而主张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举。考察域外立法经验,既有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如美国,也有追究行政责任的如欧共体,还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如俄罗斯,但基本没有三责并举的立法例。总体考察,欧美对违反市场统一规则所设置之法律责任以禁令为主,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为辅。这种立法安排,主要是为了防止过重的行政责任或财产责任损害地方政府及其官方为其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创造性与服务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因害怕担责而不愿提供对居民有益却可能(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少)受到市场统一规则审查的服务,则地方政府的地方服务功能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除了民事赔偿之外,对违反市场统一规则的法律责任的设计应尽量避免使用财产责任,也应尽量避免使用惩罚性责任,应以恢复自由市场为其主要功能。如果通过行政劝告等方式能使违法行为人主动修改或废除相关文件,则可以以同意令形式结案。对不听从劝告的,可以发布禁止令。对拒不执行禁止令的,再追究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五、结语
自由流动规则与竞争规则是市场经济大国维护市场统一不可或缺的制度。它们不仅具有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而且对于文化融合与政治融合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实施联邦制的大国,制定完善的市场统一规则并保障其得以有效实施,对于建立长久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全国市场的真正统一,意义重大。虽然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维护全国市场统一的制度,但该制度从文本到运行都还有很多缺陷,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予以重构、完善。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个人拙见,但研究视角、所提观点可能有点片面或理想化。譬如本文虽然将论题定为市场统一,却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地方政府行为层面,而对如何规制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各部门妨碍市场统一的行为(这无疑是我国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没有作任何正面的讨论。笔者的观点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出台的限制性规定绝大多数最终得由地方政府来实施,所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可以达到间接规制中央政府各部门行为的目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有待于实践检验,也期待同行指正。
[1]汉密尔顿,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7,216-217.
[2]郑鹏程.论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J].中国法学,2003,(5):114 -12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
[4]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J].经济研究,1990,(3):12-19.
[5]银温泉,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经济研究,2001,(6):3 -12.
[6]楼继伟.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关键是实行经济性分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1):16-20.
[7]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4,(1):56-65.
[8]闫坤.财税改革30年:分税制改革的评价与展望[J].经济要参,2008,(51).
[9]周波.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方式演进、面临问题及对策建议[J].改革,2008,(3):58-64.
[10]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03-111.
[11]杨其静,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J].经济研究,2008,(1):99 -114.
[12]何智美,王敬云.地方保护主义探源—一个政治晋升博弈模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9(5):1-6.
[13]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6):33 -40.
[14]皮建才.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2008,(3):115 -124.
[15]刘海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J].法学研究,2004,(5):36 -44.
[16]吴睿,唐丽宁.论地方保护行为的法律责任之设定[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3):47-52.
[17]郑鹏程.美国规制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0,(2):91 -102.
[18]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M].冯克利,魏志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19]郑鹏程.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对国家干预的规制[J]. 现代法学,2009,(5):175 -181
[20]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
[21]O Z Gamze.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Turkey[J].E.C.L.R.,1999,20(3):149 -158.
[22]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6):97-207.
[23]李善同等.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经济研究,2004,(11):78 -84.
[24]孟桢尧.让“迁徙自由”缩短贫富差距[N].中国青年报,2006-01-19.
[25]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8-144.
[26]黄范章.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兼论创立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4):5-11.
On Building and Application of Basic Rules for Market Unification
ZHENG Peng-cheng
(Law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Only in an open and unified market can the rare sources be optimally allocated.However,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quirement of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single market inevitability generates local protectionism in a big country.Academic viewpoints on how to overcome Chinese local protectionism such as establishing fiscal federalism doesn't get the rules which can directly strike against protectionism,and some viewpoints like judiciary's intervention are obviously unrealistic.Free movement rules and competition rules which are of both open and neutral might be the most suitable means that overcome market separation and keep the market unification.Consequently,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reconstruct and reform the rules of market unification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general,and should add a free movement clause in 1982 Constitution,extend the cover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governmental behavior.
market blockade;market unification;free movement rules;competition rules;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DF411
A
1002-9753(2011)08-0001-13
2011-03-16
2011-06-02
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竞争法与竞争政策。
(本文责编:辛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