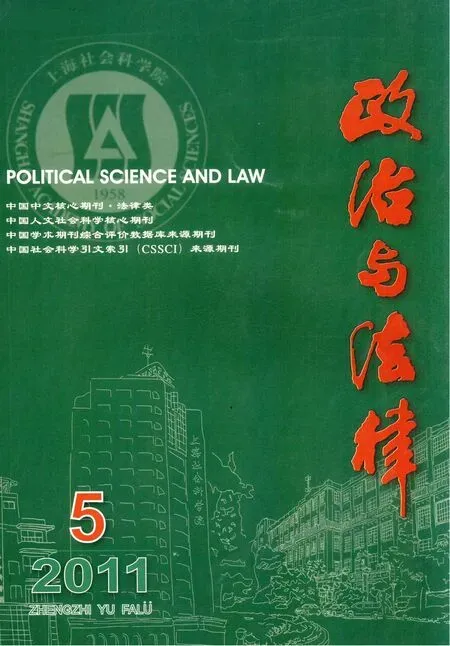司法谦抑主义与香港违宪审查权——以“一国两制”为中心
王书成
虽然“一国两制”这一独具匠心的制度设计已经在香港践行多年,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间也暴露了一些在宪法上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厘清的制度话题,尤其是围绕“一国”与“两制”而产生的诸多争论。虽然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很好地落实了“两制”问题,但是整体来看,港人似乎更强调“两制”,进而对“一国”难免有些许狭隘理解,而在司法实践中间或浮现了些许宪法争议甚而宪法性危机。
一、“一国两制”下的宪法性危机:从马维騉案、吴嘉玲案到中铁刚果案
虽然“一国两制”构想在《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之后由于英方构画“民主改革”等阴谋,1企图潜在阻止中央政府收复香港,而使得本来就需要不断实践探索的“一国两制”增添了些许艰难。1997年发生的马维騉案使“一国两制”中的宪法问题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此案中,被告被控告触犯了一项普通法的刑事罪行,由于聆讯在回归前已经开始,而在回归之后,被告便以所涉罪行的普通法并不是香港法律为由,挑战香港法院审理该案的管辖权。其所持主要论据为,《基本法》第160条规定之意旨是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香港立法会主动确认之后,原有普通法才可以被采纳为香港特区的法律。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作此确认,而且通过《回归条例》的临时立法会(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 l)又属于非法组织,因此该案所涉的普通法并没有法律效力。当然,上诉法庭最后裁定认为,《基本法》第160条并没有规定回归前的法律必须经过主动确认才有效,而且香港法院也没有司法管辖权去质疑设立临时立法会的全国人大的决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否符合《基本法》。2饶有趣味的是,虽然陈兆恺法官在遵守“一国”的前提下认为,地区法院(regional court)没有管辖权来审查主权者(the sovereign)的立法或者法令,进而在该案中当然就不能挑战全国人大设立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解决方法或理由的有效性,因为其属于主权者的行为,其不能受到地区法院的挑战,从而法院也便不能对主权行为中所设立的临时立法会进行任何质疑。但接着他又特别强调,特区法院有司法管辖权来审查主权者或其代理机构的行为是否存在(不是其有效性)。这种审查是法院必须履行的一种职责。就该案而言,特区法院则有权审查:(1)全国人大设立或授权设立该筹委会的决定或决议是否存在;(2)筹委会设立临时立法会的决定或决议是否存在;(3)筹委会是否已经在事实上设立了临时立法会,以及该临时立法会是否在事实上是根据全国人大和筹委会的决定或决议设立的。3由此可见,法院在该案中一方面基于“主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为持一种谦抑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进行一定的权力保留,而确认其可以在个案中对主权者的法律或行为是否存在进行“事实审查”,尽管不可以进行“法律效力审查”。
虽然马维騉案也带来了一些关于香港法院是否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宪法争议,但整体而言,法院对于国家层面主权问题的明确谦抑姿态并没有扩散这场宪法性危机。但是,1999年发生的吴嘉玲案,4可以说彻底在“一国两制”下挑起了一场宪法性危机,且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方法而草草收场。法院基于《基本法》第19(1)条、第80条所规定的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明确指出,香港法院有权审查特区立法机关的立法或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如果有抵触,则可以宣布其无效。而且行使这种司法管辖权是法院责无旁贷的责任,没有任何裁量的余地。那么,法院当然也可以在《基本法》之下履行对立法及行政进行制衡的宪法角色,从而使其符合《基本法》。5虽然与马维騉案一致,法院也否定了当事人对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挑战,但是问题在于,法院在违宪审查权的范围上能动地向前又迈出了“一大步”。终审法院李国能大法官在判词中写道: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57和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是常务委员会,二者行使国家立法权,因此他们的行为属于主权行为。特区法院审查上述二者之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来自于主权,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31条制定了特区《基本法》。《基本法》既是全国法律,也是特区的宪法。和其他宪法一样,《基本法》既分配权力,也界定权限,并且制定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区法院在高度自治下享有独立的司法权,那么特区法院当然可以决定由此而产生的与《基本法》相冲突的问题,因此也可以决定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行为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尽管其也受制于《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由此,特区法院当然具有管辖权去审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在发现与《基本法》相抵触时,可以宣布其无效。6更为积极能动的是,终审法院明确对上诉法庭在马维騉案中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行为是主权行为”的结论进行了否定,而认为法院对其具有违宪审查权并宣布与《基本法》相抵触的行为无效。
法院这种以“国家主权”为后盾并以《基本法》为“依据”的司法推理及判决,立刻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激烈批评,并迫使新华社以新闻稿的形式明确指出,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7以肖蔚云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更直接地指出,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不是终审法院的权力。因为根据《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特区立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认为特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关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不符合《基本法》,可将有关法律发回。同时根据《基本法》第160条,香港原有法律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同《基本法》抵触外,采用为特区法律。这些都表明审查香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在特区终审法院。这样便更谈不上由香港法院来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否符合《基本法》。8这种立场无疑又明确否定了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最终,可能迫于宪法性危机带来的“政治”压力,使得终审法院应律政司的要求罕见地就它之前作出的判词进行了“澄清”,表明其判词“并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9虽然法院所采取的政治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暂时平息了这场宪法性危机,但是政治上的较量并没有使得“一国两制”下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权究竟该如何定位在学理上得以澄清。也许是缘于学理上的混沌模糊,香港法院在触及这一命题时,看似在《基本法》之下轮廓清晰,实则摸不着头脑。2010年发生的中铁刚果案10使得香港法院又一次卷入了一场潜在的宪法性危机。在该案中,由于先前刚果民主共和国于80年代向南斯拉夫公司(Energoinverst)借巨款发展水电工程,之后于2003年在仲裁中败诉,接着则由美国对冲基金(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来承接追索此判决的债务。后由于获悉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中铁(香港)等公司在刚果取得采矿权,但要支付逾2亿美元的入场费给刚果,该基金遂申请在香港执行原仲裁判决,要求法庭禁止中国中铁付款给刚果,而将采矿入场费用作抵偿原先债务。一审法官认为,该案所涉为国家间行为,不是商业行为,因此根据“国家主权有限豁免原则”,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从而判决刚果胜诉。但在上诉过程中,上诉法庭法官则指出,除了1978年英国立法将主权国豁免权的法律扩展适用至香港外,回归之后一直没有全国性法律,因此香港得遵循普通法,沿用英国的“有限豁免权”原则,进而改判基金方胜诉。同时法官也指出,中国已于2005年签订支持“限制性豁免权”的《联合国国家及财产豁免权公约》,尽管至今尚未生效。而刚果方作为另一方当事人,对此则以《基本法》第十九条进行反驳,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而且期间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曾两次发信重申中国的立场是奉行“绝对豁免权”原则。11虽然国际法学者围绕“主权豁免”也发表了诸多看法,但是案件的命脉在很大程度上仍盘旋于香港法院在“一国两制”下的宪法角色问题。就法院将外交部所发表的中央立场置若罔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与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权的限度相关。
这三起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度不同的宪法性危机,颇具典型性。一方面,通过这些宪法性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和领悟到香港法院基于“两制”所呈现的政治情绪,时而激情似火而后又不顾自身的司法权威忏悔式地发表“澄清”,时而又不顾风险再次高扬姿态将中央表明的立场弃之不理;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香港司法权乃至违宪审查权在“一国两制”下角色扮演的制度困惑,时而倾向于“一国”,时而倾向于“两制”。虽然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或说教,但在一定程度上尚未给香港法院带来知识性启发,否则,香港法院何以又一次身不由己地陷入中铁刚果案带来的潜在性宪法危机呢?从香港的角度来看,吴嘉玲案中的“澄清”足以表明了香港既想维持自身的司法独立乃至普通法制度,也不想在国家层面发生抵触。只是穿梭于两者,时常是棋局难定。这也说明关于香港违宪审查权的知识创造任务尚未完成,仍须为此进一步探索,进而逐步形成与“一国两制”原理内在契合的香港司法哲学。
二、“一国”与“两制”下之香港违宪审查权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一国两制”在很大程度上意指香港在一个主权之下实行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普通法制度。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当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以及案件终审权。但是,对于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权的形态则存在不同的解读。总体来说,内地学者一般从一国主权的角度来解读。如有学者指出,香港法院享有司法违宪审查权的前提在于其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的。12也有学者从主权理论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含义非常明确,即香港的“高度自治”来源于主权政府的授权,无疑是“主权——授权——高度自治”的理论进路。由此,对于以《基本法》为基础的违宪审查,原则上应该坚持主权者“解释”,即第158条规定的“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此外只是有限地授权香港进行违宪审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而排除对中央事务的解释权以及对中央和特区关系条款的解释。13这种从“一国”主权角度对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定位,无疑体现了一种以主权为原则而以特区为例外的双轨违宪审查制度。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香港违宪审查在常态下的出场者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作为例外的特区法院。诚然,这种解释中的授权理论不存在争议,但是存在的缺漏在于其混淆了授权主体,而且对“一国”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两制”。首先,既然全国人大(并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也具有约束力。而《基本法》明确地授权香港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解释,那么当然暗含一种违宪审查权。既然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及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要遵守,那么何以见得香港法院基于授权进行的违宪审查就该是有限的,或者是例外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解释就该是原则的,或者是常态的?以上论断在学理上显然解释力不足。其次,既然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是“高度自治”而且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要遵守这种“高度自治”并以此为界,照此,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解释当作原则而把特区的解释作为例外就不违反全国人大在《基本法》中对于“高度自治”的规定吗?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反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当然有可能,况且根据现行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无权制定基本法律。再次,根据《基本法》,香港实行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普通法制度,那么实践中进行司法审查的常态主体当然是香港法院,而不可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又怎么可能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司法性解释成为原则呢?再进一步,这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为“原则”就不会对“两制”下的香港司法独立及终审权构成威胁吗?也许这种通过主权理论的解释性学理可以给全国人大常委在《基本法》的解释上提供一种主导香港法院的依据,但是从香港的角度来看,其并不能“以理说人”,因为在吴嘉玲案中,法院正是根基于主权理论以及全国人大的授权理论否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为,其中的推理逻辑与上述主权理论的解释进路在很大程度上并无二致。
反过来,从“两制”的角度来说,既然《基本法》已经授权香港实行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普通法制度,那么依此“授权”,香港法院完全有理由沿着普通法制度继续向前。作为普通法制度内核的判例法制度当然也要继续存在。遵循这样的制度逻辑,从判例法的角度来看,在香港回归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司法审查权。在1991年R v.Sin Yau Ming14案中,上诉法庭认为《危险药品条例》的部分条款因违反了《人权法案》和《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无罪推定条款而无效。这虽然并不算是实质性的违宪审查,因为并没有涉及香港殖民时期的宪法——《英皇制诰》,但是无疑已经潜在地宣示了其所具有的违宪审查权。其后,在The Queen v.Lum Wai-Ming案15中,上诉法院首次行使了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权,审查了修订后《危险药品条例》的部分条款(1992年6月26日生效)的合宪性。在1994年的R v.Chan Chak Fan案16中,法院又进一步发展了违宪审查原则,指出“《英皇制诰》禁止立法机关制定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在香港适用的法律,而《人权法案》是该公约在香港适用的产物。法院作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者,应推翻任何因违反《人权法案》而违宪的立法。并且,违宪审查的标准与《人权法案》审查的标准一致”。17由此可见,遵循普通法的制度传统,香港法院当然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且与其所享有的司法独立及终审权相辅相成。那么基于此,香港法院在吴嘉玲案中的判决难道具有普通法上的正当性?如果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看,即使吴嘉玲案中的判决有违反《基本法》的嫌疑,那又如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不会对香港的司法独立乃至违宪审查权构成干涉呢?且这种解释也正是香港民众一直批评的对象。
因此,从“一国”及“两制”角度来看,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知识及方法上的模糊之处,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当然这种现状也有其存在的客观缘由,因为现有司法权的经验模式并不能完成“一国两制”创举下的知识任务。当然值得肯定的是,不管从哪种角度分析,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客观存在的,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高度来恰当地为“一国两制”下香港违宪审查权进行定位,使其既不偏于“一国”,也不单执于“两制”。
三、香港违宪审查权之“一国两制”定位
纯粹从普通法的制度逻辑来看,香港法院在案件中所行使的违宪审查权具有正当性,但在“一国两制”之下,必定具有其特殊性,否则也不会出现如吴嘉玲案中的宪法性危机。就如同香港回归前受到英国殖民政策限制一样,回归之后的违宪审查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一国”的约束。由此,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宪法定位必须在“一国两制”下进行。
首先,既然香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区,那么其基于普通法制度所享有的违宪审查权必然区别于国家形态下的违宪审查权。从司法违宪审查的国家形态来看,现代司法权作为单独的国家权力当然可以审查其它国家权力行为,其中包括对立法行为的审查从而纠正立法过错,同时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民主制度下的多数人暴政。然而,既然香港不属于国家范畴,而是国家下的一个特区,那么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权所依据之“宪”以及所依“宪”进行审查的对象必定也要限定在特区范围之内,而不能逾越至国家层面,否则香港将不再属于“特区”,而成为一个“国家”,其违宪审查也将超越特区而逾越至国家层面,这将明显与“一国两制”相悖。既然在特区范围内,那么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所依据之“宪”必定是作为特区宪法的《基本法》,而不可能是国家层面的宪法,同样其审查对象也必定要限定在特区范围内,即审查香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而不能逾越至国家层面去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或其它行为。由此可见,香港法院在吴嘉玲案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为进行“违宪审查”,无疑已明显违反了“一国两制”原则。
其次,根据《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在香港所施行的法律的范围限定在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以及属于《基本法》附件三所列举的,或者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附件三中予以增加的那些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全国性法律。由此可见,在一般情形下,香港法院面对的主要是香港特区的法律,而不是全国性法律。但问题是,如果遇到在香港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香港法院基于司法独立以及普通法制度可否对其进行审查呢?同样基于“一国两制”,香港法院当然不能就全国性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违宪审查,否则其司法权将逾越至国家层面。如果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层面的问题,香港法院当然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当然,这并不排除这些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范围内的适用。
再次,既然这些全国性法律可以在香港适用,那么从方法论上来说,法律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暗含着对法律的解释,那么香港法院可否基于司法权自身的特性,在适用全国性法律的司法过程中进行解释性审查呢,或者通过司法过程中的解释来增加或者改变全国性法律的含义呢?从原理来看,这也完全符合司法权的本质。对此须明确两点:一方面,从司法权的角度来说,法院当然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对规范进行一定的理解或解释,这是司法裁量权的内在要求;但另一方面,基于“一国”是“两制”存在的前提,法院解释的目标对象(subject)应该限定为特区内的法律,而非全国性法律,否则又将逾越至国家层面而超越了所授权的范围,即法院可以通过全国性法律来解释特区法律从而完成司法任务,而不能通过特区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包括《基本法》)来解释全国性法律。当然,在通过全国性法律来解释特区法律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对全国性法律的“理解”,那么同样有可能出现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透过这种“理解”潜在地改变全国性法律的内容。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形。如果在理解过程中,既存在“特区法律与全国性法律相冲突”的理解,也存在“两者相互一致”的理解,那么香港法院此时应该采取推定特区法律符合全国性法律的解释方法,尽量避免触及对全国性法律的解释。这样一方面可以完成司法裁判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立法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否则,香港法院虽然完成了司法任务,但会面临侵蚀香港立法权乃至中央主权的危险。当然,如果在理解过程中出现特区法律明显与全国性法律相冲突的情形,其已属于中央与特区关系方面的事务,那么香港法院此时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18
由上可见,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在“一国两制”下具有特定的内涵。然而,《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法院享有终审裁判权,那么如果出现法院通过“终审裁判权”来进行基于个案的违宪审查,且逾越至国家层面,那么又如何解决呢?一方面,既然是“终审裁判权”,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出场是否会违背“两制”下的终审裁判权呢?另一方面,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对普通法制度以及香港法院终审权的尊重,那么又如何避免香港法院的“终审权”不逾越至国家层面而侵蚀“一国”呢?从马维騉案到中铁刚果案来看,所涉宪法性争议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完全消除这些疑惑。为此,既然香港属于特区,对于香港法院的终审权同样需要在“一国两制”下进行理解,否则很难走出困惑。
首先,由于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法院作为特区的司法机关当然享有对案件的终审权。特区之外的任何机关原则上不得对其加以干涉。《宪法》第31条以及香港《基本法》诸多条款都对之进行了明确规定。香港终审法院可以说是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
其次,虽然香港法院在司法层面享有终审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宪法层面具有至上性,因为司法权来自于宪法授权,也具有宪法上的边界。比如,美国各州法院可以作出终审判决,这意味着其对于具体个案来说是终局的,但并不意味着具有宪法上的最高性,因为其仍要受制于宪法层面的司法审查。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如此,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宪法法院等宪法审查机构在宪法层面的制约。如果司法权没有宪法层面的制约,则无异于司法帝国主义。由此可见,法院的终审权在性质上区别于违宪审查权,两者并不冲突。如果简单地以香港法院享有的终审权来彻底排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层面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异化为司法暴政。
在厘清了香港法院司法权在特区以及国家层面的特定内涵之后可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层面所进行的解释并不是对香港司法权或其普通法制度的侵蚀,而是一种宪法层面的合宪性控制。当然,这种合宪性控制一方面必须充分尊重香港法院针对个案所享有的终审权,另一方面其必须限定在宪法审查层面,比如对香港法院所适用的立法或解释进行宪法层面的解释或澄清等等。当然,由于基本法明确规定了香港的特区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控制只能以《基本法》第158条为基础并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来进行,而不能直接对香港特区的立法进行控制。这种合宪性控制对于“一国两制”是必要的。从马维騉案到中铁刚果案来看,特区法院在行使独立司法权过程中,虽然遵循了普通法下的司法独立原则,但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应有的宪法轨道,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可以基本法为依据进行适当的合宪性控制。
在剖析了香港法院终审权、违宪审查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控制权的原理之后可见,目前一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权毋宁说是司法权。19两种说法都具有片面性,因为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第158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控制者角色,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在立法层面对《基本法》的解释,同时也是一种司法层面的合宪性控制。这种解释权兼具立法与司法特性:首先,这种对《基本法》的解释具有普遍约束力,当然具有立法性质;其次,根据《基本法》第158条,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涉及到中央事务等情形,由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那么此时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司法性。但是,基本法只明确将司法权授权给特区法院,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具有的这种司法性权力是否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且与“一国两制”原理一致呢?其实,不仅不悖,反而是完全契合。首先,这种司法性解释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权,而是宪法层面一种特殊的违宪审查权,并不与香港特区层面的司法权存在矛盾。当然,这种司法性解释权根源于国家主权理论以及《基本法》的授权,在性质上截然区别于香港特区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具有行使这种司法性违宪审查权的制度正当性,因为代议机关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自身可以享有一定的司法权,如实行议会主权至上的英国在其议会内部设立具有审判职能的枢密院。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主权的执行者,在宪法层面行使一定的司法性审查权无可非议。再次,这种兼具立法及司法性的解释权完全符合违宪审查权的本质特性,因为违宪审查权本来就是如此,如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不仅体现为司法性权力的行使,而且由于判决处于宪法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其也体现为立法性权力的行使,因区别于普通法院判决的个案拘束力。
虽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双轨违宪审查权已很难通过传统“单一制”或“联邦制”理论予以阐释,但对特区法院终审权、违宪审查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进行宪法层面的剖析之后发现,各种权力在“一国两制”下各居其位、相互共生、互不冲突。如果产生了宪法性冲突,其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权力在“一国两制”中的错位。
四、司法谦抑主义:香港的方法选择
虽然“一国两制”为香港违宪审查权作宪法定位提供了方向,但如果没有相契合的司法哲学,香港法院在已有的制度空间内仍有可能引发宪法性危机。比如在马维騉案中,法院本可以在无须决定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的情形下处理普通法连续性的案件。所有法官也承认,他们本可以在分析了《基本法》第8条、第18条和第160条后立即刹车。代表申请人的李志喜已提醒人们注意“无必要裁定”的危险。然而,法院仍继续决定其他问题。正是这种离题导致法院作出了极具争议性的有关宪法管辖权和人大“主权”的陈述。当然法院的理由是,在法庭上对这些附带的问题已进行过广泛的争辩。另外,如果法院关于第8条和第160条的观点是错误的话,法院对这些附带问题的决定可以为其判决提供例外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法院认为这些问题特别是临时立法会的有效性极为重要而需要做出判决。例如,黎守律法官指出,拒绝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因为这样终审法院和人大常委会便可能失去一个迅速解决此问题的机会。20虽然这似乎体现了法院的社会责任感,但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法院并未认清其在制度中的角色定位,从而出现时而基于民意来积极能动地解决社会问题,时而不顾司法权威进行忏悔式的政治“澄清”,时而置中央政府意见于不顾“我行我素”。虽然《基本法》赋予香港法院将案件提交人大释法的权力,但是上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任13年未曾动用这一机制,而宁愿在制度空间范围内积极能动司法。可以说,香港司法近乎走入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司法浪漫主义。
当然,这种司法浪漫主义的蔓延也有其特定的制度缘由。如有学者指出的,香港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与强度在事实上要远远高于美国的最高法院,因为从香港法官的遴选来看,其选任依据是《基本法》第92条与第88条所规定的专业资格要求与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体制。除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需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备案外,其他法官的遴选基本上由委员会决定。而且,香港立法会不直接修改基本法,所以在司法机构宣告立法会条例违宪的情况下,立法会无法通过修宪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同时,除终审法院与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外,香港司法机构也不受任何其他民意机构制约,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香港选民。21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便可理解香港法院秉持能动司法的制度空间所在。
进一步看,从香港的角度来看,法院能动司法或者反对“人大释法”的理由主要在于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以及法治,认为人大释法会从根本上削弱香港法治,22进而主张香港法院采取司法能动姿态,避免提请人大释法。以上三起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这种倾向。从逻辑上来说,法院通过能动司法来“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及法治”,似乎天经地义,而且这也体现了香港法院在维护社会正义上的责任担当。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能动司法不仅无益于香港法治,反而会极大地损害其法治。这种对能动司法的错误认识已经在实践中损害了香港的司法权威及法治,吴嘉玲案即为例证。在该案中,由于香港法院能动司法而导致其脱离了“一国两制”的法治轨道,从而迫使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进行释法对其进行相应的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的司法权威。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人大释法完全符合基本法,但香港法院的能动司法却给自身带来了负面效应。法院当然不会咎由自取,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法院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钟爱的能动司法恰恰是与法治原理相悖的司法方法。从法治经验来看,司法谦抑主义方为法治正道。
司法谦抑主义一般指法院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应该持一种谦抑的姿态,比克尔更是将其称为司法的一种“消极美德”。23那么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法院在涉及“一国”及相关问题时应秉持谦抑态度,其法治意义在于:首先,司法谦抑与作为前提的“一国”相一致。能动司法往往致使法院逾越“一国”边界,进而影响司法权威。其次,司法谦抑可以避免法院介入政治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巩固。相反,能动司法容易使法院介入国家政治而难保中立。再次,司法谦抑与司法自身的被动审判职能相互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司法独立。司法权的首要任务在于被动地解决纠纷,如果能动司法,虽也可以解决纠纷,但往往容易将纠纷之外的影响性因素卷入司法而影响司法独立。比如,法院在马维騉案中处理了诸多案件之外的因素,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过程。
那么在司法谦抑主义之下,香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于可能属于中央事务或者中央与香港关系方面等事务,或者对于“是否属于”存在多种可能或疑义的,原则上都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处理。当然,在不影响对案件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下,法院也可以回避处理中央或与中央相关的事务,这也是司法裁量权的应有之义。这并不排除法院主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当然,这种司法“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谦抑主义语境中法院对“一国”的尊重。
当然,司法谦抑主义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一国”以及主权理论可以进行任意解释。基于基本法赋予香港保持独特的普通法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过程中同样须对香港司法持谦抑态度,其主要表现为对法院的判决予以尊重,否则同样会反过来影响其主权地位并削弱“两制”应有的内容。从方法上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应该尽量避免涉及香港法院的判决,除非其明显地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事务。在非明显的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量避免作出影响香港司法的解释。由此,一方面与“一国”相互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保护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相反,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持常态下的能动解释立场,即使在基本法的授权范围之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香港的司法权威并弱化“一国”在香港的政治基础。
然而,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谦抑主义有时可能需要一定的非正式沟通机制予以调和,从而获得各自的立场,为谦抑主义的实践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间。当然,如何将这种非正式沟通机制具体化,则存在一定的制度灵活性。比如在中铁刚果案中,外交部两次发函强调中央政府所坚持的“绝对豁免权”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此来表明中央的立场,那么此时在出现法律上的真空而具有一定回旋余地的情况下,虽然香港法院可以进行裁量性“决断”,但谦抑主义方法则要求法院须尊重中央的立场,进而与法治要求相契合。当然,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也可以通过非正式机制来获得中央的立场,从而更有效地践行司法谦抑主义,避免宪法性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
马道立上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后明确表示,法院只可解决法律问题,不能解决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问题,以此来尽力维护香港法治,维护司法独立。24殊不知,法律从来都与政治无法割裂,且法律问题往往就是经济及社会中的问题。25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法院如何担当责任来践行谦抑主义司法哲学。香港法院在制度上的能动可能性,并不代表这种能动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对于香港司法权威的巩固以及法治未来,法院作为司法权行使主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完全脱离“一国两制”来积极能动地抵制“人大释法”,而是要在“一国两制”下遵循司法谦抑主义原理,既以“一国”为前提,也以“两制”为根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宪法性危机,稳妥地推进法治进程。
注:
1参见鲁平、钱亦焦:《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2、3See HKSAR v.David Ma Wai-Kan,(Reservation of Question of Law No.1 of 1997)([1997]HKLRD 761,[1997]2 HKC 315)
4、5、6See Ng Ka Ling&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1 HKLRD 315.
7、8参见新华社:《内地法律专家对终审法院判决的意见》,载佳日思等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第57-58页。
9See Ng Ka Ling&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Clarif ication[1999]1 HKLRD 577-8.
10See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v.Democratic Republ 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2010]2 HKLRD 66.
11《基金告刚果上诉得直》,《东方日报》(香港)2010年2月11日。
12参见胡锦光:《关于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法学家》2007年第3期。
13、19参见陈端洪:《主权政治与政治主权:〈香港基本法〉主权话语的逻辑裂隙》,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年3月11日访问。
14[1991]HKLY 134.
15[1992]2 HKCLR 221.
16、17[1994]2 HKCLR 17.
18这种解释方法在原理上与合宪性推定及合宪性解释方法的逻辑相一致。具体可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之正当性》,《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0参见佳日思:《〈基本法〉诉讼:管辖、解释和程序》,载佳日思等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21参见程洁:《论双轨政治下的香港司法权》,《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22参见易锐民:《香港法律界游行抗议港府释法要求》,《联合早报》(香港)2005年4月8日。
23谦抑的具体内容与美国法院对总统的谦抑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虽然存在本质差别。See Thomas W.Mer ri l l, 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utive Precedent,Yale Law Journal,Vol.101,Issue 5(March 1992),p969.
24参见《马道立:法院不能解決政治》,《明报》(香港)2010年9月8日。
25也有学者通过区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来试图使得香港法院尽量不积极能动于政治领域。参见程洁:《论双轨政治下的香港司法权》,《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 政治与法律的其它文章
- 涉及第三者的防卫行为探析
-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立法若干问题思考*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与近代英国宪政研究”(项目编号:09FXC010)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论英国宪政与城市化对我国的启示”(项目编号:V0857-10)的阶段性成果。
- 难办案件中立法过时的认定主体*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YJC820055)的阶段性成果。
- 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820157)的阶段性成果。
- 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宪政原理*本文系中南大学前沿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服务型政府法制化研究”的研究成果。
-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措施:新型的贸易壁垒*本文是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新型贸易壁垒及江苏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0FXC009)以及江苏省教育厅201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国际环境条约不遵守情事程序研究”(项目编号:2010SJD820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