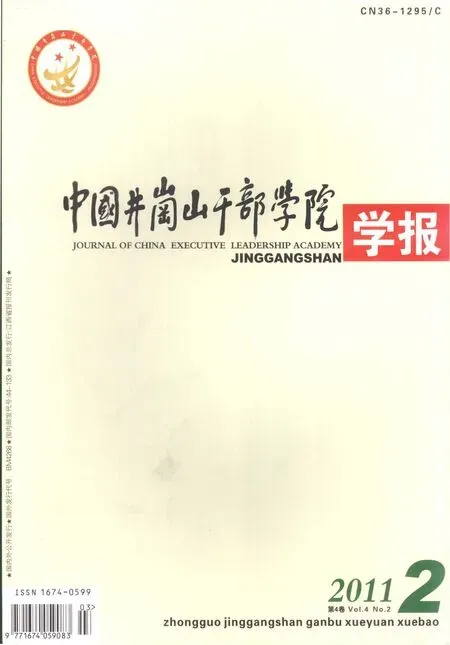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
□阎景堂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 100038)
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
□阎景堂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 100038)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异常艰苦而曲折的斗争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坚决实行战略转变;在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中,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以及建设游击根据地紧密结合;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坚持共产党的旗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在这些经验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经验;党的领导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和中国军事史与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最大特点和与其它战争或战略行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高度分散,各自为战,独立坚持,并由此派生出来的是斗争的极端艰苦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主力红军长征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八省十五个地区坚持斗争,他们分别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展开殊死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无数次的疯狂“清剿”,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给予高度评价:“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1]P399毛泽东也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2]P384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异常艰苦而曲折的斗争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其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历史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审时度势,在历史转折关头坚决实行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重大的战略转变。在这两次战略转变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各个苏区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能否实现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关系到红军游击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分局初期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加之对当时的严重局势和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革命已转入低潮并采取相应对策,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的反攻上;没有从日益恶化的局势出发,及时地转变斗争方式,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而仍然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有的战斗(如谢坊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无法改变当时的基本形势,反而“过早暴露了留守红军主力,引起敌军跟踪决战”。[3]P489后来正视现实,特别是遵照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4]P251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果断地组织部队分九路突围。此时虽然为时过晚,致使部队在突围中损失惨重,但终于摆脱了困境,使斗争出现了转机。
在闽西地区,福建省委同样未能及时摆脱“左”的思想桎梏,没有将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而是将所属的红19团、20团集中在长汀四都一带山区,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形势。结果事与愿违,四都决战,使4000多人的机关、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不幸牺牲。
与此相反,闽北、闽东苏区以及闽西(龙)岩永(定)(上)杭地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由于打破了“左”倾方针的约束,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量,果断地实施战略转变。闽北分区委摒弃了“不失苏区寸土”和“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错误主张并适时地撤出苏区首府大安。闽东特委批判了“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左”的口号,提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5]P60及时地转入游击战争。闽西(龙)岩永(定)(上)杭地区在张鼎丞等领导下,主动放弃大兵团作战,就地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湘赣边的湘赣军区及其所属5个独立团、湘鄂赣边的湘鄂赣军区及其所属红16师、浙南的红军挺进师、鄂豫皖边的红28军等地红军,也都是在初期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一些挫折后,才实现了由集中兵力作战向分散游击的战略转变,从而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
在实现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过程中,项英、陈毅以及大多数游击区的领导人,关注时局的变化,千方百计了解党中央新的政策与策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转变政策。首先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进行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方针的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同时防止投降主义,为实现战略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对谈判条件作某些必要的让步,使之达成有利于共同抗日的协议。在下山改编过程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扎”,严防国民党军的袭击和破坏,警惕其阴谋,从而保证了谈判、改编的顺利实现。但是,在实现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也发生过“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这些右的(如闽粤边的“漳浦事件”等)和“左”的(如皖浙赣边的杨文翰部错杀要他们下山改编的原省委书记关英等)错误,都使红军游击队受到了很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二、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红军游击队在力量弱小、武器缺少且没有补给的条件下,与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长期的周旋,其斗争的艰苦性、残酷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才能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游击战争开始之初,红军部队由于受“左”的军事思想的影响,战术单一,一味强调“强攻硬打,猛打猛冲”,使自身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后来,红军游击队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使情况逐步有了好转。这些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贏就躲”。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不攻坚,“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在战术原则上强调隐蔽、突然、出敌不意与出奇制胜。
为了粉碎敌人疯狂而不断的“清剿”、“堵剿”、“驻剿”、“搜剿”,红军游击队主要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通常采用“设伏诱敌”、“声东击西”、“夜袭智取”、“化装奇袭”等战术,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长,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打击敌人的主要手段。敌人来搜山,游击队就采取打埋伏,截尾巴;当地形有利时,才打整股敌人。敌人重兵“清剿”时,伺机跳出包围圈,避实击虚,奔袭敌据点和后方。例如: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袭击南雄县乌迳镇,闽东红军游击队袭取海港沙埕,闽西红军游击队夜袭龙岩城,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雨夜奔袭安福县洲湖镇等战斗,都是成功的战例。不但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的:“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6]P111
红军游击队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还在于利用各省边界有利条件,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审慎、秘密的准备,与神速敏捷的行动,寻机打击弱敌,设法摆脱强敌。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斗争实践中运用创造出来的许许多多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如鄂豫皖边的“四打四不打”(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否则就打);[7]P88湘鄂赣边的“大游小击”;闽西的“散兵群”;浙南的“兜圈子、‘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等等,[8]P159从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
要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灵活机动的特点,还要处理好藏和打、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藏,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打,是为了坚决地消灭敌人。只藏不打,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只打不藏,则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红军游击队既反对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死打硬拚的冒险主义,又反对消极隐蔽,不敢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保守主义。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以及游击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赣粤边等15个游击区,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土地革命的战斗洗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则是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之本。在那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正是由于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结成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才保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与胜利。正如项英所说:“民众力量是最伟大的。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就是依靠民众力量。若是没有民众的拥护和参加,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不能坚持长期斗争以至遭受失败。”[9]P562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革命群众舍死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的生动而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湘鄂赣边“平(江)浏(阳)铜(鼓)万(载)的群众,他们房屋被烧毁,儿女被杀害,甚至全家遭不幸,也要豁出命来支持革命。”[10]P295对此,陈毅曾满怀深情地歌颂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6]P112
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坚持武装斗争与非武装的群众斗争相结合,是各游击区普遍采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争取群众的第一件法宝就是严明的群众纪律。无论部队怎样苦,决不动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无比信赖。第二是每当攻占一个城镇时就开仓分粮,尽可能地给群众以物质利益。在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五抗”(即抗捐〈或抗丁〉、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使群众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才是代表和维护他们利益的。第三是实行干部地方化,和群众交朋友。游击区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分头深入到群众中去,协同当地干部领导群众斗争。干部地方化,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坚持武装斗争与建设游击根据地相结合,是红军游击队生存之本。没有这种结合,游击区就无法存在和发展。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反过来又支持了武装斗争。斗争实践证明:武装斗争和建设游击根据地结合得好,形势就好;结合不好,就可能招致失败。因此,各游击区都十分重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各游击区开辟根据地的通常的做法是:首先选择群众基础好,反动势力比较薄弱,或敌人较难立足的地区,建立基点村,随后逐渐向其周围扩展,形成小块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积极培养地方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区委),组织群众武装,成立游击队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由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大块的游击根据地。闽东游击区依此法先后建立了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及(福)鼎平(阳)4块游击根据地。他们把这种做法叫做“狡兔三窟”。这“窟”就是根据地。闽北游击区则比喻为“叫花子打狗背靠墙”。这“墙”也就是根据地。他们背靠崇安老区这道“墙”,先后派出三支游击队,开辟和恢复了建(瓯)松(溪)政(和)、邵(武)顺(昌)建(阳)和资(溪)光(泽)贵(溪)3块游击根据地。鄂豫皖边创建的遍布全游击区的百余支便衣队,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鄂豫边游击区通过农民自卫会的组织形式,控制边区基层政权。其他游击区也都通过不同形式,加强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注重了根据地的建设,游击区内的许多村寨,不仅是红军游击队的可靠“宿营地”,而且也是补充给养的“后勤基地”和养伤治病的“家庭医院”,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坚强堡垒和后盾。
四、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发展革命的“两面政权”,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处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斗争环境,而要在这种新的环境里生存、立足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斗争方式、新的斗争策略和新的革命口号。红军游击队面对着强大敌人和各种反动势力,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正确地掌握、分析、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多数,孤立和反对少数,团结和动员群众,瓦解和战胜敌人。而在国民党密布各地的保甲制度中实行“白皮红心”,大力发展革命的“两面政权”,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和采取的一种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保甲制度等问题上,各游击区大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时曾一度采取公开对抗的政策,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把最反动的敌人与一般反动分子以及被迫担任保甲长的人区别对待,一律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树敌过多。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总结经验,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即实行“白皮红心”,大力发展革命的“两面政权”。就是对于国民党基层政权中的联保主任、保甲长,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即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具体做法是:对于作恶多端,坚持与红军游击队为敌,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对于只是应付敌人,且有悔过表现的中间分子,采取争取政策,既往不咎,使其中立,成为“脚踏两只船”的兩面派。对于出身较为贫苦,接近人民群众,靠拢红军游击队,同情革命,被迫担任上述职务的人,则采取团结的政策,使他们逐步成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心”的人,“即挂着国民党的招牌,而为共产党干事情。”[11]P100同时,在一些革命力量较强的地方,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开明人士担任保甲长。采取革命的“两面政权”,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来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斗争。
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扩大和深入开展,各游击区还在实际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政策。闽西游击区提出了“争取壮丁队为农民抗日自卫队”、“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的口号,即所谓“旧瓶装新酒”。赣粤边游击区在赤白交界地域建立了“黄色村庄”(有的地方称“灰色村庄”),进行合法、半合法的斗争,以取得情报联络,获得物资给养。
实践证明,这样做既分化了敌人的营垒,争取并团结了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力量,缩小了对立面,又得到了游击区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使红军游击队不仅站稳了脚跟,求得了发展,而且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五、坚持共产党的旗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运用巧妙的对敌斗争策略,打破敌人的“清剿”,完成两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正是由于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游击战争才得以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红军游击队才具有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决心和坚持到底的毅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长期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独立坚持、各自为战的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党的核心领导作用,集中体现为各游击区的党组织根据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独立自主地领导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这就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斗争的实践证明,项英、陈毅以及各游击区许多党的领导骨干不负党和群众所望,因为他们具有共产党人特有的品格。这就是:首先,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第二,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时局及周围事变发展的进程有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第三,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观察、分析、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和政策;第四,具有发挥集体智慧的领导艺术和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身先士卒的优良作风。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由于敌人的反复“清剿”,战斗频繁,斗争残酷,党的组织经常遭到破坏,一些领导人牺牲了,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叛变了。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首要的任务是要及时地调整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各个游击区根据当时各自的情况,先后重建、新建或调整了省委、临时省委、特委或军政委员会等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游击区内分别设置了中心县委和县委、中心区委和区委,并相应地组建党的基层组织,从上而下形成了党的统一领导的系统。同时根据“统一指挥,分兵行动”的原则,各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区直接领导和指挥斗争。
保持党的旗帜,就必须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游击队的生命线,是红军游击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在长期的“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所处的环境之险恶,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斗争之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红军游击队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于斗争的极端残酷和处境与生活的异常艰苦,一些意志薄弱者、投机者,相继叛变投敌,如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湘粤赣边特委书记陈山等等。他们的叛变曾给各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加强红军游击队内部的巩固与团结,一方面大力开展反叛徒斗争,揭露叛徒们的罪行和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则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反对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斗争”,加強形势教育、理想教育和气节教育。经验证明,斗争越是艰苦,情况越是复杂,实行正确的政策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越是显得重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依靠全体红军游击队员的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战斗中,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许多同志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敌人的监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忠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头可断、血可流、意志不可摧的伟大革命气节,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初期斗争中牺牲的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何叔衡、方志敏,以及贺昌、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方维夏、毛泽覃、梁柏台、李天柱、李才莲、李赐凡、万永诚、龙腾云、刘畴西、寻淮洲等许多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在尔后的游击战争中,各游击区牺牲的主要领导人有:赣粤边的李乐天;闽赣边的赖昌祚;闽粤边的张敏、张长水;皖浙赣边的唐在刚;浙南的黄富武;闽北的吴先喜、黄立贵;闽东的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闽中的王于洁、刘突军;湘鄂赣边的陈寿昌、徐彦刚;湘赣边的彭辉明;湘南的彭林昌;鄂豫边的张星江等,以及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他们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壮举和崇高品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也是党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骄傲。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2]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A].毛泽东选集(合订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5日)[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5]叶飞.叶飞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6]陈毅.游击战争纪实(1936年夏)[A].陈毅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文献资料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林维先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二十八军[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8]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9]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牟12月11日)[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0]谭启龙.三落三起话当年[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1]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
YAN Jing-tang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Military Museum,Beijing 100038,China)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 experienced an extremely arduous and intricate process,having accumulated enriched historical experiences.These experiences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being determined to execut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t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carrying out flexible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s;closely relying on the people,and combining armed struggle with non - armed people’s struggle and construction of guerrilla bases;using artful strategy of struggle,striving for the majority and opposing the minority;and holding up the bann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or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Among these experiences,persisting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historical experiences;leadership of the party
D231
A
1674-0599(2011)02-0050-06
(责任编辑:贺文赞)
2011-01-16
阎景堂(1933—),男,河北内邱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编审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及中国工农红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