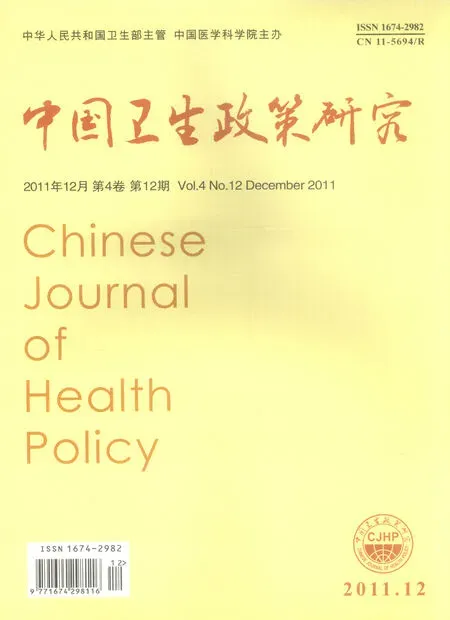试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伦理困境与法律对策——以法定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为背景
殷炳华 易 敏 王 瑛
1.山东警察学院法律部 山东济南 250014
2.山东省军区门诊部 山东济南 250014
3.济南军区总医院 山东济南 250031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这有助于促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严格履行医疗伦理义务、尊重患者的医疗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但是,《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部分简单、概括,乃至有些模糊的规定,也给医疗机构尤其是医务人员带来了诸多的伦理困境,影响了相关规定在医疗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本文拟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并从法律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有所裨益于《侵权责任法》的完善及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1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的伦理困境
1.1 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时的伦理困境
在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医疗告知等伦理性义务,都将面临民事侵权责任风险。因此,履行医疗告知义务不仅成为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需要,而且也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规避医疗伦理责任风险的有效措施。但在医疗实践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却经常困惑于如何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才能做到既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让其在充分了解相关医疗信息的前提下,自主做出医疗选择,又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掉入医疗伦理过失的“陷阱”,而免于承担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国外常见的做法是,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告知义务进行明确且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003年民事责任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医生只有在未告知患者以下风险信息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违反风险警示义务:(1)处于患者立场(patient’s position)的一个合理人(a reasonable person)所需要的信息,以便能就是否接受治疗或顺从建议做出一个合理的知情决定;(2)医生知晓或应当合理地知晓患者在就是否接受治疗或顺从建议做出决定前所要求的信息。美国则通过Canterbury案确立了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告知标准,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行为指引,该标准的内容包括:(1)医生向患者告知信息的范围应以“患者的需求”来衡量;(2)患者所需求的应是对其同意决定具有“实质性”作用的信息;(3)一条风险信息是否属于“实质性信息”的判定标准是,一个处于患者立场的合理人是否对某一信息具有“赋加重要性(attach significance)”[1](该标准被加拿大最高法院、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新西兰患者权利立法吸纳)。
但是,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应该如何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规定的过于简单、概括,对医疗告知的内容、范围、程度、方式以及时间等,都没有明确且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对诊疗行为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指引作用。其结果便是导致这样一个伦理困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要么选择结合患者的自主判断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质性”[2]告知,这样就会因为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可能使自己陷入“伦理过失”,承担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要么选择自我保护,罔顾医疗告知义务的主旨,即让患者充分知情以便理性地自主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不斟酌告知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程度等因素而进行概括地告知,甚至“过度说明”,“将全然不足信的风险,如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或者诊疗失误的危险,都无所不包地列入说明表格中,留待患者签名。”[3]这样就可能导致“告而不知”,或者患者“被知情”,使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受到损害,但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规避法律责任风险有其现实意义。
1.2 知情不同意时的伦理困境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确立了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权,这不仅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阻却侵袭性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提供了法定事由,而且也可体现我国立法对于患者自主决定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提供明确的伦理价值导向。而“知情不同意”实质上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患者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的知情不同意却常常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陷于医疗伦理困境中,艰难地在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自主决定权之间尴尬取舍。
有研究认为,知情不同意是指病人、病人家属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医方对疾病的诊断措施、诊断或提出的治疗方案。[4]《侵权责任法》第55条明确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知情不同意使得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失去了阻却侵袭性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法定事由,违背患者意志实施保护其生命健康权的医疗行为,明显侵犯了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的医疗自主决定权。但在具体医疗实践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相应医疗行为,虽然缺失明确的法律依据,却往往能够获得社会的伦理认同,即所谓的“合理不合法”、“合情不合法”。尤其是在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知情不同意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所面临的这类伦理困境更甚。有关调查显示,“有34.6%的患者知情后不同意的原因是怀疑医生的正确性,19.9%的患者认为医生为赚钱,另有35.7%的患者是因为经济负担不起,而其余9.8%的患者是顾虑家人意见”。[4]针对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主要基于医疗费用的沉重负担和对医生技术水平的质疑而导致的知情不同意,乃至因对医方伦理素养的不信任而产生的知情不同意,凡是理性、有医疗良知的医务人员,面对此类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是顺从其意志放弃治疗,还是违背其意志继续施治,恐怕都会有一番伦理上的挣扎。
在紧急救治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同样难以摆脱相应的医疗伦理困境。尽管《侵权责任法》第56条明确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似乎拥有了法定的实施相应医疗措施的权利,但是,如果医方在实施紧急救治前,已经取得了诸如“近亲属同意,患者不同意”、“患者不能表达意见,近亲属不同意”、“患者及其近亲属均不同意”①如2010年12月在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的孕妇拒绝手术事件,以及2007年11月北京朝阳医院的肖志军拒绝签字为其“妻子”进行手术的事件等。等明显不利于患者生命健康的“不同意”的意见,医务人员仍将面临如何在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与知情同意权,乃至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之间进行抉择的伦理困境。
1.3 法之局限性下的伦理困境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义务是其承担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基础,如果《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义务给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界定,特别是在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就很难摆脱医疗伦理过失的“陷阱”,而只能在医疗伦理困境中无奈地平衡患者的知情权、自主决定权、生命健康权以及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义务方面的规定确有不足之处,削弱了其应有的规范指引作用。
首先,《侵权责任法》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医疗告知的内容、范围、程度、方式、时间等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且可操作的界定。关于医疗告知义务,《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在这里,对于对55.6%“知情不同意”患者起关键性影响的诊疗费用情况、对54.5%“知情不同意”患者起关键性影响的医生个人技术及道德状况[4]以及一般情况下对患者有重要影响的“不实施相关治疗的后果”等内容均没有明确列入医疗告知义务。对于68.3%的患者所关心的医疗告知方式[4]以及医疗告知的针对性、相关性、实质性等都没有定性的要求,而一个“等”字又为“过度说明”、“概括说明”、把医疗告知“异化”为风险转移手段[5]大开方便之门,医疗告知的范围和程度弹性过大。本款在规定“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的时间时,也缺少了向患者说明时“及时”二字的要求。
其次,《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告知对象的转换条件和转换对象的规定不明确。《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在医疗实践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如何判断是否属于“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况,是依据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判断,还是依据医疗信息对患者心理、病情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呢?法律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致使该规定缺少可操作性。另外,对于需要向之说明的患者“近亲属”的范围也应该加以界定,以提高告知效率并免除医方遗漏患者的某些“近亲属”而陷入医疗伦理过失之虞。
再次,《侵权责任法》第56条并未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紧急救治情况下的临床强制干预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仍要在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权、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自身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风险之间的伦理困境中抉择。《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依据本条规定,医方能够取得的“意见”应该包括“患者、近亲属一致同意”、“患者近亲属一致不同意”、“患者和近亲属意见不一致”、“仅有患者意见”、“仅有患者近亲属意见”、“患者近亲属意见不一致”等多种情况。在抢救患者生命的紧急情况下,如果患者知情不同意,且该“意见”不利于其自身生命健康,医方如何行为?此时,近亲属“意见”与患者不一致时如何行为?一致时又如何行为?如果只能取得近亲属“意见”,但其“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医方该如何行为?如果不能取得患者意见,而其近亲属的意见不一致,医方该如何行为?这一切问题都很难从本条找到明确的答案。更何况即使符合了“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这样的要求,经过相关“负责人批准”,医务人员仍是“可以”而不是“应当”“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因此,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紧急救治的情况下是否具有临床强制干预权,尽管学界争论纷纷[6],但《侵权责任法》第56条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
2 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法律对策
2.1 制定明确、规范的医疗伦理行为规范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却没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履行法定医疗伦理义务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规范,使其只能尴尬地陷于医疗伦理困境。事实上,在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困境中,法律对医疗行为选择的影响远远大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因此,针对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的伦理困境,可以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进行司法解释,或者通过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来改变这种状况。用法律形式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如何履行医疗伦理义务主要是医疗告知义务进行明确、规范,包括医疗告知的主体、时间、内容、范围、程度和方式等。具体方式可参照国内外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如“主观医师说”、“客观医师说”、“主观患者说”、“客观患者说”、“共享型医疗决策说”[7]以及关于医疗告知程度的“实质性说”等,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如患者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传统“家文化”影响深远、社会医疗保障机制不健全、城乡差别大等情况,提出明确的、定性化的要求。另外,还要对医疗告知对象转换的条件予以明晰,对需要向之说明的患者的“近亲属”范围和顺序进行界定等。
关于《侵权责任法》第56条,有研究认为“这一规定表明医疗机构可以在患者知情权与患者生命权、重大健康权之间作出符合患者利益的选择,体现了‘生命至上’的原则。”[8]也有研究认为“本条不包括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明确表示拒绝采取医疗措施的情况”,“这个问题情况较为复杂,应当总结实践经验作进一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再作明确规定”。[9]但是作为具体实践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需要的是清晰、规范的行为指引,至少应该让他们明白立法的价值取向。基于此,建议对本条进行修改,并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相衔接,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临床强制干预权,说明在患者需要紧急救治的情况下,当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的“知情不同意”明显不利于患者的生命健康时,经适当程序审核,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对于“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情况,由司法机关对适用本条规定作出司法解释,明确“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这句话,是指“患者不能表示意见且难以取得患者近亲属的一致意见”这种情况。既明晰了行为规范,又体现了对患者自主决定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另外,为了促进医疗技术的进步,可在该条款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行使临床强制干预权时,给患者造成损害的,除非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免予承担侵权责任。
2.2 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
明确的医疗伦理行为规范,使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的伦理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预期性。但是,导致医疗伦理困境的因素往往是多元的、变动的,既有患者经济能力因素,也有患者认知能力、患者心理、医患间诚信缺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公信力、患者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医疗伦理困境的消除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依法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非常必要。
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其主旨在于通过科学、理性、便于操作、有公信力的医疗伦理争议裁决,把医务人员从医疗伦理的个人抉择困境中解放出来。据调查,经“医生多次说明,患者仍坚持己见导致死亡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此时有53.1%的人认为医生不承担责任,有46.0%的人认为医生仍承担责任。”[4]该调查数据表明,尽管患者对知情不同意的态度比较客观和冷静,但完全由医务人员个人来选择方案的行为将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平诊或者实施紧急救治时遇到的医疗伦理争议,应通过依法设置“医疗伦理审核委员会”来解决,以降低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风险。医疗伦理审核委员会可通过立法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经医疗机构申请,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在医疗机构内部设置。医疗伦理审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具备医疗、伦理、法律、社会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并经过严格的道德审查,以确保该机构的公信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依据“医疗伦理审核委员会”的结论从事医疗行为,视为已依法履行医疗伦理义务,将免于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风险。
对于除平诊和实施紧急救治时遇到的医疗伦理争议以外的其他重大医疗伦理争议,如近亲属之可能导致“植物人”患者死亡的放弃治疗、严重缺陷新生儿的处理、住院患者因经济窘迫可能导致自己死亡的放弃治疗等,虽事关患者生命利益,但时间要求并不紧迫,因此,可通过相关司法解释扩大法院受案范围,让与医疗伦理争议行为有关的患者、近亲属、医务人员、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利益相关方均可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通过司法途径对引起医疗伦理争议的行为进行裁判,并借助司法裁判使医务人员摆脱伦理抉择的困境。
2.3 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和医疗伦理督察制度
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制度,是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于患者“知情不同意”可能导致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甚至死亡的情况,医患双方通常都会陷入医疗伦理困境。在医疗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救与不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前所述,针对由于患者坚持己见导致死亡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情况,尽管医生已经履行了充分说明义务,仍然有多达46.0%的人认为医生应承担责任。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制度,就是要通过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严格界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义务,明确“临床强制干预权”或者“救人优先,术后交钱”类的原则性规定,从根源上降低发生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风险的概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扩大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和适用对象,提高理赔率,在最大限度地保障患者利益的同时,有效转移医疗风险,避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了自我保护而选择对医方最安全的保守治疗方案或者放任患者的不明智行为等对患者不利的行为。
依法建立健全医疗伦理督察制度,是减少医疗伦理困境发生的重要手段。结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医疗伦理督察制度,有助于促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严格履行医疗伦理义务、提升医务人员的职业伦理素养、增加患者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信任。据调查,“54.5%的患者把知情不同意的主要原因归于怀疑医生的正确性和认为医生是为了赚钱,并且54%的病人到一家医院看病后又到另一家医院再看,这也说明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4]患者及家属对医疗活动的信任、对医生正直人格的信念及医疗活动所带来的利益都会影响患者对所告知信息的认知。由于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心理上有着下意识的“隐瞒”基础——双方在信息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关系,而在目前医疗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对这种隐瞒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再加上临床中触目惊心的医疗事故和现存的一系列消极治疗(过度医疗、虚假医疗、无效医疗、欺骗性医疗等)更加深了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而信任是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没有良好信任医生就不敢在医疗活动中进行医学技术的探索与创新,就缺乏为患者承担意外风险的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让医务人员冒着医疗伦理责任风险在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自主决定权之间进行个人抉择,无疑会陷入医疗伦理的困境。
[1]赵西巨.论违反告知义务之医疗侵权形态的特殊性[M]//山东大学法律评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赵西巨,王瑛.论美国法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及我国的立法思考[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5(3):178-182.
[3]张谷.浅谈医方的说明义务[J].浙江社会科学,2010(2):7-10.
[4]姜兰姝,杜治政,赵明杰,等.尊重自主权:如何面对患者的知情不同意——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五[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4):37-40,57.
[5]马辉,孙文利.论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异化”[J].法制与社会,2011(3):80-81.
[6]胡晓翔,孔蓬,邹效波,等.《侵权责任法》能否成为维权利器——从“强制干预权”的失范谈起[J].临床误诊误治,2011(4):2-4.
[7]杨玮嶷.医师告知义务的法律解构与重构[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10):49-51.
[8]周婷玉,邹声文,陈菲.侵权责任法能否成为维权“利器”?[N].人民法院报,2010-07-05.
[9]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