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的张力——《北国之春》、《鹿港小镇》中的现代性认同
文/冯 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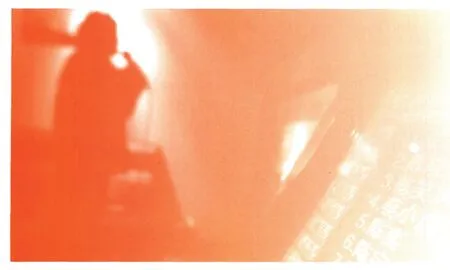
一、卡拉OK、东亚伦理与现代性自我认同
汉学家贝淡宁认为东亚人的卡拉OK娱乐是对儒家礼乐教化传统的现代继承[1](P95、P97)。这种来自“他者”的判断可以给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个别样的观察视野。《礼记·乐记》云:“乐者异文合爱者也。”无论古今中外,音乐都能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情感的直接交流达成共识。然而,一种约定俗成的现代观念似乎把这种“音乐”之“乐”单纯等同于“娱乐”之“乐”,“合爱”的社会功能则被淡化了。现代生活被切割为“娱乐”与“工作”两截,晚上去卡拉OK的人们更多寻求的是对白昼高压状态的“放空”。如果有人在唱歌时依然保持平日的严肃,人们会嘲笑他“放不开”。于是,“放开”、“减压”、“娱乐”渐渐成了“乐”表面上的唯一功能。
即使如此,卡拉OK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合爱”的文化功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传统的东亚儒家伦理建立在义理(礼)与人情(乐)两大始基之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这些古老的理念排空,白昼的现代生活被技术理性与科层制管理模式约束着,人类的自然情感得不到有效的抒发;于是,夜晚的“娱乐”反而是对自然情感的回归,在“放空”的过程里,人们悬置了白昼生活的精神重负,沉浸到人伦关系的脉脉温情之中。此外,东亚人看似对公共事务(福利、治安乃至参与政治)十分冷漠,但实际上“在这种缺乏公共责任感的另一面却是强有力的私人相助的传统,它远比西方任何情况下的意义都更强烈。……仁爱的精神——且经常是非常博大的仁爱精神——存在于东亚,但却往往只针对自己的家族或邻里,而不是泛泛于整个人类社会。”[2](P134)唱卡拉OK的时候,亲情、友情与爱情的主题在宽屏电视上滚动呈现,人们在光影声色的刺激之下让躁动不安的自我获得了情感的扎根。即使接受了全球化的生存方式,传统文化的血缘也无法切断。“仁者亲亲”的古训依然有效。
卡拉OK表面上是为了排遣寂寞而“娱乐”,细究起来则是一种综合的文化仪式,不同种类和风格的音乐携带着庞杂的文化符码,潜移默化地帮助每一个歌唱者实现自我人格塑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卡拉OK和流行音乐进行严肃的分析。文化学家格尔茨认为,对文化的分析应当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对分析对象进行“深描”式的解码和阐释,挖掘其“意指结构”与“概念世界”;这种阐释应当是是语境的、融贯的、微观的,以求达到对“巨大的文化景观”的学术化展现[3]。对于卡拉OK和流行音乐而言,这样的分析必将伴随着对歌曲主题与形式细节的具体把握,进而展开对其语境背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张力的考察。
“现代性”是一个宏大宽泛的理论命题,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其中与“个体认同”相关的方面。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现代”意味着全球化新秩序的来临,这给每一个生存个体带来感官与意识上的强烈冲击。吉登斯看到,这种现代性虽然被认为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4](P1、P3)。传统被内化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其固态的、保守的结构进而变得流动且开放。此外吉登斯也看到,人们的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的普遍化过程是同时发生的,通过每一个人对自我的反思和建构,一种综合的文化生活秩序得到建立。卡拉OK就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建构自我认同的现代“游戏”: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反思性区隔,对梦境般私人体验的审美表现,对作为事件和情景的歌曲的反复吟唱,一种“生活政治”得到发挥,在其中,人们能够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4](P9-10),社会的、伦理的意义进而生成。

为了说明这种“反思”与“认同”的发生机制,我们需要分析具体的卡拉OK文本。这里选择的是《北国之春》和《鹿港小镇》这两首国人并不陌生的经典名曲。由于迎合了时代大潮,《北国之春》(1977)得到日本人民的普遍喜爱,其演唱者千昌夫也在30岁时一炮走红。在中国,这首歌被知名歌手邓丽君、蒋大为等先后翻唱,成为华语流行乐的经典。台湾流行乐教父罗大佑28岁以歌手身份出道,《鹿港小镇》(1982)是他的处女作。这首歌奠定了罗大佑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的音乐风格。把这两首来自不同文化圈但几乎同时代的歌放在一起谈论,并不仅仅因为它们都涉及“城乡”这一现代话题,还因为它们以各自的抒情方式共同体现着东亚文化圈独特的伦理内涵。正如歌词的字面意思所传达的那样,这两首歌具有同一个文学主题:思乡。不同的是,在《北国之春》中,思乡者的故乡是城市,风光秀丽的北方对他而言只是客居之所;而《鹿港小镇》则表现了一个在冰冷大都会中流浪的青年回忆起渔港故里的矛盾心态。这两首歌在情感上是不对称的:《北国之春》的情感直接、昂扬而自信,我们称之为“上升的情绪”;而《鹿港小镇》的情感则是忧郁、愤怒与颓废的暧昧综合,我们称之为“下沉的情绪”。我们不禁思考: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接受这些歌曲的人们又会产生怎样的“认同”影响?

二、《北国之春》:古典自然审美与大地产现代性
历史上,日本曾经有着“神国”的自我认同经验,这种认同的来源于对自然界的感性体验和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接受。子安宣邦看到近代以来“神国”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建立在儒学之上的“神国日本·皇国日本”变成了“诸神之国日本”;这种“诸神之国”是对所谓日本独有的“共同体世界”的理论开辟,是一种意图“构筑与西洋文明和中国文明不同的日本文明史的话语”[5](P123-128)。这种转变对现代日本的美学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诸神之国”的提出意味着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否定,意味着对民间元素的认同。进而,近代以来日本的“物哀”审美就天然融合了一种对民俗、乡野风味的偏好,而其核心的文化精神则是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把捉。在这个意义上,《北国之春》这样的“演歌”得以成功结合“传统”与“现代”,开辟出独特的审美特质,“寒衣”、“饮酒”等等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述对广大的民众阶层构成了情感上的召唤结构。但是,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真的实现了它的原初目的,即对自然、纯美的民间情怀的展现吗?
毫无疑问,《北国之春》的文化原型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无论是“白桦、碧空、南风、棠棣、朝雾”的起兴手法,还是言及父兄家母爱人的“敦伦”姿态,抑或是回环往复的三段结构和“何时可归”的直抒胸臆,都让人体会到这首歌与《诗经》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吟唱这首歌的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儒家文化独特的伦理审美体验中,这也正是这首歌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获得普遍认同的原因。中国文学的抒情性传统在这首歌中得以绵延:一个前往北方大地工作的青年,目睹美好的自然春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用歌唱的形式表达对“家”的怀念。这种怀念集中体现在对“伦理”的凸显上:身处城市的母亲、姑娘、父兄的音容笑貌依次浮现,这让处于流浪状态的开拓者获得了“根”的宽慰。在这首歌里,“城市”作为流浪者的立身之本、作为“家”而存在着。
溯回到诗经的传统,就会发现,旅行在外的抒情者们往往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这种使命多与开拓和镇守“土地”有关(如《郑风·叔于田》、《王风·君子于役》)。在《北国之春》中,这种古老的抒情传统其实遭逢了一种隐蔽的现代改造。我们可以认为:城里的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是因为北方的大地正亟待开拓;作为“流浪者”,他们需要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和改造获得自我认同。在歌曲之中,这些城市来客信心满满,让美好的风光环绕自身,为自己的行动添上一抹美学的光泽。这种对“风景的发现”正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的客观表征。柄谷行人认为,这个发现风景的人是一种内在的、处于自我对话状态的现代人,他关心的不是“美”而是别有意蕴的“崇高”[6](P15、31)。这也正如安格利卡·威尔曼在谈到席勒《散步》一诗时所说的那样:“散步者没有梦想回归到不复存在的人和自然合而为一的状态。他更多地是作为‘风景的主体’出现,并且把自然作为他观察的对象。……散步者能够享受自然之美景,恰恰是因为他疏远了自然。”[7](P86-87)
《北国之春》的深层逻辑也是如此:人通过对自然的抽象,通过对风景的“崇高化”,最终实现了对万物的占有。按吉登斯的话说,这种现象意味着“自然由于变得社会化而被拉入到对未来的拓殖中去,从而进入到了受现代制度支配的所有领域创造的不可预期的危险地带”[4](P194)。就像美国的西进运动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一样,昭和时代的日本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鲁莽的自信,新干线、北海道大开发和填海工程全都发生在那个飞速跃进的时代。在这个语境之下,《北国之春》中其实潜藏着古老的土地情结与现代化思潮相杂糅的扩张逻辑。这种土地情结来源于对土地与自然界的占有欲,如马克思所言:“正象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他的家族史,他的家世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家世,使地产人格化。”[8](P84)在北方谋生的青年们如春秋时期的先民般,通过起兴的方式占有自然风光,表达“向上的情绪”。在他们的逻辑里,这片被歌颂的土地就被合法地圈占,原始积累完成,一个具有主宰型人格的现代主体也就进而站了起来。在这首歌中,现代人的自我认同与对土地的占有紧密相伴,“传统”的抒情形式与“现代”的野心构成了同谋。
值得注意的是“城里不知季节变换”:相对于敏感的蛮荒自然,城市显然呈现出一种情感麻木的状态。这种麻木源于城市自身早已完成开拓的状态,源于阻隔自由大地之后感性资源的匮乏。当资本主义的“大地产”彻底完成之后,乡村的土地与事业资源被瓜分殆尽,通过占有而实现的自我认同也就变得万分艰难。在昭和年代晚期,随着泡沫经济阶段的到来,日本的流行音乐开始大量描写都市生活颓废、幻灭的一面。体制化的压力与“游荡”的处境让都市人难以认同自我,不得不求助于“歌曲的力量”(日本最著名的歌唱节目“红白歌会”的口号之一)。然而,在卡拉OK厅中,对“梦想”、“爱”、“人情”的歌颂渐渐减少,往昔的理想与自信早已不见踪影,吟唱《北国之春》不再能带来“向上的情绪”,“思乡”也就成为难以根治的认同缺失现代病。
在优雅的审美表象背后隐藏着大地产现代性的自我合法化过程,也隐藏着一种日本文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认同困境。一旦狭小岛国的土地被开发殆尽,一旦经济泡沫狂涌而出、掀翻一帆风顺的大船,社会生产机制必将发生极大的转变,古典的自然审美也就必然会让步给流行的文化,新一轮的自我认同必然来临,《北国之春》中那种昂扬情绪也就必将过时。按照最早关于“诸神之国日本”的设想,独立的“文化共同体”来源于对每一个民间元素的充分尊重和发展,来源于对人之自然本性的尊重。然而,当这些本土“神灵”不再能够配合全球化的飞速节奏时,它们究竟还会得到多大程度上的供奉?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万物分崩,中心不复”[9](P89)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还能从歌唱之中找回自信吗?
三、《鹿港小镇》:深度反思与“徘徊”的无力
日本人执着于构建想象中的举国共同体,不得不让传统的自然审美观与都市现代性媾和。同样处于东亚时代精神的笼罩之下,台湾歌手罗大佑显然有着另一种描绘“乡愁”的姿态。如果说《北国之春》是温柔敦厚的“正风”,那么《鹿港小镇》就是“礼义废、政教失”之后出现的“变风”。正风可以“兴”,可以“群”,构成《北国之春》的“敦伦”功能;“变风”可以“观”,可以“怨”,便构成《鹿港小镇》的“讽刺”功能。虽然同样在歌词中出现了“爹娘”、“姑娘”这样的字眼,但他们都不再是“寄来包裹”、“无语对饮”的行动者,而是被有意抽象了的“淳朴的笑容”与“长发迎空”。“亲人”不再有具体的行动,而是一张张被抽空的面孔。他们是歌手对传统乡镇人情的概念式的表达。“真正的田园风光似乎总是存在于上一代。”[10](P59)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的情感渐渐从现实世界中淡去。在歌手眼中,“台北”自然是一个成年后的都市之梦,但“鹿港”何尝不是一个童年的乡土之梦?“黄金天堂”和“淳朴善良”都是梦,梦醒之后,来临的则是撕心裂肺的幻灭。在这种幻灭感之中,《鹿港小镇》独特的“下沉的情绪”就具有了《北国之春》不具备的“反思”的高度。
在《鹿港小镇》中没有任何可供现代性隐匿的地方。通过对“过渡”或“徘徊”状态的深度描述,现代性的内在张力被暴露无遗。在《现象七十二变》、《首都》、《皇后大道东》这样的作品中,全息景观式的城市观察和社会批判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发生;然而在《鹿港小镇》里,罗大佑所关注的重心并非都市本身,而是沦落为“过渡”之所的小镇鹿港,其所采取的艺术手法也变成了蒙太奇式的时空转换。在歌曲的第一、二段中,歌唱者与“你先生”的“对话”是批判得以展开的关键;而在歌曲的第三段中叙事由实转虚,由对话过程中的回忆转变成了睡梦中的返乡场景。相比起《北国之春》工整的三段式展开和回环往复的曲式,《鹿港小镇》的这种线性的不对称形式恰恰唤起了人们对片断性、分裂性和流动性的直观感知,节奏上渐趋狂烈的摇滚旋律让歌唱者和倾听者随之达到情绪的高潮。从内在的文化逻辑上看,不难发现,歌曲中那些乡镇的、传统的“符码”体现着对空间稳定性的确认,譬如“妈祖庙”;而城市中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则暗示着一种变动不居的时间性特质,这种流动的城市现代性最终必会把静止的小镇卷入自身。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的壕堑战并阻碍时间的前进。时间则是战争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11](P14)在《北国之春》中,乡村是城市以空间逻辑实现的殖民地;而在《鹿港小镇》中,这种殖民则升级为时间逻辑上的同质化。小镇那“世世代代”的虔诚历史在都市的扩张过程中被遗忘,红砖房被水泥取代,淳朴的人民已经“看不见”。
进而,《鹿港小镇》的深邃之处并不在于呼喊“台北不是我的家”,而是对那些被现代时间所征服、进而失去“历史”的“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的发现。这样一种无所适从、心力交瘁的“徘徊者”形象充分暴露出现代社会“无根”的认同危机。这种无家可归“是现代社会芸芸民众和民族(‘不自愿的四海为家者’)永恒的命运”,因为“在日益以流落、移居、移民社群为特征的世界里,由于动荡和混杂带来的一切后果,不会有哪个地方符合绝对的纯正和真实。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哪个地方似故乡。”[12](P139、P141)进而可以看到,《鹿港小镇》中的“徘徊者”形象是对整个台湾的隐喻。受到殖民地历史、移民文化与少数族裔等因素的影响,在台湾的艺术传统里,对自我“历史”的追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鹿港小镇》中的抒情主人公毫无疑问失去了自己寄托在“斑驳木板”与“香火”之上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地方性审美经验”,失去了足以扎根的土壤,这与台湾处于文化与政治夹缝之中的遭遇几乎相同,也让人们联想起“变风”中“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无力形象。
这种被抽空历史认同感之后的“无力”感是现代性“颓废”的一大表征。“无力”的个体是与跋扈的城市化进程相对出现的。吉登斯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无力感相对于占有”(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的状态,他认为:“现代性的剥夺是无法抗拒的……剥夺的过程是现代制度成熟的一部分和一阶段,它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去,而且还进入到自我的核心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作为个体就一定会失去行动力。相反,这种“无力”的体验总是与积极的目标、抱负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向上”发展为“更大的关怀”。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坚持下去,克服磨难,把握生活的自主性[4](P225-228)。然而,这种积极的“生活政治”并不容易实现。在《鹿港小镇》中,慷慨激昂的歌声最终只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孤独的‘流浪者’在人群中行走着和观看着,但永远不能理解整个城市,城市生活也不是容易被理解的。”[10](P70)罗大佑的“徘徊”只是原地逡巡,并不能够找到出路,这是由其“颓废”的基调所决定的。事实上,“颓废”这种美学立场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物资充盈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13](P183),没有可供扎根的土地,没有可以继承的历史血脉,“徘徊者”也就彻底变成了“无产者”,他们在寄生状态下提出的反思与批判最终也将变成对自身的反讽,变成绝对的认同危机。我们不难发现流行音乐乃至一切流行文化在批判与反思方面与生俱来的软弱。在“市场”的魔力之下,“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许多年后,当名为“鹿港小镇”的台湾餐饮企业四处开花、标志着台湾本土文化经验的成功时,当初那种对土地和历史感的现实吁求,早已被产业化、同质化为全新的资本主义现代景观。“本土认同”也就最终拜倒在时间性的强力之下,成为了“全球认同”。
四、余论
以上的分析让我们渐渐摸清了这两首歌中隐藏着的文化逻辑。《北国之春》的“向上的情绪”是一种对空间现代性占有万物的骄傲,《鹿港小镇》的“下沉的情绪”是一种对时间现代性吞噬万物的焦虑。前者强调土地的吞并,后者强调历史的缺失,它们共同表现着进步的、扩张的现代性对传统伦理精神的侵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制度的逐渐完善,“生产”与“进步”会成为新的伦理,如同鲍曼所描述的那样:“道德是伦理的产物,伦理规范是生产方式,伦理哲学是工业技术,伦理说教是道德工业的实证主义;善是它所计划获得的收益,罪恶是它生产中的废品或副产品。”[14](P31)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假如一切美好事物背后都潜藏着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那么追问“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卡拉OK这样的日常审美活动究竟还能带来什么?
马歇尔·伯曼认为,面对现代性困境,“我们需要尽力追求不稳定的、动态的平衡”,保持一种“知性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9](P120)。事实上,纵使制度、法律和审美趣味等等都是相对的,人的基本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却是普遍的。因此,传统的“义理”与“人情”依然能够直指人心。如果伦理生活已被现代性所同质化,为何“前现代”的“义理”与“人情”至今依然为人们所信仰并追求呢?我们之所以唱歌,是因为的确能够从中获得一种认同,只不过这种认同已经不再是民族、地域和历史层面的认同,而是对所谓“伦常”的认同,即对“普遍人性”的体认。在一个土地与历史双双被抽空的时代背景之下,“乐”唯一能够唤起的就只有这种“伦常”的力量;同时,由于能够唤起这种力量,“乐”的独立意义也就依然存在。可以看到,“思乡”就是一种“普遍人性”,通过“思乡”我们可以获得认同。“认同是个记忆问题,尤其是对‘家’的记忆的问题。”[12](P124)吟唱熟悉的歌曲能够唤起对故土和历史的印象,唤起对“家”的情感。在这种追忆过程之中,我们起码可以“把根留住”。《北国之春》与《鹿港小镇》也因此得以传唱至今。尽管生活中充满了“异化”的机制,但是我们可以明察到自己内心这种“回归”的正当欲望。在对共通人性的积极乐观的歌颂中,在对“家乡”的追忆过程中,我们的心灵确实得到了真正的净化。
[1]Daniel A. Bell.China’s New Confucianism: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M].黎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3]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王铭铭,校.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M].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6]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7]安格利卡·威尔曼.散步:一种诗意的逗留[M].陈虹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M].Penguin Books,1988.
[10]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12]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14]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何百华,译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