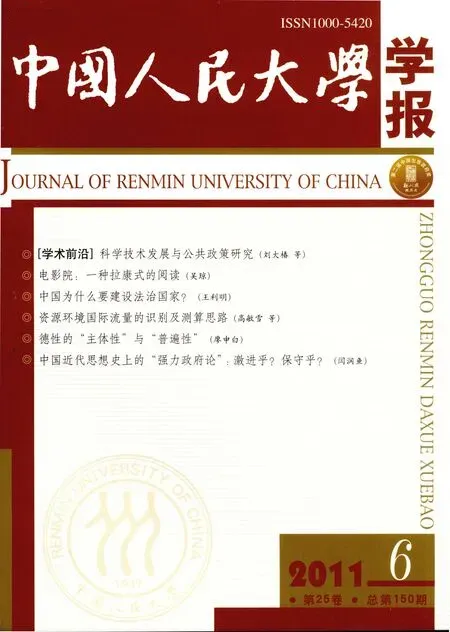历史意识与西方的自我认同:思想史的考察
张广生 张彦丽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高级文明似乎都曾有过一种自我轴心意识 (self-axial consciousness),由此,他们在民族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区别和认同关系 (relationship of discrim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但是,把这种中心主义发展为一种普世的历史观,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特别是伴随着17世纪的势力扩张,西方社会认为诸种现代世俗价值重新为世界历史提供了见证,而自己正居于这一历史进程的轴心。①沃格林认为,现代进步的文明论是谋弑上帝、僭越存在等级的 “灵知主义”思想的表征。参见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41~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这种特别的历史意识如何建构了西方的自我身份认同?它的思想来源和构成是什么?它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从思想史角度探讨这一议题又有什么意义?对于深受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影响的我们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现代西方的认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 (will to power)已经伴随着 “现代性”的思想和实践深入到我们思考和言说的内部。②德里克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第三世界历史叙事能力的支配和塑造效果。参见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pp.52~83.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安然处之,也不能绝对地弃之不顾,我们不得不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思考工具,一方面进行思考。
一、进步的历史: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
现代西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即所谓 “普世历史或普遍历史”。这一叙事方式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最明显的形式的方面,就是从 “古代”经由 “中世纪”而进入到“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另一个内容的意象就是为这种演进历程提供统一目的的自由或解放之类的 “进步”标准。无论现代性观念中这两个思想要素的来源是什么,它们在实质上都构成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那就是把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所主张的 “完善 (perfection)”的概念转化为 “可塑性 (perfectibility)”概念,正是可塑性的概念使得人的本性如何实现的问题主要变成了历史问题,特别是普遍历史的问题。[1](P104-109)
康德哲学 “三大批判”所构筑的理论体系把现代生活的精神结构描绘为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世界。知性、理性和判断力分别对应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人类生活领域,依次回答有关真理、正义和品味的基本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最终都要指向 “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卢梭的信奉者,康德要用自己的哲学来完善前辈那看似模糊的方案,而卢梭思想的暧昧性正来源于他对人的本性或者说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充满矛盾的看法。卢梭提出了救治 “文明”弊病的宏大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 “人与公民”双重教育任务的成败。①尼采认为卢梭有一种幼稚的、非历史的 “回归自然的愿望”,但卢梭的伦理与政治教育的任务恰恰是要改变人的本性。参见皮尔逊:《尼采反卢梭》,8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如果说,柏拉图的方案更倾向于选择聪颖的精英来受教育的话,那么,对卢梭来说,选择爱弥尔,恰恰因为他是普通的孩子,他所具有的仅仅是人人皆有的人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是人在原初的朴素自然状态下就具有的,否则,自然灾害、外在强力就不能够通过偶然性来把自然状态的人带入公民社会。但卢梭对人性的这种可塑性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所带来的 “文明”必然会败坏朴素的民风;另一方面,他又要以一种相当人为的 “自然教育”培养同时是欲望节制的而又急公好义的好人和好公民,这种教育同样需要这种人性的可塑性。可塑性或者说 “自由”成为人性构成的特点,那么,自由就等同于或者替代了 “善”。问题是,人性的自由又如何能够保证向善趋进呢?“自由人联合”的善良意愿如何才能具有普遍真实的性质而不限于善良的一厢情愿呢?
针对这一问题,康德通过一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提出保证:这种伦理学是建立在以主体性为中心的形式普遍性基础上的,这种形式普遍性的自明性理解提供了一种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的视野,在此视野下,真正的自由意志只能是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历史。因为,人性如果只是可塑性,那么,人的可塑性的普遍成果就要依赖于群体的长期积累。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成分使他怀疑 “进步”,但他所主张的人的自然权利也即 “自由”又不能不依赖偶然,他的继承者调和这种偶然与人的自由的方式之一就是相信历史进步。②康德由法哲学转向历史哲学的动力来自于其在形式主义伦理学和政治社会因果性世界间的调停企图。参见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8~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由于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的分离,自由意志的实现必须要克服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个人意志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于所有人。所以,对康德来说,把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联系起来,追问自由的后果时,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引入了暧昧的 “普遍历史观”,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要依赖于时间中的历史,而且不能是一个盲目无规律的历史,只能是一个合于 “天意”的进步的历史。人们所观照到的自然因果世界的时间不过是主体的先天感性能力的形式,所以,如果追问自由与自然和解为至善天福的时间,康德的回答就变成了奥古斯丁式的救赎许诺:时间性变成了对 “德福一致”实现的纯粹期待。
正是黑格尔更加自觉地把这种救赎许诺的期待时间变成了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 “精神自我和解的辩证时间”。时间不是一般 “被直观的变易”或 “过渡”,而是和精神运动相关联的 “否定之否定”。[2](P474-492)黑格尔是要为卢梭揭示出的、康德清晰表达出的现代文明的精神分裂找到一条自我疗救的道路。这种精神自我和解的道路被理解为 “合理性的”与 “现实性的”之间的辩证运动,因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在实现自身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对异化的克服都被理解为 “自由”作为理念或最终目的如何在世界中实现的问题。康德所追问的 “至善天福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得到了黑格尔的肯定,因为,“真正的善”即 “普遍神圣的理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理念,而是有能力实现它自己的原则,此 “善”或 “理性”在它的具体形式里就是上帝;所以,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实现。[3](P38-51)基督教的神圣救赎观被黑格尔转化为充满必然性的世俗历史观。世界历史被理解为 “自由意识中的进步”,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 “理想”只能通过在历史中主体间的 “相互承认”的斗争来推进,并“成长为一个世界”。①在歌德那里,作为理解世界上发生的精神事件钥匙的大自然,对黑格尔来说却仅仅是世界精神的 “自然舞台”。参见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64、289、2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黑格尔用 “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来勾画 “普遍精神”即 “世界精神”的发展。新时代是 “绝对精神”经自然界、人类历史到人本身的最后阶段,是绝对精神认识其自身的阶段。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理性还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一种知性,“我们的时代”才是理性发展的最后阶段。②对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展示的理性精神虽然是不完整的,但据说,只有理性的狡计实现后,才能有世界精神。参见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1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黑格尔在讲述 “普遍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旅程时,还分析了 “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世界历史从 ‘东方’到 ‘西方’,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 ‘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 ‘全体’是自由的。”[4](P110-111)这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表面上是分析 “世界历史”的空间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的非地理根据,却使得 “东方”和 “西方”这种地球上的相对方位概念被绝对化了,“西方”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更加强烈的确认。
黑格尔式的现代西方与理性的这种 “特殊选民”关系直到马克斯·韦伯那里仍被认为是自明的, “现代化”意涵正是导源于韦伯的 “理性化”。韦伯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思考一个 “总体历史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6世纪以来的欧洲日益走上了一条自己特有的 “理性化”道路,这一历程覆盖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宗教、经济、技术、科学、法律、行政甚至艺术,概莫能外;作为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欧洲以外的文明,政治、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都没能走向一条欧洲式的理性化的道路?[5](P15)不过,在韦伯这里,理性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价值合理性,二是工具合理性。[6](P89)正是在这种两重理性概念的观照下,韦伯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发展抱悲观态度。在韦伯看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工具合理性逐渐压倒了价值合理性,人类日益被驱赶进工具合理性的牢笼。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则完全舍弃了韦伯对 “理性化”进程的保留态度。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化理论对韦伯的现代性概念做了两个分离:首先,这一理论把 “现代性”同它的现代欧洲起源分离开,使之成为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在时空上的中立模式;其次,这一理论切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从而现代化过程不能再被视为理性化或理性化结构的历史客观化。③韦伯的说法当然有模糊之处,但他明确持有一种文化主义的立场,必要时,他就借此反思,撤销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有效性。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1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二、救赎的历史:西方认同感与基督教意识的离合
建立在现代历史感基础上的 “普遍历史”观与基督教意识有着深刻复杂的关联。④沃格林认为西方现代历史意识并非 《圣经》与基督教教义的嫡传子孙,而是灵知主义旁支的延续。参见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78~8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古代—中世纪—现代,这种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意识是从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二元世界观裂变而来的。
在 《但以理书》中,但以理通过为尼布甲尼撒解梦,提出了世界四纪说,透露了一种典型的二元世界观。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座巨大的塑像,像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而脚是半铁、半泥的。有一块巨石打在了那塑像的脚上,结果,金、银、铜、铁都一同被砸得粉碎,而砸碎这雕像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满了大地。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释了这个梦的喻义:金头象征尼布甲尼撒的帝国;随后依次又有银、铜、铁帝国,但关键是与地上的国相对照的那块巨石所代表的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第2章)。在为尼布甲尼撒的释梦中,但以理预言了世俗历史共有金、银、铜、铁四纪。而上帝的永不败坏的独立的国不归属于任何世俗的国,却要打碎灭绝世俗的列国,结束这四纪。
对 《但以理书》喻义的默会,在居鲁士以后的犹太教和波斯宗教中催生了一种世俗世界与上帝之国的二元世界感。这种世界感以上帝即将降临的救赎为世俗历史的循环轮替提供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和方向,其本质是一种宗教救赎的意识。这种在奥古斯丁那里还可以清晰看到的世界意识,对此前古典世界把历史看做没有目的的循环观念进行了深入改造,关键就是世俗世界之上,上帝之国的最终方向的出现。上帝之国使无目的、无意义的世俗历史有了期待救赎的意义。但上帝并不以世俗历史为媒介实现对信众的救赎,世俗历史中的荣辱兴衰对救赎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救赎只是上帝之国的突然不期而降。[7](P74)这样的上帝救赎的宗教许诺并没有把世俗历史的圆周改变成直线,而是要径直地砸碎它们。如果世界末日也即救赎尚未来临,世俗的历史还是古典世界观下的那个无目的的、此消彼长的循环。[8](P209-230)
从这种二元的世界意识到西方历史意识的古代—中世—现代的三分,的确需要一种把目的和意义植入世俗历史内部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使救赎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有机地融入同一历史时间之中,而不是分离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两个世界之中。
弗罗利斯的约阿西谟 (Joachim,1131—1202)完成了这个革命性的贡献。约阿西谟对《启示录》中所说的 “永远的福音”的解释最值得重视。关键在于:福音传布的权利不应被某个世俗的教会组织垄断,真正传播福音的组织在历史的最后时期应该是像圣本笃 (der heiligen Benediktus)修道院似的圣徒社团。这样的社团才是真正的教会,因为真正的教会应无条件地以清贫、谦恭、真理和心灵追随自己的主和导师,这样的教会是 “圣灵”的教会。圣灵教会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救赎的天国向度和世俗的此世的历史被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贯穿起来,这标志着一种“神学历史主义”的诞生。
这种神学历史主义通过创造性地解释 “三位一体学说”,而划分了意义、秩序与时间合一的三个不同时代。它们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阶段。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不同时期中启示自身,也相应的要求三个时期中的不同秩序,也昭示着不同时代的根本意义。[9](P75-78)神秘的数字“三”被用来做整体性的历史分期[10](P178),又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秩序:第一种秩序是圣父的秩序,在历史上是已婚者的秩序;第二种秩序是圣子的秩序,在历史中是教士的秩序;第三种秩序是圣灵的秩序,在历史中就是修士的秩序。[11](P75)三种时代秩序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维度就是称信者和上帝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直接:第一时代,犹太人是圣父律法下的奴隶;而基督徒与第一时代人相比,已经是灵性和自由的了;到了第三时期,灵性的自由将得到最完满的实现。[12](P178-179)
由二元世界的历史感到线性进步的西方的历史感,演变的关键在于救赎与世俗秩序,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有机合一。对于奥古斯丁式的世界感来说,围绕耶稣降生,被钉上十字架,复活,这一独一无二的事件,此前的历史和此后的历史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时间的含义根本不是从过去延伸向未来,而是集中于现在:救赎许诺的临在。从这种临在或者我们关注的现在出发所定义的未来实际上只是一种 “期待”,这种期待的性质就像 《罗马书》中对终极时刻来临的描述—— “像贼的到来一样”——末世的确切降临时刻是不可预期的,这种神学从根本上拒斥对未来终极事物作历史的解释。[13](P75)
但对约阿西谟的神学来说,世俗历史的未来和神学的预言的实现是经由圣父、圣子向圣灵时代的必然过渡。教会组织并不仅仅是个传播福音的团体,它在第三个时期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严格遵守福音训诫、努力拯救世界的圣徒组织。基督教的教会之所以不能获得一个永恒的合法基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 “时间的实现”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耶稣基督以后,历史仍然有其必然的进展。这种必然性体现在预言的完成并不是由超越历史时间的彼岸带来一个突然临在的末日,而是在从既是救赎的又是世俗的历史时间的内部有机发展来的一个最后历史时期内的实现。[14](P181)
斯宾格勒曾称约阿西谟为第一个具有黑格尔特点的思想家:“他抛弃了奥古斯丁的二元世界形式,运用他的本质上属于哥特人的智能,在新旧约宗教以外用了第三个词来叙述当时的新基督教,把它们分别称为圣父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和圣灵的时代。他的教义触动了方济各和多明我会中的优秀人物,但丁、阿奎那的灵魂深处,唤醒了人们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缓慢地,但确实地完全占据了我们文化中的历史感。”[15](P20)如果说,从奥古斯丁一直到18世纪,“世界历史”作为一种 “普遍历史”一直是在神学的笼罩之下的话,那么,伏尔泰和吉本似乎已经使世俗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神学中摆脱出来。这种历史哲学把视野从天国转向了人间,把历史的意义从神义转向了人义。但这种转向之中,思想的形式仍然继承了基督教传统中的 “普遍历史”和 “线性 ‘进步’”的基本模式。[16](P78-83)17世纪之后,我们看到各种通史的叙事,无论观念史还是社会史的叙事,难逃神秘的 “古代—中世—现代”的三分,只不过进步的阶梯所接近的目的不断由上帝的救赎替换为西方世俗社会的时代信念而已。[17](P185-188)
三、德性的历史:古希腊罗马的教诲
古希腊罗马,虽然被古代—中世—近世的流行叙事描绘为西方的 “古代”,但与西方的世俗“现代”和基督教 “中世纪”相比却更像是另一个独立的高级文明社会。现代西方虽然不断援引古希腊罗马为自我认同提供思想资源,但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拥有与基督教和现代西方迥异的历史感和世界意识。
历史的眼睛在希腊人那里当然是投射到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流变领域,但他们的变化观念并不是一种线性演进类型的,他们的变是一种强烈的 “突变”:“从事物的一种状态突变性地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的那种意识,从小到大,从骄傲到谦卑,从幸福到苦难的那种意识。”[18](P54)这种对流变的关注当然不会获得对人事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但对流变有正确的意见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附属于在实践中做出明智举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的历史被指责只关心政治大事就一点也不冤枉了。希腊人的历史学本身就是深思慎行的智慧指南,而非后世所谓的历史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理解古希腊人的历史学,恐怕也必须理解他们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切联系的 “人事 (human affairs)”之学。
柏拉图 《理想国》中,由王制或贵族制向荣誉制、由荣誉制向寡头制、由寡头制向民主制、由民主制向僭主制的变化是由人的德性 (virtue)或者说统治者德性的变化导致的。依照 《理想国》最末一章的生命循环神话,灵魂不灭仿佛是为了那些在有生之年德性和作为恶劣的人与善德善行的人各有 “因果报应”,但重新 “造人”或者说 “轮回”的寓言关键是要说明对统治者的灵魂进行教育的必要,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政体衰败,教育跌落到了极点,统治者的德性败坏到了极点,就伴随着文明衰落的极点。人伦生活中最重要的流变也即政治文明的盛衰取决于人的灵魂类型的变化,而灵魂类型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为灵魂类型的 “轮回转生”,不如说是因为教育——人性的内在卓越或平庸因为与教育的耦合而能出现在每一个 “此世”或每一个 “来世”。所以,循环转生的历史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必然的拯救,每个 “来世”正像每个 “此世”,只是给予你一次生命,有自由意志的你是选择王者的灵魂或政体,还是僭主的灵魂或政体,是创造卓越的文明还是腐朽的世界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而是取决于你活着时能发挥出的德性,德性是人选择生活,创造世界的力量。[19]
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 《政治学》关注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人事”。亚里士多德列举了王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共和制 (或混合制)、僭主制等政体形式。他把寡头制和民主制看做是最常见的政体,而且讲述政体的轮替也是从这种常见政体在经验上向其他政体变化落笔的。在他看来,政治本质上是人的德性践履的领域,在沉思的、实践的和生产的生活这三种基本类型中,实践也即政治的生活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而践履德性的活动。而幸福并不是所有外部有利的条件与运气的总和,幸福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也即内在的善。内在的善落实于人的灵魂的品质,幸福就是人的灵魂品质能够得到无阻碍的实现。而政治的活动本身表现了人的灵魂品质经由审慎的德性而实现。由于来世是人们难以预见的,幸福的含义是让人在此世用一生的努力使自己灵魂的品质得到实现。幸福涉及此世的正义,而正义就是要把人类灵魂的品质依照人类灵魂应有的构成等级变成一种此世的现实秩序。[20]
古希腊罗马人把历史看做是循环的,但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所透露的信息,这种循环的时间意识并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未来,因为 “来世”的内在可能就在此世内部,而不是外部彼岸,或者如果有 “来世”,“来世”也不过是对可能的 “此世”的再现,对历史充满憧憬的人不过是希望自己的世代能够在历史的永恒循环中扮演伟大复兴者的角色。柯林伍德敏锐地注意到了希腊历史意识对 “此世”的 “执著”,但他不能理解这种 “当世执著”背后隐藏的区别好的事物与祖传事物的判断力来自何方。并非如柯林伍德所说,希腊人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才能写作历史,而是可能相反,流变是在不变的映衬之下,德性确定了历史人物的角色类型,虽然这角色由不同的具体的人扮演,但人物的是非成败取决于他的可修行的 “德性”及不能选择的 “命运”,而不是衍生出来的 “个性”。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空间感是与城邦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波斯人对希腊的征服也给希腊人带来了帝国的体制,此后又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又有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地理中心的帝国统御版图给他们一个现实的世界帝国的感觉;但是物质地理的秩序构成原则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人们内心秩序和意义构成的原则。古希腊罗马人的家园感是与他们那种 “纯粹在场”的生活参与感密不可分的。以德性为媒介的秩序和意义是可见的,“在场的”,因而也是范围有限的,古典帝国秩序也许更像一串葡萄,一个个高度自治的实体被一个征服者主导的中心城邦用武力和有限的治理能力联结起来。①希腊罗马文明即便进入帝国统治时期,城邦与有德行的公民的政治秩序观也是其 “世界史”意识的核心。参见古郎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388~3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总之,古希腊罗马人的 “世界历史”,是自我限制的世界历史。其自我限制性来自一个重要的哲学认知,那就是秩序与意义的来源在于人在世俗一生中的努力,来源于他们的理智和伦理德性的卓越及这种卓越的人伦政治效果。根据古希腊罗马人的这种此世中心的历史循环论,只要一个民族在某段时间里足够卓越,这个民族就可能开创一段辉煌却有限的世界历史。然而,每一代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命运女神只给人们转生的机会,却不先天赋予人们足够的智慧和德性,所以,虽然有些民族能创造辉煌的文明,但任何文明都难逃衰落的命运;继起民族或许能开启新一轮文明的循环,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者。由一神之恩典承诺的 “普世救赎”和“普世历史”,在古希腊罗马的心智看来,不是太热望,就是太绝望,这样 “绝望”而后又充满“热望”的历史太缺乏自我节制了。
四、结语
流行的世界史叙事是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时间三分法。伴随着西方的扩张,其他轴心文明的独特历史也日渐被整合进以现代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的长期浸润之下,对于许多轴心文明心智来说曾经相当陌生的异文明的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其讲述自身和世界进程的共同预设。但事实上,这种宏大叙事本身就是利用现代西方特有的历史意识建构其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当西方把自己描述成现代世界的轴心时,这种叙事的内在逻辑是:在被假设为线性进步的人类文明历程中,现代西方穷尽了世界的最深刻经验,因而成为人类世俗价值和历史的终结者;那些被卷入这一世界进程的其他民族或文明,必须以这些价值为最后的价值,以西方的历史为唯一可能的历史。但是,这些价值是否就是最后的价值呢?思想史的分析告诉我们,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用线性进步的观念来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追溯到被视作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伯来传统,无论对犹太教还是早期的基督教而言,神恩突然降临的时间终结意识和二元论的世界观都使他们对世俗历史保持一种冷静的距离,救赎历史的世俗舞台也因此局限于古叙利亚、古波斯和古代希腊化世界的有限区域。如果回溯到那被视为西方文明另一源头的古希腊罗马传统,我们更会发现一种理性的循环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派生的、健康的多元文明的世界观。从这种历史感和世界观来看,支撑现代西方自我认同的普世历史观是一种模仿一神论的狂热的世俗弥撒亚主义,它太缺少节制、理性和中道了。总之,进步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和德性的历史叙事透露出相当不同的历史感和世界观念,甚至,在这些不同的世界历史意识背后,我们可以辨识出性格迥异的独立文明。只有批判地揭示出现代性话语背后隐藏的独特的历史观念,深入地探讨现代西方历史意识的来源、构成和内在矛盾,我们才能在反思自身认知构成的基础上正确理解西方文明,重新获得某种认识和建构自我身份的能力。
[1]张广生:《文化、文明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考察》,载 《东南学术》,2006(4)。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4]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9][11][13][16]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10][12][14][17]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5]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ume one,Trans.by Charles F.Atkinson,London:George Atten Unwin LTD,1928.
[1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9]柏拉图:《理想国》,第8、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政治学》,第5、7、8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