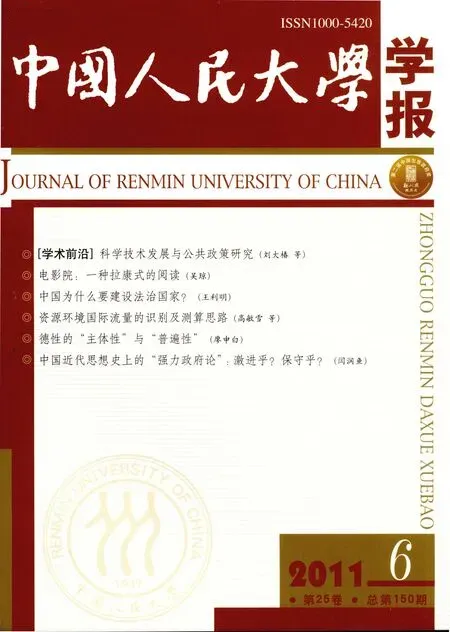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强力政府论”:激进乎?保守乎?——基于梁启超、孙中山相关思想的考察
闫润鱼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进与保守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被广为引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关于何谓激进与保守、如何评价激进与保守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相关著述中都有探讨。鉴于此,本文不打算就激进与保守的概念和评价展开讨论,而是希望通过对近代思想史上的“强力政府论”的剖析来展现激进与保守的复杂面相。
之所以把梁启超与孙中山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他们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想家还是作为政治实践家,都是相关研究不能不重点关注的人物。不仅如此,他们也是身份特征最为鲜明的人物:一为改良派,一为革命派,他们分别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又进行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位历史人物在构建什么样的政府问题上,所持观点却惊人的一致,都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力政府”。有学者在梳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时,曾列出诸如“1906年梁启超提出的开明专制论”、“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筹安会发起者杨度提出的君主立宪救国论”、“1925年国家主义者发起的醒狮运动”、“1928年至1929年由蒋介石使之具体化的训政论及从此开始的训政实践”、“1933年至1934年喧闹一时的法西斯主义的鼓噪”、“1935年丁文江蒋廷黻提出的‘新式独裁论’”等运动。[1](P57-67)看得出,这些所谓政治保守主义的思想或思潮,大都带有“强力政府论”的思想色彩。以此而论,梁启超、孙中山的政府论也可归之为政治保守主义的范畴。问题是,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都存在明显差异的梁启超和孙中山,是出于何种考虑或论证逻辑而一致导向“强力政府论”的呢?揭示其中的所以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梁启超、孙中山的相关研究,特别是被学界相对忽略的有关政府思想的研究,也对理解激进与保守的复杂性有所裨益。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机关、社会生活的管理机构,政府的存在几乎与文明史一样久远。但在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近代西方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政府”却并不存在。直到近代,受西方政治和政治学说的影响,“政府”才成为中国人谈论和设计的对象。一般认为,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府指包揽了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事务的所有机关,统称国家机关。狭义上的政府,则仅指国家行政机关。鸦片战争后,诸如美国“大酋”(总统)、英国公会所(议院)等设置开始进入关注“海国”、“瀛寰”概况的学者们的视野。到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已有不少思想家认定,在西方,不论是君主制国、民主制国,还是君民共主制国,“开议院”都是其强盛的主要保障。不过,由于这个时期政治改良的重心是适度扩大君主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人们津津乐道的议会,其现实功能多被定位在“通上下之情、合君民一体”之上,它们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范畴。在近代思想史上,只有变革政体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政府形式——不论是广义上的国家机关还是狭义上的行政机构,才真正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有趣的是,探究该问题的思想家们尽管对君主专制的制度结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要求由君主立宪制、进而是民主共和制来取而代之,但却并不因此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或有意识地弱化行政权力,相反,程度不同的“强力政府论”在思想界一直都有声音发出。换言之,在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偏于保守主义的声音却一直萦绕在耳。在这股持续不绝的声浪中,梁启超、孙中山的相关论说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二
不论是“弱政府论”还是“强政府论”,都包含着对政府是什么的基本判断。在梁启超的笔下,与政府有关的学说作为西学的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其向国人“无限制尽量输入”的对象。受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的影响,他将政府成立的缘由解释为“民约”,认为国家虽为人民所有,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但人民却并非个个有能力和时间顾及国家事务,于是就有“于吾群中选若干人而一以托之焉”一幕的发生,这便是政府的成立。不过,政府虽然是人民的受托机关,但它一经成立,就拥有了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治权。“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2](P1)梁启超的这种看上去不偏不倚的观点,“实际上是赋予了政府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3](P12)按照政治学的一般原理,缘于“民约”的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要向人民负责或受人民掣肘,亦即“政府为人民所有”。一旦将人民与政府间的关系界定为互不统属、彼此独立的关系,政府就获得了在逻辑上本不属于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政府缘起的本身就已规定了政府的责任,对此,梁启超有清晰的表述:“夫政府之为物,既不过受民之委托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机关,则其所当循守之责任可知矣。”[4](P108)具体而言,就是“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5](P2)虽然政府的根本责任是助民生计、保民自由,但政府通常又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意味着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6](P43)因此,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究其实质也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阐释基本上是以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为依据的,认为国家的“第一目的,则其本身(即国家全体)之利益是也。其第二目的,则其构成分子(即国民个人)之利益是也”。[7](P44)无可否认,他在阐释西方一些享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的学说时,也关注到了他们思想的复杂性。比如,他注意到在“常无偏党者”的伯氏学说中,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是有限制的:“苟非遇大变故,则国家不能滥用此权。苟滥用之,则各私人亦有对于国家而自保护其自由之权理云。”[8](P89)他也观察到“近世政学之士”,出于“舆情自安”、祸乱“不萌”的考虑,对于霍布斯的学说,多取其“民约之义功利之说”,而摒弃其“专制政体之论”,一味强调政府的功能“惟在保护国民之自由权,拥卫其所立之民约,而此外无所干预”。[9](P93)在划分政府与人民的权限时,他也指出:“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10](P3)但所有这些论说在“遇大变故”的现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都不及以国家利益作为第一目的来得重要。
如果说以上所涉是广义政府的概念的话,那么,相对于立法(议会)而存在的政府(内阁)就是狭义的政府概念。关于议院,梁启超认为它的“最重之职务,在于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即参与立法之权”,这也是议院的“根本精神”所在。[11](P110)正因为议院是一个民意机关,所以责任政府“对于国民所选举之国会而负责任”[12](P25)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梁启超虽然强调“今日欲兴新治,非划清立法之权而注重之不能为功也”,但如同他在平衡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利关系时最终偏向了政府一边一样,在承认立法与行政“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13](P105)的同时,“隐约中却含有倚重行政之意”。[14](P10)原因是,他既对立法与行政的分立可以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的可能性不抱乐观看法,认为相互牵制的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治虚伪等不良后果;同时也对立法监督弹劾行政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认为既然总统是因受人民的信任而被选任的,阁员任职是得到国会承认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职有权,若处处受掣肘,就是不合理的:“夫既已保证之于前,而旋或纠问弹劾之于后,同一机关,翻云覆雨,揆诸理论,宁得云当?”[15](P62)在梁启超的论述中,政府虽然同议会、君主一样,都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国家而负责任,非甲机关对乙机关而负责任”[16](P12),但由于政府拥有“每一职必专任一人,授以全权,使尽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属之”的职权[17](P104-105),所以,政府权力的独立或不对立法机关负责,实际上就是自身权力的提升或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加大。
可见,不论是广义上的政府还是狭义上的政府,它相对于人民和立法机关而言都享有独立并优先的地位。梁启超对政府所做的这种安排,目的是使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所谓强,亦指善而强者”,“善”与“强”是融为一体的。在他看来,国家建设都“必以能得良政府为前提”,既然有这个前提在,那么,人民对于“以治事”为职责的政府,就“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他认为,政府只有获得“广大巩固之权”,才能“得尽其才以为国宣力”。“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18](P63,62)
不可否认,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在政府问题上的主张前后也有一些不同,大体说来,前期多受民约论的影响,后期特别是出访北美以后,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尽管如此,“这归根到底并不完全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19](P163)因为在梁启超那里,判断一个政府的好与坏,自始至终都是以其是否适应时代的需求为标准的。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政府的权限问题,依据政治学的原理讨论与依据现实讨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以政治学之原理论之,政府之事业当渐次轻减,使人民各以个人自营之,故政府最终之目的,则放任主义也。”[20](P100)以现实论之,“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21](P87)他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卢梭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已无人问津,权力集中已成趋势,“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22](P89)而国内的情况是,民智不发达,法治机关不整备等一直制约着中国的发展。鉴于民治方面“无论在政治上,在生计上,其种种设施,类多不能自举,而必有待于国家之督率”[23](P47)的现状,他主张“惟有雄武有力者起,挟莫大之权力以鞭挞之,然后屏息敛手,栗栗受命于其指挥之下,而其群始渐能团合”。[24](P12)为了国家的存立,他呼吁顺应保育主义再度兴起的国际潮流,“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25](P46)在梁启超这里,不论政府如何行使权力,只要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即出于“善”,其合法性就不该受到质疑:“不能以侵夺人民自由与否,以鉴定政治之良不良。所当察者,其目的何在耳!”[26](P22)
三
讨论孙中山的政府论,离不开他的“五权宪法”和“权能分别”说。“五权宪法”中的行政权即政府;“权能分别”中的“能”指“治权”,包括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这些权力属政府所有。如果说前者是狭义上的政府的话,那后者就是广义上的政府。不论是何种意义上的政府,孙中山都主张强固或扩大其职权,使其成为一个“万能政府”。
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一直非常注意西方各国的政治,在广东举事之前就有意识地“详细考究”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们建设的张本”。在这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流亡各国的日子里“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出这个五权宪法,补救从前的不完备”。[27](P572,573)对于当时的宪法体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孙中山“以最高尚的眼光同最崇拜的心理去研究美国宪法”所得的结论则与之大相径庭,他发现美国宪法不完备的地方还很多,流弊也不少。究其原因:一是从发展的眼光看,“无论什么东西,在一二百年之前以为是很好的,过了多少时间,以至于现在,便觉得不好了”。[28](P573)二是从政治制度的设计上看,没有安排独立的考试机关和监察机关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些流弊的发生。
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在三权的基础上再添加两权,一个基本考虑就是要为政府松绑,使其成为一个能发挥效能的“万能”政府。特别是监察权的设置,针对的就是议院擅用纠察权、挟制行政机关的“议院专制”现象。他在对西方宪政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就是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29](P331)此外,“从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也是“不恰当的”。[30](P320)因此,监察权的独立在他看来是必要且合理的。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虽然接受了三权宪法的影响并沿用了“分权”的称谓,但他对“万能”政府的期望则内在地规定了他所谓的“五权宪法”,主要关注的并非是像西方三权分立政体中的那种权力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而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人民之间应该具备的良性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既反对“占据国家机关者,其始藉人民之选举,以获此资格;其继则悍然违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莫如之何”[31](P33)的政府,也不希望人民过度“挟制”政府,使其成为一个无能的政府。孙中山观察到:“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32](P730)对于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一旦政府被弄到无能的地步,有政府也就和无政府没有什么两样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非常重视民权,考虑到间接民权即“代议”不能真正实现民权,他甚至主张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但他所谓的民权,并不是经由与政府的对抗而确定的,如果民权进一步,政府能力就相应的退化一步,使政府成为无能的政府,民权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保障。因此,他表示不能认同“人民反抗政府的态度”,不能接受政府“无论如何善良”而人民“皆不满意”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33](P730,73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想出了“一个根本办法”,也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那就是“权与能要分别”。[34](P731)
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上阿斗和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被我们作为一个成功的先例援引来处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既然诸葛亮是受阿斗之托“管理政事”的,那么,一方面,阿斗就应该信任诸葛亮,把治理国家的大事放手地交由他做,因为受托的人是“有本领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35](P739);另一方面,作为阿斗的人民“把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不要看做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做是赶车的车夫”,或者“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等即可。[36](P742)总之,在孙中山的设计中,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西方现代民权政治下的那种对抗关系,而是为“主”者放心用人、为“臣”者尽心事主的彼此信赖关系。我们看到,在孙中山那里,很少有提醒人们对政府保持警惕的论说,而是强调人民对于政府官吏应该放心使用,“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就“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如果“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37](P740)
人民之所以可以放心地让政府自由行动,是因为人民掌握着对政府的罢免权。“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现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38](P738)行使罢免权的是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都由它统辖。按照这种设计,国民大会下的五权,实际上成了五个工作“门径”,这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合作和配合远比“制衡”来得重要,所谓“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就是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状态。孙中山曾把五权宪法的关系比喻为:“好像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职。”[39](P572,573)只有五权之间互相帮助形成群力,政府才可以“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40](P756),“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41](P763)
在西方的分权政体中,“没有一个部门在实施各自的权力时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部门具有压倒性的影响”。[42](P252)而在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结构中,五权之间是一种“联属”、“统一”而非“制衡”的关系,它们要负责的对象都是国民大会。不过,五权之上尽管有一个国民大会,但国民大会只是在必要时才动用它的罢免等权,一般情况下,对“专门家”或“有能的人”的治权行使,并不刻意设防。如此一来,享有五权的政府机构内部,虽然没有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每一个部门都必须承担“帮助”其他部门的职责,政府“群力”由此得以形成。五权之外,虽然国民大会对其有“压倒”性影响,但国民大会并不以掣肘五权的具体行使为目的,因此,政府便会“无限”地发出“威力”。这就是孙中山理想中的“万能政府”。
四
就梁启超、孙中山“有意识”①在余英时那篇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他所谓的激进与保守,主要是讲“在思想上某些有意识发展出来的看法”,“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orientation”。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1~2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提出“强力政府论”的态度或取向而言,可以说既具保守的一面,也有激进的一面。就保守论,是因为他们并不要求根本推翻并重建整个政治秩序。梁启超的《干涉与放任》、《开明专制》等是在晚清发表的,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此时的他无意根本改变现状,彻底颠覆君主专制统治。在与革命派的论争中,他虽然清晰地表达了反对革命、拒绝共和的理由,但当民主共和真的来临时,则以积极的心态接受之。其《中国立国大方针》等探讨政制的文字,就是为民国政制提供的改革方案。孙中山虽然很早就注意各国宪法,但有关“万能政府”的清晰表达,则多在民国建立之后。作为民主共和的缔造者,他虽然对篡夺其权力者或后继者的施政大表不满,但“万能政府”的理想依然是在认可现实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为未来政治的发展所设计的方案。就激进言,是因为不论是在晚清还是在民国,政府无能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孙中山的“强力政府论”所表达的正是要急于结束或彻底改变这种现状的激进取向。此外,从前文的梳理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梁启超的“强有力之政府”论,还是孙中山的“万能政府”论,他们理想中的有效政府都是靠权力资源的相对集中和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少受牵绊来保障的。梁启超认可“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的时代发展趋势[43](P89),孙中山则特别在意对政府“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44](P740)这种带有“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改造工程”的思想特征,实际上是很难与激进主义区别开来的。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在政治层面上的中国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迷信政治国家的万能,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以整体主义来处理社会不同层面的问题。”[45](P41)
如果从比较的视野来分析,梁启超、孙中山所阐发的“强力政府论”,在所谓激进与保守上,又有程度或论证逻辑上的某些差异。虽然他们的“强力政府论”都是从对于现实的观察出发的,但观察的角度或关注的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梁启超赋予实行强力政府的合理性依据主要是国民的开化程度,他特别担心将民权交与缺乏法纪意识的国民后会导致天下大乱,并因此使民权落空。从他的相关论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基本关怀和态度取向。国民素质的低下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步步深入,国民素质也会随之提升。一旦“大变故”结束,环境条件具备,真正的民权政治就有望推行开来。这其中既包含着对人民能力的不信任,也赋予了“新民”以必要性,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民权的关切和对未来实行民权政治的信念。作为以传输西学为己任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不仅熟悉也比较认同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承认“政府之事业当渐次轻减”[46](P100)应该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不难看出,所谓“强有力之政府”,如同“开明专制”一样,只是梁启超针对“过渡”时代所做的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非其理想中的或与民主政治价值高度吻合的制度选择。“强有力之政府”论的这种“过渡”特征,使其具有较为浓厚的保守色彩。
而孙中山的“万能政府”论,主要是从如何有效地避免西方实行民权政治以来出现的弊端着手阐发的,特别是立法对行政的过分牵制以及人民与政府的对抗关系。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虽然向往西方的民主共和制,但却处处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比如,在揭露和批评三权分立政体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弊端时,他曾以不成文宪法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认为“我们中国也有三权宪法”,一是君权,一是考试权,一是弹劾权,其中君权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47](P580)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谓的五权宪法,与其说是对欧美三权宪法的修正,倒不如说是对中国宪法的重新修订,即将君权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再加上考试权和弹劾权,构成五权。就孙中山为其宪政思想刻意打上传统文化的印记而论,其“万能政府”论无疑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不过,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在他的相关论证中又流露出革命性或激进化的思想色彩来。比如,他曾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等,第一等为发明家,第二等为鼓吹家,第三等则为实行家。[48](P164)“人分三等”说不仅为其确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也使其“万能政府”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安排。与梁启超相比,“人分三等”说并不仅仅适用于当下中国的人群划分,而且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社会。在孙中山的论证逻辑中,一个社会不论进化到何种程度,人依然可作三等之分,普通大众永远改变不了其所处的实行家位置。既然人群的基本类型不变,那么,基于人民为主、政府为仆的理念,或由“先知先觉”、“后知后觉”者组成的“万能政府”来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安排,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无可否认,孙中山的“万能政府”理想离不开时代需求的制约,但就其设计的理路而言,则无疑具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激进主义倾向。若就国民素质本身论,孙中山与梁启超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看法也有明显不同,他甚至讲过“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即使不够高,也无需搞那么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因为“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49](P280,281)显然,他将对大众的思想启蒙宣布为缓不济急,将少数“志士”的思想高下视为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少数志士仁人努力,“万能政府”即可打造而成。
[1]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5][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陆央云:《梁启超政府思想研究》,未刊稿。
[4][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6]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8][22][4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5][18][23][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0][21][4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27][28][32][33][34][35][36][37][38][40][41][44][47]《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9][30][49]《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31]《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9]《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4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5]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8]《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