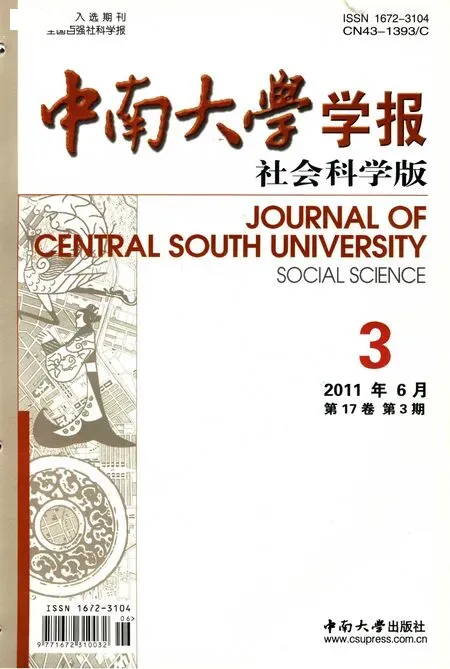可撤销的营业转让合同研究——以日本判例和学说为中心
郭娅丽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北京,100025)
营业转让合同的可撤销,是指已经成立,但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合同溯及地产生无效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法定有效要件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不真实性,即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或意思表示有瑕疵。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就营业转让合同而言,主要指三种情形:①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②显失公平的合同;③内部决议存在瑕疵的营业转让合同。对于前两者,营业转让合同与其他合同并无差异,而对第三种合同则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尤以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而签订的营业转让合同最为典型。这方面日本有许多学说和判例,本文以此为中心展开分析。
一、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营业转让合同的效力分析
(一) 股东大会决议与营业转让合同的关系——“必要说”与“不要说”
早期公司法均贯穿了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或称为股东主权原则,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财产是由股东投入的资本形成的,他们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因此公司的重大事务均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法的制度设计紧紧围绕保护股东利益展开。营业转让是决定公司命运的重大交易行为,关系到公司的存立基础,对股东利益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各国公司法均规定营业转让是股东大会专属决议事项,通过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形成公司的意思,保护多数股东的利益;对于异议股东一般均赋予其股份回购请求权加以保护。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股东的高度分散,公司治理结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对于股东而言,只要得到了满意的分配,就愿意把公司的各项事务交给董事处理”,①且由于董事的决策效率相对较高而受到青睐。在关于营业转让的决策权归属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必要说”和“不要说”。“必要说”认为营业全部转让的情形,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经过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而重要部分转让的情形,转让方应经过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受让方无须经过此程序。也有学者认为,在营业重要部分转让的情形下,“只要从受让公司的现状来看能够认定其重要性,应要求有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更为妥当”,[1](396)作为例外情形,“转让的财产是作为公司存续基础的重要的营业性财产时,……这种财产的转让会导致营业的停止和中断,与营业的转让并无不同,因此,要适用第374条1款1号,要求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1](399)并有判例支持该观点。[1](399)“不要说”则认为营业转让属于董事会经营管理决策范围,无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其中“必要说”为多数说,对特殊情形中的营业转让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则应根据不同情形决定,以下做一详细分析。
1. 歇业中公司的营业转让
汉语中的“歇”有四个含义:休息;停止;睡;很短的一段时间。[2]一般理解均含有短时间停止的意思。歇业,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定义,多数学者将其解释为停止营业,但笔者认为不太恰当。因为“歇业”一般只意味着暂时停止营业,并非寿终正寝。在日本称为“休业”,与“废业”相对称,区别二者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存在“活着”的能够活动的营业财产,“休业”长期化,根据客观情势恢复营业极其困难,就达到了“废业”状态。[3](51)休业的公司可能是“休眠公司”的一种——“资格有,实体无。”[4]当公司处于歇业状态时进行的营业转让是否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我们通过对日本最高法院审理的两个案件“富士林产工业事件”[5]和“寿兴业事件”[6]仔细研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判断营业转让是否需要股东大会决议的标准为是否存在可保护的股东利益;其二,歇业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存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必要性。在“富士林产工业事件”中,公司歇业3年,可以认定长时间地歇业达到事实上的废业状态,股东的被保护利益丧失。因为根据公司法规定,定期股东大会须每年一次在一定的时期召集,那么,该公司至少应召开三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用脚投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假如公司在歇业期间未召开股东大会,仅以此也可推知公司的状况,股东已经丧失从公司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期待,公司职员等姑且不论,一般股东也已经云消雾散。”[7]因此,歇业时间较长时,营业转让无须股东大会决议。而“寿兴业事件”正好相反,歇业时间只有5个月,受让人承担债务,继受了营业活动,营业转让对股东利益影响重大,存在可保护的股东利益,应经过股东大会决议。
2. 债务超过②公司的营业转让
债务超过一般认为公司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可能濒临破产,公司的股价下跌,无论将股份出卖还是由公司回购,其价值均近似于零。所以,学者主张该种情形中,营业转让无须股东大会决议,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优先于股东利益保护。[8]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债务超过概念的着眼点是资债比例关系,考察债务人偿还能力仅以实有财产为限,不考虑信用、能力等偿还因素。而现实中,即使债务超过资产,但债务人有良好信用、未来收益足以具有清偿能力,仅是暂时的债务超过情形时,债务人并不导致破产,此时进行的营业转让若不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极可能导致侵害股东利益,所以债务超过公司的营业转让是否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不能一概而论。
3. 清算中公司的营业转让
公司解散后清算中的营业转让是否应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有“不要说”和“必要说”两种见解。“不要说”认为公司解散股东已无可保护的利益,故没有必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必要说”则主张:公司的解散决议是营业废止的意思表示,即使作出解散决议,并非马上就化为单纯的个别财产,也可能进行营业转让。只要存在有机性财产,对其处分的最终判断就应委以股东。[3](12)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分两种不同情况加以判断:公司清算有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之分,各自有不同的发生原因,在西方国家,特别清算主要适用于财务上面临破产危机的公司,该种情形下股东已经无可保护利益,故无须股东大会决议。对于普通清算,“严格意义上讲,公司解散和公司清算均是指公司结束其生命和消灭其独立人格的一种法律程序。公司解散是此程序的开始,而公司清算则是这种程序的继续和结束。”[9]该种情形下,股东的经营目的已经达到,通过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反映了股东的意愿,对于公司剩余财产的处理仍应尊重股东的意思,营业转让时应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4. 母子公司之间的营业转让
母子公司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既有共同利益存在:母子公司作为同一的公司集团成员,有共同的经营目标,子公司受到母公司的控制;但又有各自的个体利益:母公司、子公司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其独立的利益。当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特别是绝对控股的母子公司之间)进行营业转让时,从转让的对价来说,一方的损失正好是对方的利益,反之亦然。因此,《日本公司法典》第468条规定:特别控股公司(指法务省令规定的其他公司及持有其他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及其他准于此的法人持有某股份公司全体股东 9/10的情形)的事业转让属于简易受让,无须依股东大会决议对该行为的相关合同承认。这是它们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母子公司之间的营业转让有两种情形:一为母公司向子公司营业转让的情形。营业转让如果免去股东大会决议,则完全由母公司董事会决定,母公司的股东完全丧失表示意见的机会。[10]如果母公司采取先决议转投资设立子公司,然后子公司将其受让的营业转让给第三人,则规避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3](45−46)台湾企业并购法称之为“脱壳法的营业让与”,是严重的脱法行为,需要依据“股东穿越法理”③保护母公司股东的利益。二为子公司向母公司营业转让的情形。如果子公司向母公司营业转让无须经过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则子公司可能成为母公司分散投资风险、转嫁责任的工具。这是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子公司、子公司少数股东均处于从属地位,母公司在根据自身利益或集团利益决策时,很可能将某个公司作为其经营战略的棋子,以牺牲子公司利益来换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做出对子公司及其少数股东利益有损害的决定。”[11]母公司、子公司各自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均独立承担有限责任,子公司事业亏损不能累及母公司,子公司营业转让可能成为解散或破产原因,母公司对此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母公司受让子公司全部营业无须经过母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则无视母公司作为子公司股东的重大利益。[12]因此,母子公司之间的营业转让,从维护股东实际利益出发,仍然以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为妥当。
(二) 欠缺股东大会决议的营业转让合同一概认定无效的弊端分析
日本学界和实务上早期通说认为,除特殊情形外,股东大会决议是营业转让的必经程序,对欠缺决议的营业转让合同认定为绝对无效的合同。但是一概认定营业转让绝对无效,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失误,在实践中亦逐渐暴露出弊端。
第一,理论上违背民法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基本法理,混淆了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认定标准。根据民法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基本法理,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最显著区别是涉及违反社会利益还是仅涉及不当侵害私人利益,[13]前者为无效民事行为,后者为可撤销行为。就营业转让合同而言,公司营业转让意思的形成是通过股东大会决议表决机制实现的,如果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则公司意思本身欠缺。有学者认为“须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对外性决议,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而达成时,对其交易本身的效力带来影响(例如营业转让)。……因此,关于须经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因缺少股东大会决议或决议有缺陷而无效、取消时,等于股份公司意思欠缺,从而绝对无效”。[1](349)笔者认为,该观点过于绝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三分法”④)对营业转让合同的效力存在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有三种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情形又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日本公司法认为: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包括无召集权召集的股东大会所作的决议、根本未召开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伪造决议;无效的决议的情形包括决议内容违反强行性法律、法令的决议;可撤销决议的情形包括股东大会召集程序或表决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或显著不公正;决议内容违反章程以及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行使表决权形成不当决议。不同情形的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对营业转让合同的效力影响并不相同,决议瑕疵包括程序上的瑕疵和内容上的瑕疵,决议不成立属于程序上的瑕疵,可撤销决议中的召集程序、决议方法违反法令亦属于程序上的瑕疵;而决议无效的股东大会决议、决议内容违反章程属于内容瑕疵,“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行使表决权形成不当决议”形式上是程序瑕疵,其实质是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而导致的内容瑕疵。原则上,对于程序瑕疵,从鼓励交易和交易安全原则出发,可以从程序上补正,由股东大会决议进行“追认”,允许股东大会重新作出决议,治愈之前决议的瑕疵,促成营业转让合同的有效,而不赋予当事人撤销合同的权利;如果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对营业转让事项形成否定决议,则欠缺公司意思,应赋予当事人撤销合同的权利。对于内容瑕疵,违背强行性法律不能得到治愈,违反章程的决议是 “基于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可由股东大会决议变更,并无赋予与法令相同效力的必要”,⑤如果股东大会决议变更该决议,则该瑕疵得到治愈,公司意思具备,营业转让合同有效;反之,该股东大会决议被撤销,则欠缺公司意思,赋予当事人撤销合同的权利。总之,当关于营业转让的股东大会决议为不成立的决议、可撤销决议不能得到治愈时(以下所指的欠缺股东大会决议的合同即限定在这一范围),欠缺当事人意思的营业转让合同,因仅仅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双方利益,并不涉及违反社会利益,原则上不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应认定为可撤销 合同。
第二,实务上漠视交易安全原则,侵害善意第三人利益,损害公司利害相关者利益。将欠缺公司意思的营业转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则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当然不生效力,当事人可主张无效,法院、仲裁机关也可以主动确认其无效,这样受让人即使受让了营业却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对交易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一旦被确定为绝对无效,将导致该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的后果,但只是不受法律保护,毕竟已经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受让方对营业持续地利用,已经发生一系列的营业行为,形成债权、债务、劳动关系等一系列的法律关系(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比起一般买卖合同的“流动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使已经发生的法律关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将导致公司对外的所有法律关系崩溃,导致整个社会交易秩序的混乱。事实上,只欠缺公司意思并未违反社会利益的营业转让合同本质上属于契约自治的范畴,法律应赋予与其瑕疵性质相符的法律效果,允许受害人依其意思去选择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确定其为可撤销行为更为妥当。因为可撤销行为是特定的意思欠缺方在较短的期间内享有撤销权,能够使转让合同尽快处于确定状态,对交易的第三人更为有利,更有利于实现营业转让的目的。此外,营业转让还涉及到了包括债权人、劳动者等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他们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均注入了专用性投资,同时分担了公司的一定的经营风险,营业转让属于公司的重大决策,对他们同样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团体法上的行为即使存在瑕疵,在法律上仍应尊重过去已发生的事实关系,如果不予尊重,将使公司对外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长期累积而陷于混乱、难以解决的地步。”[1](41)如前所述,将欠缺公司意思的营业转让合同,首先采取补救措施治愈,对于其余不能治愈的情形,认定为可撤销合同,从实务上来看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同时兼顾公司利害相关者利益,更好地维护交易安全。
二、营业转让合同撤销权的行使
(一) 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营业转让中就撤销权的行使主体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受让人是否享有撤销权。民法上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受损害方或有瑕疵意思表示一方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只应赋予受损害方或有瑕疵意思表示一方以撤销权。依此,在营业转让合同中,在全部营业转让的情形下,《日本公司法》⑥、《韩国商法典》⑦规定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一方欠缺股东大会决议则欠缺公司意思,欠缺公司意思一方享有撤销权,包括转让方和受让方;如果双方欠缺股东大会决议,则双方均欠缺意思,首先应补正程序,促成交易;如果不能补正,双方均享有撤销权。在重要部分营业转让的情形下,《日本公司法》《韩国商法典》规定转让方应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受让方无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依此,转让方欠缺股东大会决议则欠缺公司意思,转让方享有撤销权,受让方不能享有撤销权,否则可能对转让方更为不利。
(二) 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民法上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以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行使,因撤销的原因不同而分别规定以意思表示的方式或诉讼的方式行使。[14]而在公司法上,因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撤销股东大会决议对股东的利益影响较大,各国均明确规定应以诉讼进行,由法院来审查是否符合法定的撤销情形,在平衡股东利益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慎重作出裁决。就欠缺股东大会决议的营业转让合同来说,与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相比,不仅存在对股东大会决议的内部效力的认定问题,而且要对瑕疵决议对外的效力作出判断,涉及的法律关系更加复杂,从公正性和效率性出发,不宜由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应以诉讼为之,由法院作出划一、确定的裁决,避免同样的行为不同的法律效果所带来的团体法上法律关系的混乱。
(三) 撤销权的行使期间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受到一定期间的限制,民法中首先规定行使权利的一个有效期间,同时还规定一个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限制。如《日本民法典》第 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可追认时起,5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行为时起,经过20年时,亦同。”[15]营业转让合同作为一种特殊合同,如果特别法未作出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自然应受到该期间的限制。但是,由于营业转让合同的效力受到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影响,因此,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起诉期间与营业转让合同的撤销期间的关系如何,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最高法院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X公司是有三个工厂的股份公司,将其中一个工厂的所有营业均转让给Y公司设立前的发起人代表A。X公司由于不知法律规定,所以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就进行营业转让,并办理了转让手续。Y公司是A作为代表董事设立的股份公司,其承继了营业,但在原始章程中未按照公司法第168条“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规定记载该项财产承受,同样是因为A不知法律的规定。Y公司承继营业后亦未向X公司提出过请求,在支付了一部分转让价款后,X公司和Y公司之间确认余额、达成了延期支付的合意。但是,Y公司其后营业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停止了营业活动。于是,X公司向Y公司提出了要求支付剩余价款的诉讼。一审中,Y公司以X公司转让重要部分营业违反公司法第168条1项6号规定、未作为相对必要事项记载为由主张无效,法院未予采纳,支持了X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Y公司又以X公司转让重要部分营业,违反商法第245条1项1号未经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营业转让契约为理由主张无效。但是,在此之前,X公司、Y公司的股东、债权人等公司利害关系人均未对营业转让契约主张无效。[3](132−133)
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接受公司的原始章程没有记载因而无效的情况下,转让人根据营业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债务,接受公司也以营业转让有效为前提对转让人承认自己的债务,履行一部分受让金接受制品、销售或消费原材料,并且由于受让公司在营业转让合同经过9年后,第一次主张其无效。其间,接受公司的股东和债务人等对营业转让合同有无效力没有作为问题等判决所表示的事情时,接受公司主张营业转让合同无效一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能允许。”⑧同理,受让公司在合同经过20年后,以欠缺股东大会决议为理由第一次主张营业转让合同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笔者认为,本案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受让方是否有撤销权。最高法院主要是从股东、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从起诉期间的角度来考察,9年、20年因期限较长容易判断,假如只经过了半年或1年,受让方是否可以主张无效恐怕难以判断,所以有学者提出“不如通过一般条款直接否定其主张。”[3](55)这与笔者之前的分析一致,在重要部分转让的情形下,欠缺股东大会决议的转让方是欠缺意思的一方,可行使撤销权,作为相对人的受让方并不享有撤销权,否则对转让方更为不利。二是营业转让合同的撤销期间是否适用民法可撤销行为的最长期间限制。众所周知,商事交易贵在迅捷,甚至有学者将效益原则作为商法的首要原则[16],所以商法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符合交易的迅捷要求,在交易后果的确定上实行短期时效主义。就营业转让的股东大会决议而言,各国公司法中对决议不存在、决议无效之诉无时间限制,对可撤销决议只规定了起诉期间,如《日本公司法》第831条规定为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3个月内以诉讼请求撤销该决议,《韩国商法典》第376条规定自决议之日起2个月内提起诉讼,但均无最长期间的规定。以此为基础签订的营业转让合同,如果存在可撤销的原因,那么其行使权利的期间也应相应地实行短期时效,特别是采用营业转让的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较短。⑨如果时效期间过长,将使企业的经营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同时可能存在的情形是,较长的期限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及至行使权利时撤销权的相对人早已不存在,从而使该制度成为一项摆设。因此,笔者认为,对营业转让合同的撤销权应规定短于民事时效的短期时效,以不超过1年为宜,对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诉讼时效应规定最长时效期间(如 2年),避免团体性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以使交易关系尽快确定,维护交易安全。
三、营业转让合同撤销权的限制和排除
(一) 营业转让合同撤销权的限制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欠缺内部决议程序,使得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而该瑕疵仅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该种合同可确认为可撤销合同,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即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是否所有的撤销权人不问其主观心理状态均可以行使撤销权呢? 笔者认为,对此应作出必要的限制:即原则上存在意思瑕疵的一方享有撤销权,但是对于恶意的转让人例外。具体来说,对于明知营业转让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程序,而故意不履行该项程序,待看到受让方日后经营状况好,转让方以未经过该程序为由主张无效;或者受让方明知受让该营业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程序,而故意不履行该项程序,待受让方日后经营状况恶化时,受让方以未经过该程序为由主张无效,这两种情形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享有撤销权。如日本判例亦表明了此观点:有转让方在转让时故意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看到日后经营状态好转,为了取回营业,以没有决议为理由主张营业转让无效,法院判决认为:这样的无效主张不值得保护。[3](53)
(二) 营业转让合同撤销权的排除
对于欠缺股东大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被确认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以此为基础缔结的营业转让合同,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应承认该合同有效。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包括两种: 一是因信赖对方股东大会决议记录而签订合同的第三人,当股东大会决议被确认为撤销、无效或不存在,营业转让合同亦随之被确认为无效,对信赖方明显不公平。因为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是内部文件,董事会提供该文件使得交易的相对人产生了信赖,第三人已经遵守了法律对他的较高要求,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对于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法律应该予以保护;二是不知道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的营业转让的第三人,这里的第三人因组织形式的不同,其注意义务也不同。对于股份公司因其有严密的治理结构,所以具有预见和防止公司重大决策失误的能力,而其他组织或个人则不然,所以对于他们的注意义务的判断应适用较低的标准。根据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按照行为人需尽义务程度,过失分为三种类型:重大过失,系法律对某种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程度有较高要求时,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对其较高的要求,甚至连一般人都应注意并能注意的义务也未尽到所致,也称为“专家注意义务”;抽象轻过失,系行为人未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所致,也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具体轻过失,系当事人未尽为自己事务之同一注意义务所致,也称“自己事务的注意义务”。这里的善意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它们虽然不具备严密的治理结构,但毕竟是从事营利活动的商主体,具备一定的预见经营风险的能力,对其只要求与一般自然人同样的注意义务,易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当然,法院还应就个案具体衡量双方的经营状况、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作出判断。此外,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转让方欠缺股东大会决议,当受让人将该营业又转让的,转让人能否向转得人主张撤销权? 日本学者山下真弘认为,“为了交易安全,有必要推导出转让公司对转得人不得主张撤销权。”[3](54)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营业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有些国家明确将其作为不动产综合体对待,营业的移转有其特殊的规则,当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就取得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原转让人不能对其行使撤销权。总之,当交易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存在行使撤销权的原因,但从交易安全原则出发,仍然应排除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
注释:
① Saleem Sheikh, William Rees, Corporate Governance & Corporate Control,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5: 225.转引自钱玉林:《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学术交流》2002年第1期,第47页。
② 债务超过:指在财产计算中,消极财产超过积极财产的情形。法律指财产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形。参见[日]《法律用语辞典》,自由国民社2002年2月20日,第495、648页。
③ 股东穿越法理:指公司集团中,当控制公司处于绝对支配或基本绝对支配地位,控制公司股东得透过控制公司和受控公司的界限,直接就受控公司重大事务行使股东权的制度。参见赵志钢:《公司集团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5 页。
④ 就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学理和立法上存在“二分法”和“三分法”之争,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决议成立为前提,对决议瑕疵程度分析基础上进行的划分;后者则将决议的成立和生效区分,增加了“决议不成立”为一类型。本文赞成“三分法”。
⑤ 北泽正启:《修正股份公司法解说》,税务经理协会1982年版,第61页. 转引自钱玉林《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载《法学》2006 年第11期,第36页。
⑥ 参见《日本公司法典》第467条。
⑦ 参见《韩国商法典》第374条。
⑧ 日本最高法院判决56(才)1094 61.9.11第一小法庭·判决148−445,转引自马太广编译:《判例所表现的商法法理》, 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51页。
⑨ 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5.9年,在北京中关村只有2.9年。”参见CCTV.com 经济信息联播,2007年12月14日 22:39,2009年7月21日访问。
[1]李哲松. 韩国公司法[M]. 吴日焕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2000.
[2]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273.
[3]山下真弘. 營業讓渡と讓受の理論と實際[M]. 东京: 信山社出版株式会社, 2001.
[4]吕冰心. 揭秘“休眠公司”[J]. 法人杂志, 2007, (2): 21−22.
[5]昭和四〇年九月二二日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判决[J]. 民集,19(6):1600.
[6]昭和四一年二月二三日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判决[J]. 民集,20(2): 302.
[7]宇田一明. 營業讓渡法の研究[M]. 东京: 中央经济社, 1993:216.
[8]龍田節. 營業讓渡と株主總會決議[J]. 法學論叢, 105(3): 12.
[9]冯果. 公司法要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38.
[10]落合诚一. 新版注释会社法(5)[M]. 东京: 有斐阁, 1986: 272.
[11]张华硕. 论母子公司关系的法律规制[D]. 长沙: 湖南大学法学院, 2008: 13.
[12]藤井光二. 一OO%子公司の营业全部の让受と株主总会决议の要否[J]. 商事法务, 1980, (861): 46.
[13]龙卫球. 民法总论(第二版)[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517, 521.
[14]张里安, 胡振玲. 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J]. 法学评论, 2007,(3): 115.
[15]渠涛编译. 最新日本民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12):31.
[16]赵万一. 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