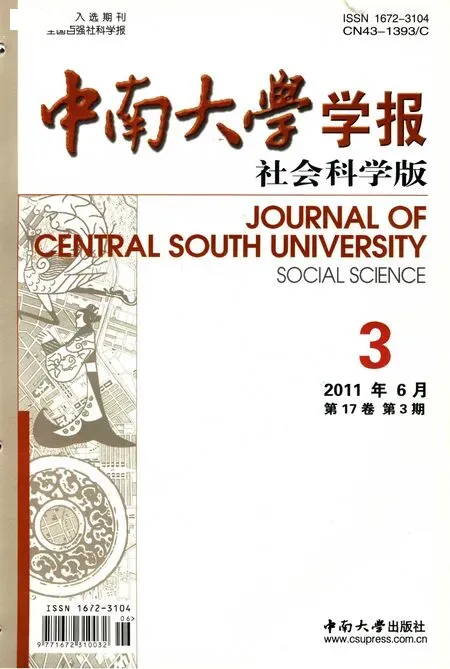国际不法行为责任上的主观因素
赵洲
(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律系,安徽 巢湖,238000)
根据 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2条的规定,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该行为依照国际法可归于国家;二是该行为构成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背。对此,国际法委员会第三任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教授指出,条款草案所规定的责任构成要素只是为了适用于一切情形而在立法上进行的巧妙抽象,它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一切特定案件中排除目的、过错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
一、国际不法行为的目的与动机
国家行为是国家行使其主权的表现和结果。一般而言,国家总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或动机而实施相应的主权行为,然而,在国际间关系上,“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在它正当目的以外行使而能成为正当。”[2]“善意也限定国际法上的权利,因为以违反善意的方法行使权利,就成立权利滥用。”[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明确要求,条约应当善意地予以解释和适用。“国际常设法院曾经表示下述的见解: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虽然在技术上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但实际上却由于滥用它的权利而可能担负责任。”[4]总之,任何国家行为在目的、动机上应当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以不危及、损害他国的正当权益及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为限度。否则,特定的国家行为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即便该行为具有形式合法性,也将构成实质上的国际不法行为,主权国家将承担由此而造成的国家责任。“正当性”(legitimacy)的重要功能就是补救实定法漏洞,修正实定法的错误。[5]在国际社会里,由于国际法规范和国际义务在理解和适用上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模糊、矛盾和疏漏之处,所以,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有助于准确合理地确定国家行为的不法性及其程度等。例如,在国际税收协调合作领域,缔约国应当善意履行税收条约义务,恶意履行税收条约可能招致不法行为责任。上世纪 70年代,为了增加美国政府的外国税收抵免额,巴西在对向国外支付的利息实行25%预提税率的同时,向借款人提供相当于预提税额85%的财政补贴。即使这种税收竞争行为未直接违背双边税收协定中的任何国际义务,它也可能导致不法行为责任。再有,国家有意规避条约义务,如缔约国一方恶意地将股票资本利得归类为不动产资本利得,以避免条约中缔约国双方分享股票资本利得的税收管辖权的约定。这种恶意规避行为也将导致不法行为责任。[6]在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如果一国的目的、动机在于限制某一特定种族群体的移民,那么,限制移民就违反了国际人权法等义务。驱逐外国人的权利也受到主观动机的限制,即驱逐的动机应当正当,否则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同样,“这样的规则表明,如果目的是政治报复或报仇,那么对外国人财产的征用就是非法的。又如,表面上是集体抵抗侵略者的行动将不再具有合法性,如果参与该活动的相关国家被证明是意在利用此以达到吞并目的。同样地,在必须或自卫的基础上,表面不合法的行为可以寻求获得正当化。行为者的动机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消除辩解的全部基础。”[7]对此,布朗利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8]2004年12月,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报告指出,同其他任何法律制度一样,国际集体安全体制的效力最终不仅取决于决定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人们是否都认为这些决定是正当的,是根据确凿的证据作出的,并有正当的道义和法律理由。安全理事会在考虑是否批准或同意使用武力时,不管它可能会考虑的其他因素为何,至少应考虑五个正当性的基本标准,其中包括正当的目的要求。即是否明确无误地表明,不管有无其他目的或动机,拟议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制止或避免有关威胁?①总之,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保证了国家行为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高度统一,国际社会秩序因而可以得到更加周延的维护。从宏观上看,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体现了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维护和进步发展的根本要求。
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有助于分析确认表面合法但实质违法的行为,除此之外,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还将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发挥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和作用。随着国际社会的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国家在各种国际活动领域的行动权利日益扩展,同时,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数量上也日益增多,这些义务在性质和关系上日益相互影响,国家的行动权利和国际义务之间更是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这也就是所谓国际社会在权利义务及其国际法规范上的“碎片化”或不成体系性的特征和现实。为了能有效地保障国际秩序及其健康发展,“每个国家都应持续、善意地作出努力,以缓解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提高国际法的有序化程度。”[9]进而言之,面对着不尽相同甚至矛盾冲突的各种国际权利和义务,主权国家应当本着以“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为根本目的、宗旨来行使其权利和承担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并以此来确定相关行为的正当合法与否。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7 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 2001年11月,WTO部长会议通过的《TRIPS协定与公共卫生宣言》确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会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卫生。宣言重申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承诺,确认可以和应该以支持世贸组织成员有权保护公共卫生,尤其是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方式解释和执行协定。②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第五十七条界定了条例和其他国际协议的关系。其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认识到,《国际卫生条例》和其他相关的国际协议应该解释为一致。《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不应该影响任何缔约国根据其他国际协议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第三款规定,在不损害本条例规定义务的情况下,作为某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各缔约国应该在其相互关系中实行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施行的共同规则。如果行为国未能或缺乏以“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的目的、动机来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即便其行为有相应的行动权利依据或符合某一方面的国际义务,其行为也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自从“9·11”以后,美国以“反恐”为目的和理由建立了秘密监狱,用以秘密关押任何被怀疑是恐怖嫌犯的人,使这些人处于被强迫失踪的状态,丧失了法律保护。2006年8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反恐为由不遵守联合国《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的规定和义务。从行为的违法性来看,这些国家的行为显然已经违反了既有的国际人权法上的法定义务。而对于那些已经签署批准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国家而言,实施秘密关押的行为则又进一步违反了特定的条约义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8年第7届会议认为,各国必须确保其反恐措施符合国际人权法等规定的义务。③总之,“反恐”目的不是弱化或背离国际人权义务的一个正当理由,以“反恐”为目的的任何行为只有在不损害人权保护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免遭强迫失踪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不论对一个人实施秘密拘禁的目的、理由多么正当,任何秘密拘禁都不符合一系列人权和人道法条约的规定。[10]任何以“反恐”为目的和理由的强迫失踪行为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责任。
一般来说,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是以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认同的“正当性”观念为内涵。这些“正当性”观念反映了国际社会秩序现状及其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但一般并不具有明确具体的行为标准。对于条约上的权利义务而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据此,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可以通过条约上的目的、宗旨的规范要素得到具体验证和判定。基于特定目的、动机的主权国家的行为如果能够符合相关条约的目的、宗旨的规范要求,那么在该条约范围内该行为可以被认定符合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例如,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由于相关的国际法规范高度原则化等原因,主权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内涵往往不够精确或细化,依据相关条约的目的、宗旨来具体验证和判定那些基于特定目的、动机的国家行为性质无疑有着极大的必要和价值。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缔约国承担了诸多国际义务,其中包括在国际层面共享公共卫生信息。在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国际间早在 50年前就建立起一个流感病毒样本共同分享的机制,即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WHO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Network)。各个国家流感中心在本国收集病毒样本,将分离出的毒株送往世卫组织,2006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敦促各国以及时和一致的方式向世卫组织各合作中心提供与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其他新流感毒株有关的信息和相关生物材料。④2007年初,印尼政府宣布不再向世卫组织发送感染禽流感病毒的人类基因样本,理由是印尼需要高价购买受专利保护的疫苗。2007年5月,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就国际社会共同分享禽流感病毒样本,以及保证病毒样本提供国享用疫苗研究成果等问题通过决议。决议重申了在应对人类流感过程中分享病毒的必要性和从国际合作中获得切实利益的基本原则。193个成员国承诺共享禽流感病毒样品。⑤不过,世卫各成员未能就病毒样品分享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包括商业性的医药公司取得样品的条件等。在2010年第6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各国仍无法就“材料转移标准协定”(Standard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SMTA)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希望建立不与病毒共享挂钩的自愿性权益分享机制。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应分享发达国家利用其生物资源产生的专利权益。⑥尽管如此,基于《国际卫生条例》的目的、宗旨,以及在各种权益相竞争时条例目的、宗旨的特殊性、优先性和不可损抑性,《国际卫生条例》下的义务仍应得到缔约国的遵守和履行,以有效地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07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上指出,不分享禽流感病毒的国家将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印尼主张对病毒样本的研发利用应遵循《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但是,禽流感病毒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所保护的那种生物资源。印尼不向世卫组织提交病毒样本既不利人类健康,也无益于生物多样性。造成全球威胁的禽流感病毒只有为卫生监测和医药研发目标所普遍共享,而不是由某些国家控制,才能造福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11]反过来说,印尼按照《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义务提交病毒样本并不会导致更坏的境况,或给其造成额外的权益损失。实际上,印尼的主张应当放在国际知识产权机制予以解决,如通过强制许可等制度完善来获得正当权益; 或者以国际人权法机制为突破,使有关病毒疫苗等的专利权人做出利益让渡;或者也可以在《国际卫生条例》的条款范围之内,明确、强化和落实关于从技术和财政上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⑦而不能通过减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方式来实现本国的利益。总之,一般而言,印尼主张从国际合作中获益以及保护本国人民免遭疾病侵害的目的、动机有其正当合理性,但是放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下予以考量,印尼的目的、动机并不足以构成背离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目的和宗旨及其所派生义务的正当性辩解和理由。以这样的目的、动机为由不向世卫组织提交病毒样本不符合《国际卫生条例》的目的和宗旨及其所要求的各项义务,难以满足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要求。
在某些情形下,为确定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等,目的、动机上的“正当性”观念被赋予了明确具体的行为标准,从而为特定的国际不法行为的确定设定了目的、动机上的构成条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4条第1款中规定,成员国在行使汇率主权时应遵守相应的义务,其中一项约束义务是,避免为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得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了《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Decision on Bilateral Surveillance over Members’Policies)。根据该决定,“判断IMF成员国汇率政策是否构成‘操纵汇率’,不在于成员国是否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而主要取决于成员国外汇政策或措施的动机和目的。例如,尽管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各国政府仍会干预和管理外汇市场,各国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仍将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起重要作用(影响汇率变动),只要相关行为的目的不在于为获得不公平的出口竞争优势,就不构成IMF所规定的‘操纵汇率’。再如,各国金融机构关于票据市场、存贷款利息、税收以及政府开支等方面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均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但如果这些政策行为并非旨在影响汇率变动,也不应被视为‘操纵汇率’的行为。”[12]总之,对于是否构成“操纵汇率”这样的国际不法行为,设定目的和动机方面的构成条件显然是必要的,它恰当地区分了正当的汇率调整行为与国际不法行为,维护了正当的汇率主权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及其健康发展。
随着国际社会人权保护观念和实践的发展,保护国内人民已逐渐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一种特殊的责任。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形成了保护责任的初步共识和规范。然而,对于国际社会应如何实施保护责任,却存在着试图淡化目标国主权或予以替代托管的主张。例如主张通过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来进行和平建设活动,履行保护责任,并且试图仅仅以“国际管理”的名称替换来解决托管所引起的殖民色彩和争议。[13]为保障正确合法地履行和实施保护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在2009年向63届联大提出的《履行保护责任》的专题报告中提出了基本的“目的指导”原则。即保护责任的目的是确立负责任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因此,即便是一国因能力不足或缺乏领土控制而无法充分履行保护责任,在国际社会提供补充保护时,该国仍然是履行保护责任的基本主体。[14]进而言之,在主权国家单独或集体实施补充保护行动时,其目的和动机必须始终是为了提升目标国的主权权能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权威等,只有在此基础上实施的保护行动才是正当合法的。[15]与行使汇率主权上的目的、动机要求有所不同的是,履行保护责任上的目的、动机应当与客观的行动效果保持高度一致,或者说,目的、动机上的要求应当通过实际的行动效果予以检验和确认。如果外来的补充保护实际背离了基本的“目的指导”原则,其行为就将构成侵害他国主权干涉其内政的国际不法行为。
综上,目的、动机表征和探求着深层次的主观因素,解释了国家行为的内在的深层次的主观缘由,其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在于,它可以规范、约束表面合法但实质不正当的国家行为。从而在深层次的主观层面上限定和规范国家行为,更加全面有效地维护着国际社会的良治秩序。
二、国际不法行为的过错
(一) 过错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在确立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时,过错并不是必备的构成要件。“在国家违反国际义务的所有情况下,并非贯彻无过失即无责任的原则。”[16]换言之,国际不法行为责任不必绝对地依赖于故意或过失这样的过错因素的存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一是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往往会对相关国家造成各种实际损害。在此情形下,违反国际义务的国家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对其行为后果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予以恢复原状或赔偿。二是各种国际义务是国家之间谈判协商的产物,它们维系着各国之间的权益关系的复杂而微妙的协调平衡。而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往往会破坏这种协调平衡,损害相关国家据此享有的权益。在此情形下,违反国际义务的国家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有必要通过承担相应的责任来恢复各国权益关系的协调平衡,如停止不法行为、恢复原状等。WTO法上的国家责任就是以“利益丧失或减损”(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为基本的确立依据,而并不考虑缔约国相关行为的过错因素,甚至并不绝对地要求行为的违法性,只要相应行为已经或可能有损于缔约国之间依据WTO协定所形成的权益协调平衡关系,以及WTO总体目标、宗旨的实现,行为国将因此承担 WTO法上的国家责任。[17]三是在国际层面进行过错的证明确认是很困难的。如果过错成为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确立所必备的构成要件,这将对援引责任的一方造成不合理的举证负担。
尽管过错不是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必备构成要件,但是,完全抛开过错因素将难以准确合理地认定具体情形下的特定国际责任的成立与否,或者难以准确地认定国际责任的种类、大小以及承担方式等。首先,“对于私人的行为,国家责任是以过失为基础的,因为通常必须表明,国家在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惩治违法者方面未表现出相当的注意”。[18]“为了不让国家对个人行为所负的责任过于扩大,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法学说只赞成在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国家机关有过失(有意或失职)时,才存在着国际法上的责任。”[19]目前,恐怖主义侵害行为及其应对又成为新的情形。各国负有防止和惩治境内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义务。“当一国防患于未然,惩治于事后仍不能阻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时,该国是否应该承担国际法律责任?若该国惩治力度被他国指责为不力时,该国是否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20]对此,仅仅依据相关的安理会决议和国际公约所提出的行为标准和义务要求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过错因素分析才能确定国际法律责任的构成与否。其次,就国家直接实施的积极作为而言,根据相应的初级规范或具体的行为情形,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也需要过错的存在。再次,更为常见的是,过错因素将影响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程度、大小等。“在评估损害赔偿时,对于有意或恶意犯下的国际违法行为的赔偿行为和对于仅仅由于过失而产生的违法行为的赔偿行为总是有很大区别的”。[18]因此,只有在个案中通过恰当合理地分析适用过错因素,才可以公平合理地界定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与否、程度大小等,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和促进国际秩序的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有观点认为,“既然《国家责任条款》按照‘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划分,旨在有助于认定国际不法行为成立的一般条件,那么,将行为的主观条件作为形式要件加以明确,是完全必要的。”[21]但是,过错因素的意义、作用不可能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的模式。在某些情形下,过错因素对责任的成立具有构成作用,而在某些条件下,过错因素更多的是对承担责任的方式、程度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问题的过分简单化,以及过分依赖客观责任、疏忽和意图等一般性主张,可能导致缺乏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技巧。”[8]
(二) 过错的认定
在确定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种类、程度等方面,过错因素的确认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过错的存在与否是一个无法直接感知的抽象的主观领域,尤其是对国家这样的拟制人格而言更是这样。从责任构成的一般法理和实践来看,对于过错的认定和把握存在着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在主观状态上来认识、界定过错,即过措就是指行为主体所具有的一种应受责难的心理状态,从而与外在的行为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过错与行为的违法性是两个不同的责任要件。但这样的主观上的应受责难状态的存在与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探求和认定,实践中一般还是要回到客观行为上加以推定。另一种则是从客观方面来认识、界定过错。即从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出发来判断行为主体的过错状态,行为主体的行为若不符合某种客观行为标准即构成过错。所谓客观认定标准具体有以下几种:一是违反法定义务的标准,凡违反了事先存在的法定义务或某种法定的注意义务即构成过错;二是对权利的侵害,任何侵害法定权利并造成损害即构成过错;三是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如行为不符合一个谨慎的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即构成过错。这些从客观角度分析认定过错状态的方式不同于纯粹的主观过错,而构成了一种客观过错,也就是通过外在的客观行为表现来推定主观上的过错状态的有无、大小等。其中,以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为基础的客观过错较为合理,并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实际运用。例如,法国的客观过错理论认为,“我们在行为时,应当总是使用更大的谨慎和更大的勤勉,这是我们的行为规则。此种规则不仅被法律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强加给我们,而且还被道德强加给我们。没有遵守一个谨慎的和勤勉的人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即构成行为偏差,即为过错。”[22]总之,客观过错是指违反了谨慎的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而成立的应受责难的主观拟制状态,这些谨慎的合理的行为标准主要是指那些保障主权权力得以审慎、正当地行使,以及各种法定义务得以遵守和履行的行为方式、内容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它可以是普适性的行为方式准则,也可以是在个案中更为具体的行为细节等要求。这些谨慎的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保证了与之相关的法定义务得以遵守和履行,同时,其自身也可以是或逐渐转化为实在法上的法定义务。但是,谨慎的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并不拘泥于或限制于现行的实在法上的明确规定,它所依据、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秩序存续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要求,其内涵是一定时期内被广泛接受的谨慎合理的行为标准观念和要求。通过分析适用这样的行为标准观念和要求来界定行为主体的过错状态,这就为一定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建设提供了保障和促进。同时,这样的客观过错与不法行为这一客观要件就得以区分开来,表现出其作为一个主观要件的独立价值与功能。
在国际社会里,认定国家行为的主观状态具有更大的困难和虚拟性,因此,以合理行为标准为基础的客观过错适宜于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程度等的分析认定。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措辞来看,“国际不法行为”的英文表述为“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而不是 “international unlawful acts”。 “wrongful acts” 这样的措辞体现了一种自然法上的观念要求和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国家行为不仅应符合实在法的要求,同时也应受到自然法的约束和调整。可以认为,谨慎的理性主体的行为标准与自然法之间有着内在的通约性,因此,“wrongful acts” 这样的措辞和内涵既反映了引入应用客观过错的必然性,也提供了适用客观过错来分析认定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程度等的基础。当然,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类似国内社会那样的纵向组织、社会权威和高度聚合性等特质,所以,除了条约、习惯等规范外,国际社会不易形成公认的和普遍接受的合理行为标准的观念、意识。但是,国际社会要想维持基本的秩序就必须形成最基本的合理行为标准的观念、意识,并且这些行为标准的观念、意识将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不断丰富、强化。这些观念、意识不仅来自于条约、习惯等正式有效的国际规范,而且更多地来自于国际宣言、原则、国际舆论、国际实践等。它们反映了国际社会秩序及其发展的深刻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理行为标准可以极大地弥补条约、习惯等实然的法定义务的缺漏,并纠正其不当之处。因此,在国际社会里不仅应当而且可以适用客观过错来分析认定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如果国家确实按照谨慎合理的行为标准、方式而行动的,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便其行为在客观上违背了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或规范,也不构成不法行为责任。例如,在外空活动领域,发射国对其空间实体应当负有不碰撞损害他国空间实体的国际义务。但是,根据1972年的《空间实体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公约》规定,发射国对其空间实体相互间造成的损害,适用过失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某一发射国虽然表面上违反了不碰撞损害他国空间实体的国际义务,但如果不存在着过错,该国将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如果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谨慎合理的行为标准、方式而行动的,将因此构成一定程度的过失,并承担过失不法行为责任。如果国家完全抛开谨慎合理的行为标准,积极追求或放任国际不法行为的发生,如进行武装侵略,则将构成违法故意,行为国将承担故意不法行为责任。例如,同样都是一国飞机侵入他国领空的行为,如果排除客观过错的分析应用,那么,所有的侵入行为都将无差别地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然而,根据各自具体的不同情形,对这些客观行为依据合理行为标准进行客观过错上的分析判断,那么,客观表现类似的行为就可能分别是故意、过失甚至是意外所造成的,相应的国家责任的性质、程度及处理自然也就大不相同。
客观过错上的合理行为标准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秩序所要求或认可的常规情形基础之上,在一般情形下,常规的合理行为标准应该是过错认定上的最低限度要求,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存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趋势。但这并不排除特定情形下对具体行为的合理标准进行调整,以便更恰当地界定过错状态的存在与否以及程度等。总体而言,合理行为标准将根据主权国家在相关活动领域里的客观实际能力来具体确定。从国家行为具体实施的角度来看,国家行为总是由具体的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相应的合理行为标准应根据这些机构及其人员的实际能力和具体环境等调整确定。当行为主体拥有更强的客观实际的行动能力时,合理行为标准应被调整为更高的行为要求。例如,在发生船舶侵入他国领海行为时,拥有先进的卫星定位系统等侦测手段的国家的军舰将因此承担更高的合理行为标准要求,而不可能按照小型民用渔船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过错的存在及其大小等。当行为主体拥有较弱的客观实际的行动能力时,常规的合理行为标准则需要适当降低其要求,例如,一个国家存在着通信等基础设施极为落后、警察力量薄弱等状况,致使在某个个案情形中无法向陷于暴力侵害中的外国人提供通常情形下可以提供的紧急救援和保护,该国的过错及其国际责任的成立及幅度显然就需要按照较低的行为标准要求来衡量。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特殊的个案情形中,并且具有合理的正当性的条件约束下,才能根据行为国薄弱的客观能力适当地降低合理行为标准的要求。如果一个主权国家频繁而广泛地不能按照常规的合理行为标准来行动,而且也不积极努力地改善这种状况,那么,即使该国确实存在行为能力薄弱的客观情形,该国在总体上也将构成一种概括的过错状态。因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国际主体,主权国家有义务努力提升自身的实际能力,并尽量按照常规的合理行为标准来行动。如果主权国家放任自流而不履行作为一个合格国际主体所应承担的这些义务,那么,这些放任行为和态度将构成一种概括的过错,国家将在此基础上承担相应的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唯此,才能促使主权国家真正成为合格的负责任的国际主体,促进国际社会全面健康的治理与发展。
注释:
① 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A/59/565,2004年 12月,第 204段,第207段,第55页。
②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14 November 2001, WT/MIN (01)/DEC/2.
③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ile countering terrorism, A/HRC/7/L.20, 20 March 2008.
④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WHA59.2, 26 May 2006.
⑤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sharing of influenza viruses and access to vaccines and other benefits, WHA60.28, 23 May 2007.
⑥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sharing of influenza viruses and access to vaccines and other benefits, Outcome of the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f Member States on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sharing of influenza viruses and access to vaccines and other benefits,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 A63/48, 14 May 2010.
⑦ 2008年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指出,必须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并履行根据适用国际人权文书与卫生有关条款所承担的义务。Global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on public health,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WHA61.21, 27 may 2008.
[1]James Crawfo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2]路易·若斯兰. 权利相对论[M]. 王伯琦,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172.
[3]菲德罗斯等. 国际法: 下册[M]. 李浩培,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776.
[4]劳特派特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上卷, 第一分册[M]. 王铁崖,陈体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1: 258.
[5]刘杨. 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以近代西方两大法学派为中心的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1, 68−69.
[6]林德木. 国际税收中国家责任问题研究[J]. 涉外税务, 2004,(2): 35−40.
[7]Louis 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Case and Materials [M]. Eagan:West Publishing Co., 1993: 552.
[8]布朗利. 国际公法原理[M]. 曾令良, 余敏友, 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487, 488.
[9]古祖雪. 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J]. 法学研究,2007, (1): 135−147.
[10]张爱宁. 论强迫失踪罪——兼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J]. 环球法律评论, 2009, (2): 143−151.
[11]David P. Fidler. Influenza Virus Sampl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J].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08, 14 (1): 88−94.
[12]贺小勇. IMF〈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对中国汇率主权的影响[J]. 法学, 2008, (10): 48−55.
[13]Saira Mohamed. From Keeping Peace to Building Peace: A Proposal for a Revitalized 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Council[J].Columbia Law Review, 2005, 105(3): 809−840.
[14]秘书长报告.履行保护责任, A/63/677, [DB/OL]. [2009−08−10].http://www.un.org/.
[15]赵洲.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57−63.
[16]松井芳郎, 佐分晴夫, 坂本茂樹等. 国际法[M]. 辛崇阳, 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18.
[17]邵沙平, 余敏友. 国际法问题专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29−131.
[18]詹宁斯、瓦茨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 第一分册[M]. 王铁崖, 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406, 416.
[19]英戈·冯·闵希. 国际法教程[M]. 林荣远, 莫晓慧,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182.
[20]曾令良, 尹生. 论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法律控制[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4): 34−45.
[21]张乃根. 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J]. 法学家,2007, (3): 95−101.
[22]张民安. 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