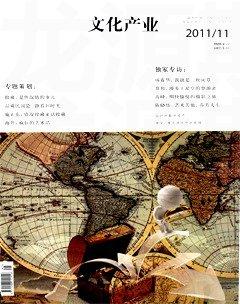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奢侈品
吴虹飞
一个朋友刚从日本回来,在东京机场附近的手工艺品商店里买了一包皮革。不是成品,只是未加工的一堆皮子,零碎,大小形态不一。她兴奋地对我一一展示:这是牛皮,这是羊皮,你看纹理不一样的,手感也不同。
买到原料皮革,是她日本之行的收获之一。她有手工的习惯,早就想给自己的单反相机做一个皮套。日本的手工艺品商店让她遂了心愿,终于有机会“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皮具了。这也是由她自己定义的奢侈品,因为用的是真皮,要花工夫设计、缝补,纯手工。
手工制作已经很难找寻了,这一传统正日渐走向消亡。这也许是人类为了更丰裕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凭借着无限趋于合理的经济和技术手段,我们能够生产出的物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快速,可也越来越丧失生命的质感。走在琳琅满目的超市里,你不会对其中的任何一件物品报以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都是从流水线上速生的,可以相互替代。你只是简单地消费它们。你并不想真正拥有它们。
和这样的消费品比较起来,另一类商品和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联结,它是奢侈品。你很快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需要我们掏出更多的钱。
人总要有一两件“贵重”“特别”的东西。这贵重特别,不光是指花很多钱,还意味着费心思,寄托感情,作为纽带。它们通常是礼物,别人送的,或是自己送自己。它们脱离了消费品的层次,变成了奢侈品。时间流逝,但它们却并不一同湮灭,相反,越发显得有味道了,耐品味,具有仪式感。
人类用很多东西,来对抗时间的流逝,比如诗歌。看起来,奢侈品也有着类似的功效,它的价值,有时会随着时间而越发珍贵。
我们当然已经排除了那些穷奢极欲的、只属于极少数富豪享用的专利:上亿的别墅、拉斐的陈酿、游艇、私人岛屿。我们说得是,可以用心思经营,赋予它特殊意义的那些物品。
我的奢侈品呢?是一支名叫“幸福大街”的乐队,我小心翼翼地呵护她,使之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女主唱乐队。我用她来示爱,我曾经深爱的一名年轻男人,直到他结婚生子,我却能在遥远的云南找到他。为他上演一场十年的演出。音乐是我的奢侈品。她使得我活在这个悲观的世上,却永远不会绝望。
好像是那个历史上捐款最多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资本主义就是把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他是在表彰市场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惠及普罗大众的效率。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大众消费品的时代,怎么样避开流俗,保持对于奢侈品的品位?
除了寄托情感,奢侈品还是一种用于社会炫耀的东西。敏于观察的社会学家早就告诉我们,这种炫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似乎也是有益的。这是个竞争社会,当优胜者无法再用征服、奴役、等级制度这些传统方式来标榜时,就用炫耀性的消费、巨大的排场、精心的雕琢、繁冗的仪式,甚至是有意的浪费,来让自己显得卓尔不群。
充斥着奢侈品的上流社会就一定有品位?不尽然。马丁·斯科塞斯的《纯真年代》就刻画了这样一个纽约上流社会众生相:极尽礼数、体面,却对真正的生命热情浑然不觉,对物有最精细的鉴赏力,对生活的品位。充满着陈腐的偏见,却自以为高明。
如何对待奢侈品,应该把斯科塞斯描述的场景当成一个反面的教材。生活在别人的意愿中,没有好奇,没有执着,没有珍重,也不曾真正感受——这其中。你一样可以奢侈,却不会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