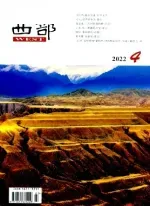鬼 脸
文/时光
鬼 脸
文/时光
做鬼脸是要讲究技巧的。
当你对着某个小孩第一次做鬼脸的时候,一定要偷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小孩,一种见了鬼脸会笑,一种见了会哭。如果你遇见了看到鬼脸会笑的小孩,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光明正大地继续做下去了,这个时候,小孩身边的大人也多半会露出善意的微笑。
如果你不巧遇见了看到鬼脸会哭的小孩,那么你可要小心了。我敢打赌小孩身边的大人就算不骂你,也会狠狠地用眼睛剜你。而那个哭泣的小孩,则会一直用惶恐不安的眼神注视着你,直到你自己也觉得惶恐不安为止。
很显然,小黄毛属于后者。
上火车的时候,小黄毛被她妈妈抱在怀里。我提着行李跟在后面,出其不意地冲她做了个类似狐狸的鬼脸,那丫头马上跟被雷击似的,哇哇大哭起来。我若无其事地弯腰整理行李,小黄毛的妈妈则看看后面,又有些急躁地安慰着她。
小黄毛看起来不到2岁,头发又稀又黄,因此我给她取了“小黄毛”这个绰号。
我想小黄毛如果有丰富的语言能力的话,她此刻一定会说:“我靠!真是冤家路窄!”
小黄毛和她妈妈正好是我的下铺,我睡中铺。小黄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安置行李,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爬上中铺,她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安,似乎担心我随时会变成狐狸。
为了不让她失望,趁她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我又冲她做了个鬼脸,然后无辜地盯着窗外发呆。小黄毛又哼哼唧唧地腻到妈妈的怀里,还不时偷偷看我。
我在心里笑开了花。
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窗外是南方那种梅雨天气,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雨。我的上铺和对面的上铺都没有人,对面中铺是一个中年妇女,一上车就开始睡,而下铺是个看起来挺帅气的小伙子,躺在铺位上不停地发短信。
我翻了几页书,觉得百无聊赖,于是爬下来坐在小黄毛对面的座位上。小黄毛坐在铺位上,玩着一个脏兮兮的洋娃娃,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便再也没有从我的脸上转移开,仿佛我的脸是一个神奇的变形金刚似的。
小黄毛的妈妈也染了褐黄色的头发,头发很随意地束在一起,像干草一样,因此我打算叫她“大黄毛”。
大黄毛不停地从地上的大黑包里拿出各种东西,比如奶瓶、饼干、水杯、卫生纸林林总总。她的黑包很大,看起来却不重,包的底部,隐约堆着几个玩具。
趁大黄毛不注意地时候,我翻着眼睛吐吐舌头。小黄毛马上爬到大黄毛身侧,一只手紧紧抓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我,嘴里叫着:“妈妈……妈妈……”
大黄毛看了看我,笑笑,又抚了抚小黄毛的头发,安慰她。
我也笑笑,对小黄毛说:“叔叔和你玩好不好……”
小黄毛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哇地大哭起来。

早知道小黄毛这么爱哭,我就不逗她了。
她恐惧地望着我呜哩哇啦地哭了五分钟,仍然没有休息的势头,哭得我心里也毛毛的,好像我的脸真的是鬼脸一样。
我有些烦躁地站起来,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抽烟。
洗手间的空气比车厢里好很多,窗户半开着,内侧焊了铁架子,上方贴了标识牌,有两个,一个是禁止从窗口向外扔东西,另一个是禁止将手伸出窗外。
我这人骨子里是有点贱的。本来没打算把烟头扔到窗外的,这标识倒提醒了我,我把烟头掐灭,从窗口扔了出去。
切,就算把东西扔出去又怎样呢?我不屑,又把手伸到窗外。
当然,纵然我再贱,也没有贱到不要命的地步。说是把手伸到窗外,其实只有四个手指伸在外面而已,我不敢伸出去太多,只伸到了中指第三个指关节的位置,我的镀金戒指正好压在车窗上。
突然,我感觉有个冰冷的小手握住了我的手指,紧接着眼前一黑,火车进入隧道了。
我急忙缩回手,看着窗外近在咫尺的黑暗,恐惧地摸着厕所的门把,却怎么也打不开。
还好,火车很快驶出了隧道,我的世界又恢复了光明。恐惧稍稍驱散,但是那种冰冷的触感依然停留在指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婴儿握过手,如果握过,就一定能明白那种细软、有力却又无助的触感。
出了厕所,车厢里的方便面、瓜子皮儿和臭脚丫子的味道,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让我感觉我又重返人间了。我重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小黄毛和大黄毛都不见了,卫生纸和各种生活用品凌乱地散在床上。我在裤子上蹭蹭手,觉得这么蹭一蹭,就能把那种恐怖的触感蹭掉。
很快,大黄毛抱着小黄毛回来了。
小黄毛安静地睡在她的怀里,那个看起来挺帅气的小伙子把手机放进裤兜里,嘟囔着:“可算是不哭了。”
大黄毛把小黄毛轻轻放在铺位上,头冲外,脚冲里。
我心里对小黄毛有几分歉意,于是忍不住关心的说:“还是头冲里面吧,外面来来往往的,小孩睡不踏实。”
大黄毛向铺位里侧看了看,里面堆着各种杂物,她看看我,微笑着摇摇头。我想大概是抱着孩子不方面整理那些东西吧。
我又在下面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天空渐渐变成了阴沉的黑色,才打着哈欠爬上床。
上去的时候,小黄毛睡得很安详,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莫名又想起了刚才厕所窗外的小手,脊背升起一阵凉意。
小黄毛看起来怪怪的,可是我又说不出是哪里奇怪。
虽然我是个男人,但却有些娇气,一到外面就睡不踏实,尤其是在火车上。
那个晚上,我梦到自己飘飘乎乎地悬在乌云的顶端,突然轰隆隆的雷声大作,继而下起大雨,眼看自己就要坠入无边的地狱。突然,一只冰凉的小手拉住我,我看不清那小手的主人,只感觉那冰凉的触觉顺着我的指尖,一路蔓延到全身。
我腾地坐起来,头碰在上铺的铺顶上,脑袋里顿然敲起了闷鼓。
我松口气,窗外的黑色急速向后流去,火车仿佛潜行在墨汁里一般。
车厢里相对安静,各种气味弥漫着,呼噜声形态各异。
我揉揉脑袋,迷迷糊糊向床下爬去,恶梦后,我习惯抽支烟。
我顺着铺梯,摇摇晃晃地爬下去,突然,脚下一种奇怪的触感,仿佛踩了一个巨大的肉虫子一般,急忙俯身,看到自己一只脚踩在小黄毛的脸上。我那巨大的脚丫子几乎覆盖了小黄毛的整张脸。
我急忙抬起脚,做好了她呜呼大哭的准备,然而她没有哭。
她脸色苍白,依然睡得很香。
我小心地下了地,颤抖着将手探向她的鼻息——她死了。
我呆坐在对面的座位上,脑子里一团乱麻。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未探过别人的鼻息,我不确定小黄毛是不是真的没有呼吸了。
食品科学与技术行业相关专家表示,中国食品工业要提质增效就要走出去,“一带一路”增加了我国食品走向世界的机会,食品的全球化将有效推动食品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有助于我国食品企业更好地掌握全球食品需求动态,掌握食品产业现状,促进企业发展。
于是我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鼻边,感觉了一下,又慢慢把手探向小黄毛。她,确实没有呼吸了。
这个时候,大黄毛突然醒了。她看到我放在小黄毛头顶的手,她一把把小黄毛抱着怀里,怒视着我。
我讪讪着笑着,也没有了抽烟的兴致,忐忑不安地上了床。
我在等待,等待大黄毛发出哀嚎的那一刻。然而没有,下铺悉悉索索了一会儿,又安静下来。
难道,大黄毛没有发现她的女儿已经死了么?
第二天,我被一阵小孩的嬉闹声吵醒,睁眼侧头,发现小黄毛活蹦乱跳地正在跟对面下铺的小伙子嬉戏。
她并不茂密的头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揉揉眼睛,怀疑自己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小黄毛突然仰起头,看着我,笑了,她笑得很天真,又很冰冷,我无法对视这样的笑容,急急地转了身。
昨夜的,那是梦吗?
不,不是梦。
因为当我爬下床的时候,发现大黄毛慌张地将小黄毛揽在怀里,然后充满戒备地望着我。小黄毛也看着我.
为了缓解气氛,我又冲小黄毛做了个鬼脸,没想到小黄毛不但没有哭,反而笑了,边笑边跟着我一起做鬼脸。
小孩子是不会装的。今天的小黄毛和昨天判若两人,难道是她觉得和我熟识了么?
她咿咿呀呀不知道说着什么,从她妈妈怀里挣脱出来,开心地蹒跚到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冲我做着鬼脸,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她在期待我和她继续玩下去。
我尴尬地笑笑,勉强挤出一个鬼脸,我第一次觉得,做鬼脸是这么不好玩的事情。
小黄毛开心地笑着握住我的手指,我一个寒站起来。
这种触觉,和昨天厕所窗外的太像了,不同的是,小黄毛的手是温热的。
这个时候,车厢的另一侧突然一阵骚乱,有好几个客人嚷嚷着,自己的钱物丢了。大黄毛一听,立刻把小黄毛从我身边抱走,并且充满怀疑地看着我,仿佛我就是那小偷似的。
我不理她,攀上铺梯把行李扯下来检查了一下,还好,我并没有丢什么。
车厢里其他客人也如梦初醒纷纷检查自己的行李。于是,有的人骂骂咧咧,有的人谢天谢地,乱作一团。
就这样,人心惶惶地又到了晚上。
十点钟,车厢里熄灯了。
大黄毛抱着小黄毛从车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边走边颠,小黄毛终于睡着了。
大黄毛依然让她头冲外面,小黄毛依然睡得和一个死人一般。
她的小脸在黑暗中很模糊。
大黄毛放下孩子后,就匆匆去了洗手间,我颤抖着把手伸到小黄毛鼻头——小黄毛没有鼻息,小黄毛又死了。
我听说过冬虫夏草,就是冬天是虫子,夏天会变成草。难道这小黄毛也是非常人类,白天活人,一到晚上就会变成死人么?
旁边厕所传来开门声,我急忙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我能感觉到大黄毛冷冷地注视了我几秒,才躺下睡去。
卧铺车厢里,增加了乘警昼夜勘查,我其实挺想报警的,但是鉴于自己昨天那一脚,又怕洗不清罪名。
大黄毛很快就睡着了,乘警在车厢的一侧警觉地窥视着我,似乎怀疑我就是小偷。
我不安地爬上床,怎么也睡不着。
黑暗里,总觉得有一双冰冷的眼睛透过床板,直直地望着我,像冰冻的针尖一般,密密麻麻的。
有时,我又感觉急速行驶的列车车顶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他们的四肢就像壁虎一般,在车顶上爬来爬去,也有几个小孩,顺着厕所半开着的窗户探进手,专门等着和上厕所的旅客握手。
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终于还是爬下了床。原本流淌着的尿液,在我落地后马上聚集到了下腹,我看了看厕所的方向,打了个寒战。
弯腰收腹屏住呼吸坚持了几分钟,我咬咬牙,向厕所走去。
厕所的窗户依然半开着,外面依然下着雨,空气湿冷湿冷的。
我没敢反锁门,以方便遇到危险时赶快逃脱。我一个大男人,撒尿被看见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命比脸面更重要。
就在这时,厕所的门突然从外面反锁上了,火车又进入了隧道,整个窄小的空间里更加乌黑了,有什么湿冷的东西打在我的脸上,我吓得大叫起来,左右扭动门的把手,却怎么也打不开。
乘警们在外面敲门的时候,火车已经出了隧道,我慌乱地打开门,一头撞在乘警身上。
“厕所门怎么锁了?!”我颤抖着。
乘警冷冷地看着我:“火车快到下一站了,厕所停止使用,自然会锁。还有,你上厕所怎么不自己锁门?”
我张着嘴,从脸上抹下一件东西,抓在手里一看,是一张湿湿的百元人民币。
“你在厕所干什么?”乘警紧紧抓住我的手,拿出手铐。
“尿尿……”
“尿尿脸上怎么贴着钱?”车警把手铐拷在我的手腕上。
很显然,我被怀疑是小偷了。
很可能,在我熄灯后坐在下面座位上发呆的时候,就已经被怀疑了。
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也不是小偷,我是做假证的,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赚钱,我没有不劳而获,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下一站被带到车站派出所
“我是警察。”我说,“我的证件在行李里。”
乘警一脸狐疑地跟着我来到行李架前,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摸摸索索地从行李里翻出一个证件,那是我的假警官证。
当警察是我的梦想,可惜此生无法如愿。原本想着拿着这个假证件回老家耀武扬威成为乡邻的楷模,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我在休假,没想到碰到小偷。钱是从厕所车窗里飘进来的。”半句真话,半句假话,乘警相信了。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如果不积极协助乘警查案,那也就显得太没有职业操守了。
我看了一眼死小孩小黄毛,她依然“熟睡”着。
也好,如果和乘警一起去询查,不但可以暂时离开这诡异的车厢,还可以藉乘警人多势众壮壮胆。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那从厕所车窗飘进来的钞票就是线索……”
那个乘警说:“我觉得也是,说不定小偷是把赃物通过车窗扔出去呢。”
“这种可能行应该很小”我尽量让自己像个警察。
很显然,把钱从车窗里扔出去是不现实的,车速那么快,任何东西扔下去,都可能被带到车轮底下,或者碰到后面的车厢,或者被吹得无影无踪,即便有人接应,成功的几率也很小。
我这样分析了一通后,乘警有些敬仰地看着我,感叹我不愧是专业的警察。那意思好像在说,其实乘警都是警校毕业考试时不及格的或者走后门的才能当上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摆摆样子吓唬人而已。
真正的警察,是应该像我这样的。
我不由有些飘飘然起来。以前卖假证的时候,我老跟那些买家说,你觉得自己是真的,时间久了,你就真的成了真的了。
此刻,我觉得自己就是真的警察。
我大模大样认真地询查着车厢,注意着每一个可疑的人,每一个可疑的细节。
可是半个晚上下来,还是一无所获。
厕所里飞来的百元钞票虽然是线索,可我们勘查了厕所之后,也并未发现可疑之处。原来当警察是如此辛苦。
很显然,在警察捉小偷的游戏里,警察是吃亏的。小偷的脸上没有写字,警察的衣服上却写了字。
于是我转头对乘警说:“我们分头行动吧,你穿着警服,我们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注意。我一个人行动,比较隐蔽些。”
乘警点点头,我们分头行动。
火车继续在急速行驶,玻璃上到处是撞墙而死的水珠。
我继续巡查下一节卧铺车厢。
车厢里静中有闹,形态各异,那些狭小的空间里,躺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像喝醉的尸体一般,或者一动不动,或者翻来覆去,或者咬牙放屁。
突然,我感觉衣角被什么东西扯了扯,回头一看,冷汗立刻湿了内衣。
昏暗的车厢中,小黄毛光着脚站在地上,扯着我的衣角,冲我做了个翻白眼吐舌头的鬼脸。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像鬼脸的鬼脸了。
我张大了嘴巴,却叫不出声,四周的人们依然沉睡着,小黄毛旁边的下铺,一个男人打着呼噜。
“熟睡”的小黄毛不可能自己穿越好几节车厢,跑到这里来对我做鬼脸的。
我捂着嘴巴,转头便向回跑。
不知不觉,我跑到了自己的车厢,气喘吁吁地靠着车窗,低头,发现大黄毛不知道什么坐了起来,她抱起“熟睡”的小黄毛,充满敌意地望着我,大概是怕我抢走她的死小孩吧。
我被大黄毛盯得毛毛的,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洗脸间,用冷水冲冲脸,看着镜中的自己。
列车一阵剧烈地晃动,斜对面厕所的门被晃开了,冷风拐了个弯儿,扑在我的脸上。
我咬了咬牙,妈的,死就死了!大概董存瑞英勇就义前也不如我现在的感觉悲壮。
我一步一步地挪向厕所。
厕所里,半开着的车窗上,露出一个小孩苍白僵硬的腿,以及半截屁股。
我又吓得瘫软在地,但随即又马上站起来。
因为我发现那半截屁股,不是圆的,是方形的,就像一个玩偶的屁股一样。那些玩具厂商,在做洋娃娃的脸的时候,惟妙惟肖,但是对它们的屁股却不怎么用心。
我定定神儿,确定那不是一具小孩的尸体,而是一个小孩大小的玩具娃娃。
确定了这一点,我鼓起勇气走近,一把把它扯下来。
洋娃娃刚刚碰到我的手,它的小手马上紧紧贴在我的手上,把我吓了一跳,难道是电影里的恐怖娃娃吗?
仔细一看却不是。
洋娃娃的手贴住的并未我的手,而是我的戒指。我那戒指,看起来黄灿灿的,其实是为了回老家充门面买的假戒指,是铁的。
原来,那洋娃娃的手掌以及脚掌上,都牢牢的粘贴着一大块吸铁石。
这个洋娃娃的肚子已经裂开,里面塞着各种面额的钞票。
我突然笑了。
我想,我大概找到小偷了。
当我带着乘警走到小黄毛扯我衣角的那节车厢的时候,小黄毛已经爬在铺位上睡着了。
这才是她睡着的样子,甜甜地,皱着小眉头。
每个人睡着以后都是有表情的,面无表情睡觉的人,不是死人,就是假人。昨天夜里的小黄毛,就睡得面无表情。
乘警把小黄毛旁边的男人推醒,给他带上了手铐。
另外一边,大黄毛也被其他乘警拷了起来。“熟睡的小黄毛”肚子上有个拉链,拉链拉开后,各种型号的手机哗啦啦地掉下来。
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巡视的乘警,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说实话,我还是有些佩服大黄毛夫妇的,做小偷用心如此,看来也非等闲之辈了。
他们的大包里,塞着好几个和小黄毛一样大小的橡皮娃娃,连头发都很像。我想,他们大概就是依据玩具娃娃的造型,给小黄毛剪的头发。
其实,那些娃娃和小黄毛也不太像,不过小孩的样子多数都差不多,况且小黄毛本来就是普通的小孩,晚上在昏暗的车厢里,很难辨别。
上车的时候,大黄毛和他的丈夫一人带着真孩子,一人带着假孩子,分别上了不同的车厢。为了避免其他乘客疑心,他们一到晚上,就会交换一次小孩。也就是说,白天小黄毛在我们这节车厢里,而到了晚上就被她爸爸抱走了。那睡在我下铺的,是个玩具。这样外人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抱的是假孩子,两个车厢的人,都看到过活蹦乱跳的小黄毛。
负责偷窃的是大黄毛,她的老公负责放风。
为了方便藏匿赃物,她不得不让洋娃娃小黄毛头靠外睡。
每当洋娃娃装满的时候,他们就把它的衣服脱下来扔掉,然后在它们的手掌和身上固定好磁铁,从厕所的窗户吸到列车的外面,这样就算引起怀疑盘查赃物搜他们的包,也不会查出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再拿回来塞到包里溜之大吉。
当然,未来得及放到外面的赃物也很安全,没有人搜查一个熟睡的小孩。
然而,真小偷遇到了假警察,只能坐以待毙了。
我到站下车的时候,那个乘警很庄重地冲我行了个礼。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真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