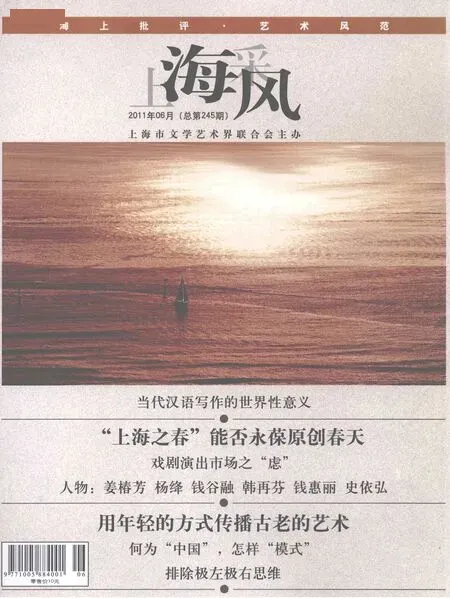百岁杨绛的情感家园
文/乌尔沁
百岁杨绛的情感家园
文/乌尔沁

杨绛近影
上海世博会倒计时进入100天时,上海《文汇报》世博特刊想邀请一位百岁文化老人题一个词。观遍文坛他们自然想到了出生于1911年的杨绛先生。经过一番电话联系,出人意料的顺利,一百岁的杨绛提笔熠熠写下:“百年梦圆,近在百日”八个丽字。文后落款“百岁杨绛敬贺”。幼年生长在上海的杨绛有时候喜欢说阿拉上海人。世博特刊杨绛题词让我不由想到了公元l9l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并且在文章里面虚构了100年之后在中国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画面情景。l00年后今天万国博览会的旧梦果真变成了现实。
人们知道,钱钟书先生在世期间,只管埋头面壁潜心读书,对于面前世界的高温恭维,钱老不断虚心谢绝。比如辞谢法国总统曾经授予的法国骑士奖章,比如婉拒中国文联授予的荣誉委员,以及诚意谢绝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荣誉称号,等等。钱钟书曾经对杨绛说过,以后我死了不要开追悼会。杨绛回允说,这在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身后的事情恐怕由不得你呀。不过后来还真替钱钟书做到了。钱钟书先生应当是著名文化人中间唯一死后没有开过追悼会的人。
央视《东方之子》曾经希望访谈钱钟书。钱先生坦言:我不是东方之子。钱钟书对媒体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吃了鸡蛋,为啥还要看生鸡蛋的鸡呢?钱先生做人的态度一贯都是低调平和,一直到他最后辞世;遗体进入火化堂之前,身边仍然没有热闹、没有鲜花、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或真或假掩面泣祭的送葬队伍,只有以杨绛先生为首的少数几人在真诚悼念。有一种民间说法是:送葬扶灵一等遗苦是人家家里私事情,旁人不好搅扰叫真。再者人呼海啸围进八宝山所谓悼念根本就是一个天大幌子。如果对逝者生前态度好一点,比披麻带孝更实在更人情。前辈活着时候,应该与他为善。
钱钟书离开十数年以后的今天,已经熠熠100岁寿的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仍然继续为人低调,并且仍然继续不配合不接受不享受实用性的新闻媒体的采访。杨绛为自己家乡上海《文汇报》世博特刊表达心意,显然是属于破了一个格。其实按照实际水准,杨绛先生也太配得上著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称谓。所以她为上海《文汇报》世博特刊题词名正言顺。1956年钱钟书升为一级研究员时对杨绛说,“你可能永远是三级了”。不过杨绛先生并不在乎什么级别。她披上了特殊的隐身衣自得其乐说:“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不睹。”隐身衣的故事是杨绛先生一直都喜欢的童话。
杨绛习惯自称个人是“零”。他们夫妇解放前夕不肯离开祖国,并且决意留待全国解放,甚至准备做“没有用的知识分子”。所谓的“零”,就是安安分分坐他们读书写作的冷板凳,不问人间的流年事不就成了“零”吗?虽然是一个“零”,但是杨绛仍然比较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她并不自暴自弃,人家眼里没有你,心上不理会你,她正好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何况身处卑微的人,无需显身露面,最有机缘见识世态人情的真相。现在的杨绛仍然恬淡,机智幽默,勤恳伏案,享乐人生。
杨绛出自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岸边做过一定级别的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l945年)名字中间的“荫”是一个严格辈分,犹如杨绛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做荫枌和荫榆一样。名字的“杭”则是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并不是自己母亲的知识,而是妈妈和爸爸的和谐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
或许可以说,这良好情感也蕴含江南水土滋育的关系。说真心话,我们这些晚辈无论如何也不好想象年轻时代的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前辈深挚的情谊友爱,是怎么样的风致娟好,是怎么样的衔华佩实。倒是在先生们晚年的一些时光里,我亲眼如实地看到了古稀年岁当中这一对白发伉俪仍然恩情如初的感人场景。
杨父荫杭膝下有8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杨绛上边有3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杨绛最早的地位。杨家8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杨家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的偏怜女,所以动不动就可以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比如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沾不上边。不过杨绛从小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从来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也不和弟妹争宠。杨绛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杨绛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也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过杨绛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滋有味。父亲休息时候,杨绛乖觉拿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静静地翻。父亲一觉醒来就会看到小天使一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小女是多么宝贵的“小棉袄”啊。
杨绛出生北京未满百日已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杨绛4岁时又随父母重返北京。杨绛生活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初住在东城,房东是个满族人。杨绛开始见到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京城满族妇女。她们的鞋子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跟的,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或者又叫做“马蹄底”鞋。这种满族鞋木底一般高5至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她们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一摇一晃。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呢?”杨绛认真想了一会儿回答:“要”。多么可爱。显然属于一口奕奕的淑女回允。
杨绛6岁进入老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不是别人正是杨绛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学校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吃得吧嗒吧嗒面前还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其他的小朋友看见了也都学杨绛的样子。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为他暖鞋,从父亲角度考虑许多问题。

童年是成年的雏形,杨绛成年以后的故事也是她个人少年时代的动感写照。杨绛总是能够给人一种江南温情的女性印象。她的样子一直都是: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体态端庄。身上没有多少所谓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和理论容颜。杨绛见到人总是和颜悦色,杨绛说话往往慢条斯理,举止言谈温文尔雅。了解杨绛的人说她是一个才貌双全的闺淑女子,同时又是一个南方水营养出来的文弱书生。钱钟书在文学所任职的时候,与杨绛总是同进同出形影不离,让太多的人羡慕感叹。曾经以往,杨绛随一批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钟书每日一信,写给杨绛,字小行密,情意绵绵,生动有趣。
这时候杨绛能够天天有钟书信读。杨绛回忆说,这是默存(钱钟书)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每一封钟书家信杨绛读了又读,总也舍不得丢,都收在衣袋里,衣裳每个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衣袋里装了十来封信就行动不方便了,杨绛只好抽出来藏进提包里。但是身上轻了心却重了。杨绛以为这些言情家信谁都读得,而且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经过许多政治运动的前人,谁的心理又对于无妄之灾不感到害怕呢?
后来,钟书来信攒多了实在无处收藏,杨绛只好硬硬心肠付之一炬。她在下乡锻炼的公社缝纫室泥土地上,当着女伴焚烧过两三次家信。如今杨绛只要谈起这件事,总是非常心疼和懊悔。不过她只好自己解慰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呀。如果信留下了,文化大革命敢不烧毁吗?再到后来,钱钟书自己也下乡,仍然偷空写信给杨绛,但是现实残酷到不能每日一封了。
“文革”初的1966年8月27日,被杨绛认为是她个人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了《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第一部已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这些译著可是杨绛的誊清稿未留底稿),到了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时,杨绛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阴阳头。钱钟书比杨绛还着急,说明天怎么出门啊?那特定时候的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天天等在牛棚候着挨斗。杨绛对于阴阳头不慌不忙灵机一动:她记起女儿阿圆剪下的两条大辫子存放柜里,于是用钟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做成假发,第二天早晨杨绛戴着假发出门了。
当时,无论年龄资格地位排名,她都属于最小,所以揪出来也晚。杨绛被揪出来后,那些革命武将对她的劳动惩罚是收拾办公楼两间女厕所。杨绛置办了小刀小铲子之类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从此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几天,厕所原先污秽不堪的地方被收拾得焕然一新,斑驳陆离的瓷坑,垢污重重的洗手盆,经过铲刮去掉多年积垢后雪白锃亮。厕所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厕所水箱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厕所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进来如厕者看见不免大吃一惊,当下就对杨绛顿生敬心。那会儿杨绛打扫过的公共厕所成为她的一个干净“避难所”。
当年“文革”中那些在河南一带劳动改造的大学者大作家甚多,比如沈从文、俞平伯、沈有鼎、何其芳等等,又比如钱钟书、杨绛等等。三四十年前钱钟书杨绛夫妇从河南干校活着回到北京,开始没有能够回到北京西三里河自己家,只能在研究所的办公室住了好长时间。对于干校劳动这一段生活改造,杨绛写下了有名的“心景日记”:《干校六记》。杨绛在《干校六记》里面回忆数十年前即将离开河南干校之前,跟钱钟书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心情对话——默存(钱钟书)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京城有太多从河南一些劳动干校归京的知名学者,他们后来这一辈子不但再没重返河南,甚至连路经河南的飞机都不要坐,一提河南,许多高级学者知名作家就心有余悸,说那里不是读书人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那里是专门整人之所。别说知识分子了,就连国家前主席刘少奇也罹难在那里。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大迁户,下农田、掏厕所、种青菜、烧砖窑、打机井、种棉花,甚至干一些毫无意义无功效的体力活。读书人一生总是渴望拥有一小角自己的读书园地,可是他们六十年代末期临下干校之前,书都烧了,志向毁了。河南当地人把读书人下放干校叫做“戴罪立功”。l998年秋学术界一大批知识分子合集出版过一本嚼着血泪的纪实著述《无罪流放》。

钱钟书与杨绛
钱先生在生活当中并不难接触,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难办的事情,特别是学问一类事情,他还是愿意出面帮忙的。有一次社科院里线装书库的年轻资料员找不到古旧版本的《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了,问谁都不灵,于是就打个电话给钱老。钱老在家想了一下,居然能够一五一十指点资料员,告诉书的位置放在哪一层哪一节,还把要找书的上下左右的书况认真描述,直到找见书。因为当年文革时有段机遇,钱老曾经长住过图书馆旁边的办公室,所以书又看了不少。对这段经历,杨绛在她的新著《我们仨》里写道:1974年5月22日我们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凡去过钱钟书家的人都晓得,其实他家里面的藏书并没有多少,完全不像顾颉刚先生藏书能开一幢个人文库,也不像戈宝权先生光是个人俄文版的书籍就足够装配一个图书馆。钱钟老记忆惊人,他把看过书的内容都藏进脑子里了。对于钱老学问,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称道: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李慎之先生也赞同说:《管锥篇》《谈艺录》征引书籍多达两千余种,还不包括许多中国无处找到的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什么错误,钱先生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国家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生前也不止一次夸奖: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ry。
依稀记得,曾经有机会陪同胡绳和吴全衡夫妇前去北京城东医院后楼探视钟书钱老。每每看见杨绛先生始终如一,尽心守护。因为当时钱老的病情不能顺利咽食,所以杨绛先生就每天从家里给钱老带来流食,亲手用食管轻轻把煎熬的新鲜鸡汁和鱼汤喂给钱老,这样一日三餐从不间断。亲眼看到:也已年迈的杨先生风尘仆仆,一天两次拎着保温饭盒从京城西头跑到城东,一跑就是连着几个月,风风雨雨的没有间断。别说杨绛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么来回折腾,恐怕也要受不了的。平常对于一些上门访者,杨绛先生坦言说:其实我们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什么偏见,主要是不想让他们写我们,怕打破了我们的正常和安静……
今天已经l00周岁的杨绛老人仍如曾经的平常日子,用普普通通的家常心,生活着工作着平和着。她说过钱先生已经去了,女儿钱媛也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打扫现场了。就在这样的心景之中,100周岁的杨绛先生依然身处原先一家人的温暖包围中间生活着。一个世纪老人就在这样一个“现场”里面,一笔一画写出了有血有肉的《我们仨》。她用一个世纪文化老人的缠绵动心之笔,书写着“我一个人思念着我们仨”的旧时光华日月。心情笔调不同人云亦云,点点滴滴都蕴藉含蓄。
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清华母校赠送杨绛先生一块四字名匾,上面书写着:寿与校同……历史悠久的清华学府不但是杨绛先生的母校,而且还是杨绛相识、相知、相随钟书先生的一处福地。愿百岁人心有福,寿长久。

乌尔沁 蒙古族。就职于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著有《沈从文先生的凤凰城》《顾颉刚先生的痛》《胡绳早期美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围城内外钱锺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