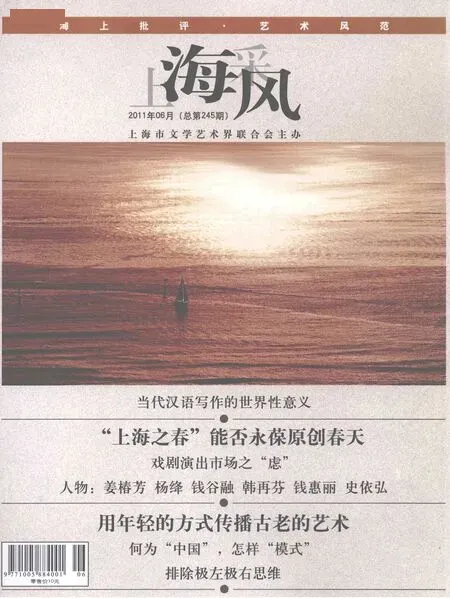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
采编/宗 和
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
采编/宗 和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如何在文化上给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则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如何构成当今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成为中国及世界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当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如何?艺术价值如何评价?汉语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如何定位?作家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我们写作的意义?这些都成为21世纪初中国文学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日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杂志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作家杂志社,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举办了“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近百位学者、批评家、著名作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探究了如何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对话,拓展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视野,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铁 凝

李敬泽

张颐武

王 宁

莫 言

刘震云

阎连科

王家新

杜博妮

刘 康

施战军

米吉提

陆建德

南 帆

张 柠

张未民
当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当代汉语写作有着怎样的世界性意义?这些成为摆在作家、学者、评论家以及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今世界上,我们如何看待和估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人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自己文学的价值,作家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我们写作的意义,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学也在逐步走向世界。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的作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在今天,一个优秀的中国作家,他的读者不仅在我们这片辽阔的国土之上,通过翻译,他的读者还可能在纽约,在欧洲的某个村庄,在亚洲和非洲的某个城市。我本人是一个写作者,我相信,这样一种情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在写作时你会感到,除了你熟悉的人们,你还可能面对着陌生的人们,面对着文化背景、文学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经验差异极为悬殊的读者,你在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和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书写,这时,你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这个问题摆在作家们面前,同时摆在学者和评论家们面前,甚至摆在中国的和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怎样站立在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又应该如何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文学,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发展,如何塑造和伸张自己的特性。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为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如何构成当今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当代汉语文学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汉语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如何定位,汉语文学是否始终在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它的世界面向如何展开?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21世纪初中国文学家必须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承担和开始的事业。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急于由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与欧美并肩,那么现在,中国文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并且在内部形成了“‘走向世界’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最近中国最热门的两部电影中看到这种变化,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小说,且都以“文革”这个最为封闭的时期为背景。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两个主人公的出国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相反,他们出国后选择再次回归,审视自己的国家,使故事得以公开。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会作为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给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源。
王宁(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1827年,歌德在接受艾克曼访谈之后提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文学的世界性概念的首次提出。如果说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乌托邦的话,在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赋予它以下三种含义。首先,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第二,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民族文学放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研究和考察,我们才能得出客观的国际性的理论标准。第三,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的演化。在这种意义下,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时候,我们应重塑中国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促使中国文学有效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这种意识正影响着作家的写作,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地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不过,在很多作家看来,无论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立足于“个人性”、“本土性”是首要的。
莫言(著名作家):关于作品的世界性,包括多个层面。一是知识层面,外国人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经验,他可以了解到他所不了解的中国一些独特的知识;另外,人性层面更为重要,如果是成为世界性的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必定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人的共同性的反应,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什么让中国的读者落泪,中国的《红楼梦》也能够感动外国的读者,这都是因为它们传达了一种共性。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应该强调个性化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则还是应该强调作家重在挖掘人的普遍性,当然也不要放弃语言、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艺术技术的探索。
刘震云(著名作家): 作为一个作者,意大利传教士和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我如果能把思想传给我的读者和我喜欢的人,我觉得就很有意义。
阎连科(著名作家):世界文学也好,中国文学也好,对我都不重要。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代作家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家人和土地是我们几代作家最根本的写作资源。然而今天居住和生活在都市,离早已变化的乡村和农人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连的农人。而失去他们,就意味着我们——尤其是我,对写作资源的彻底失去。写作到今天,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
铁凝:文学的根本精神是让人们的心灵能够相通,我们要敞开胸怀与世界各国人民对话,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我们要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学者的交流中丰富对文学的认识。但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我也经常地意识到,我的写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当我坐在书桌前时,我的书写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对着那些和我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同胞们。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呼应,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够自信地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来自我们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带着我们的作品加入到世界文学的行列。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创作,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作家,都必得首先立足于“个人性”,即从一个作家个人的独特、具体的存在开始。在我看来,写作无非是进入个人自身存在的一种努力。脱离了这种“个人性”,脱离了个人经验的具体血肉,任何对“本土性”的张扬都是可疑的。现在有人大谈“中国经验”,作为写作者,我们谁也不能代表。我们无非只是一些被代表者。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是这张“个人的牌”。文学从来就是个人的,把一个作家和诗人简单地视为某个民族或文化的化身,这其实是对文学的简化和取消。
汉语文学写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然而在一段时期内,汉语写作一直未能在国际上获得充分重视,一直被区隔于当代世界文学视野之外。相比较西方文学在中国的重大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遭致不恰当的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向全球文化中心挺进中有着怎样的短板,如何更好地让汉语写作走向世界是不少学者关注的话题。
杜博妮(悉尼大学教授):翻译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于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工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学者的关注度上都远无法与其重要性相称,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有很大的时间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思想、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先锋思潮。而随着九十年代思想先锋的告终,中国意识形态与写作的关系形成“多重幻象”。
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对新海外华人作品的评价需要一点谨慎和客观。因为第一,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出国,他们作品依托的场景、情境、气氛大多都是限于“文革”前后的一些时空,在历史和人性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有所积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第二,他们对于周围的认知基本上局限于当时的印象,对中国现代的印象,没有融入,在语言技法方面也没有新意。第三,他们的有些作品与我们期待中的世界认知无关,我们国内可以同步和国外的文学状况产生交流,但海外作家则在悬隔地带。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作家》主编):从现今的世界来看,我们拥有最佳发展机遇期,那种固执的冷战及后冷战思维已经渐行渐远,发达国家受众的眼光与欣赏品味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人真实的心境和生活。而这一点,对中文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可回避的是,在以往的作品中,我们广泛深入挖掘了民族劣根性,展示了我们民族群体的人性之恶,以期追求和抵达主题的某种深刻。但是,缺乏展示我们民族群体中的人性美的力作。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这一点,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体现。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精美之作问世。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回顾历史,我们需要检视。一百年前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怀疑中国文字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提出汉字应该废除并以世界语取而代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呼声甚至来自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核心。语言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对语言的否定就是对文化的否定。我们要注重汉语写作的重要性。另外当今汉语写作得到了认可,但我们不可仅把它作为社会记载来读,而应充分意识到其文学价值。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当代文学的经验不在于恢复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在于具有当下性的“本土”。 我们现在的民族是世界视野中的民族,当代文学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进行衡量。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文学向全球文化中心挺进中,试图将卡通版“国家吉祥物”式的作家,推到国际文学博览会上去。而我却想起了另一个看似游离实则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代汉语文学内部的“边疆想象”。近年来,重新叙述边疆世界的欲望被再度激活,它点缀了现代物质生活叙述的单一格调,同时也诱发了一种让人从现代文明中心抽身而去的冲动。我认为,文化交流不是商业贸易。在文学领域,越是边缘的越有可能成为中心。一个劲儿朝中心奔去,有可能永远是边缘。贸易线路图与想象地形图,有时候南辕北辙。
张未民(《文艺争鸣》主编):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明。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中国文学就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更进一步还要将其视为伟大的、具有弘扬古今轮廓的、具有连续性的审美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