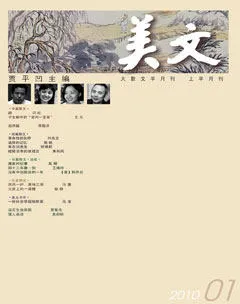比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
何平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做规矩的学术论文,也做不规矩的文艺评论和媒体书评。近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话说东北人高晖“编”了本小册子《康家村纪事》。说是“编”,不是“写”,一点没有鄙薄高晖精神劳动的意思。按我看,他也乐得承认是在“很好玩儿”地“编”,如其所说:“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有规划,后来——2003年冬天才发现:怎么写了这些关于童年和康家村的作品,为什么不单独编出一本呢?今年有了成段儿的时间才开编。”编着编着还上了瘾,据说康家村的事“纪”过了后还有两本康家村“人”与“物”的东西待编。
《康家村纪事》既出,自然由人评头论足。我留意了林林总总的说道,说得多的是技术。说技术是因为《康家村纪事》片段(1-8)、正文(1-6)、序言、附录和文本导读(1-5)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编”出来的大框子。其中最醒目的是游走于纪实和虚构,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片段”和“正文”。高晖说《康家村纪事》是“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应该说,高晖是尝到了“炫技”的甜头。几乎所有的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都觉得“此中有真意”。要知道,今天的文学早已是一个“非技术”的“浅”写“轻”读的时代。说“技术”,那是先锋文学好时代的事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的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散文的冯秋子、杜丽、钟鸣、张锐锋等等一干人马。现在去之十数年,想来好遥远,谈起来,大有“白发宫女说前朝旧事”的唏嘘不已。《康家村纪事》的“炫技”或是满足了过来之人凭吊一个逝去的先锋时代的幻觉。
但我说,《康家村纪事》的好处只是技术吗?就说技术,以我有限的阅读,只举一个例子,《康家村纪事》的这些招数至少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都曾经用过。当然这样说,我并不认为文学的惯例和程式不可以重复使用,相反的是如果高晖挪用这些惯例和程式且卓有成效,也许正证明这些所谓技术层面的惯例和程式也许就是人类面向自己记忆的本能和常态。当我们踏上记忆的返乡之路,我们所能打捞出的、记录下来的也许只能是这些“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虚构。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将对童年往事的书写不是处理成对暧昧、幽暗的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近乎绝望的追索,而是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没有迷途也没有分叉,恰恰是有悖常识的虚假的写作。《康家村纪事》的技术只不过是尊重文学,甚至是记忆术的常识。在这方面,较之前辈纳博科夫所做的,《康家村纪事》“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虚构还不能算“碎”和“虚”得彻底。
不是技术,那是什么?观念?我也注意到,一些人将高晖的《康家村纪事》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拉的《蒙塔尤》进行比附。比附前者,还算在文学道上向大师致敬。比附后者,如果高晖的《康家村纪事》真的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如果我们认为高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在建构一个正史不载村庄“小历史”,且把这作为高晖写作意义的全部和结果,那么高晖至多是一个有着田野调查癖好的地方志写作爱好者。事实上,《康家村纪事》这种只关心“我知道的”和“对我心灵有影响的”,远不能算称职的历史态度。因而,高晖的康家村村史至多只能是一个漏洞百出支离破碎的“一个人的康家村”而已。
是的,写一城一村一族一家一草民的成长史是近年的一种写作时尚。而我要说的,当下中国文学的“历史癖”正在伤害到某些文学本质的东西。批评界对这些作品关注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和“宏大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对抗。问题是文学的任务仅仅是提供一种不同于国家正史的“小历史”吗?必须警惕,“小历史”的叙述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对抗的文学政治学。当代中国文学往往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屡教不改。我认为当下以村庄“小历史”或者“个人记忆”为视角的文学书写,动辄就牵扯到对“大历史”或者“集体记忆”的祛蔽和反抗,正在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观念先行”和“政治正确”。而事实上,从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现实看,谁在压抑?谁在反抗?已经是一个新的问题。即使存在所谓的对抗性书写,除了持政治异见的文学书写依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文学的压抑和反抗也更多应该从这些非文学领域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审美惯例和审美创造之间的对抗性书写。所以,对于这些写“小历史”文学如果我们还只是将其全部意义设定在历史的真伪之辨上,显然是一个背离文学常识的伪命题。而且写小历史、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层史以及庶民日常生活也并不必然保证通向的就是文学之路。必须意识到:历史如何被叙述和历史如何被文学叙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而必须重新回过头来研究这些作品,看看其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历史”和“个人记忆”书写的文学性。也就是如果不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这些“个人记忆”或者“小历史”书写有没有自足的文学意义。
文学不只是一种“史余”一类的历史下脚料,但我不否认“个人记忆”可以获得一种见证意义,特别在我们这个习惯遗忘的国度。2009年台湾天下文化出版了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且用了一个词“记忆文学”。可以顺便说说《巨流河》,这本书大陆的三联书店最近出了删节版。《巨流河》无论是写作者自己,还是书中涉及到的政治人物、知名文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相当的公众认知度。在一个名人隐私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时代,《巨流河》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肯定会引起普通读者的关注。但我认为《巨流河》引起关注的深层原因,特别是被知识界关注,首先是因为它对何为历史,历史如何被叙述,个人记忆如何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获得意义等问题所作的思考这些“非文学”因素。布塔利亚·乌瓦什在其《沉默的另一面》说:“詹姆斯·扬格在写到大屠杀的回忆和证言时,曾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通过大屠杀得以流传下来的那许多方式,我们怎么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呢?他的回答是建议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了解大屠杀,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中国近现代史是“家”与“国”缠绕的,但在我们的叙述中常常却是“国史”淹没“家史”。我们说历史是谁创造的时候往往会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事实上人民群众参与的历史创造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却是沉默不语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人民群众却很难参与到历史的叙述,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对真正的印度历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