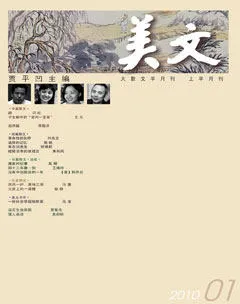一座被争议的宫殿
王潇然
公务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散文、随笔,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现居西安。
没有边界的皇宫
法家奖励耕战的主导思想,一方面刺激了民众建功立业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同时助长了秦人的功利主义倾向,即便是帝王也由此而沾染上了好大喜功的毛病。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引导下,嬴政登上皇位后,也一样开始大规模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型建设项目,借以彰显自己的功德。
在秦国的发展过程中,故都雍城、栎阳和首都咸阳,本来就有不少宫殿,如雍城就有封宫、平阳宫、羽阳宫、萯阳宫、棫阳宫、蕲年宫等。另外,还有许多遍布秦国各地的台观馆舍、凌阴冰窖。早在春秋秦穆公时,雍都的宫殿建筑就已经很有规模,经过数百年发展后,宫室更是有增无减,所以,秦始皇加冕时还到雍都蕲年宫,而他的母后离开咸阳后也愿意长期居住在雍都。自从秦孝公徙都咸阳,以此作为政治中心后,咸阳的宫殿建筑发展更快,规模更大。可是,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王朝越来越强盛,秦始皇的政绩表现欲也日益膨胀,原来的宫殿就再也无法聚纳下他更多的愿望了。
有人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穷奢极欲,为了贪图享受着手修建更大的宫殿阿房宫。其实,咸阳宫从兴建起算来也不过一百二三十年,在吞并六国的过程中还不断扩建,已经十分巍峨。有一个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荆轲刺秦的时候,随从的秦舞阳虽然也属杀人不眨眼的猛男,但是看到了庄严地皇都和威武的仪仗后,在走上咸阳宫殿前的高大台阶时,仍然被铺排的阵势给吓得颤颤巍巍,露出了一丝破绽,使嬴政有了提防,以致最后功败垂成。由此可见,咸阳宫绝对已经极具威严的气势了。所以说,兴建新宫应该跟咸阳宫落后不落后绝对没有多少关系。
秦嬴政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同时也一并在咸阳开始大兴土木。自雍门以东,到泾水、渭水之间的大片区域内,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并将从六国那里掠夺来的钟鼓、美人充盈其间。诛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更是倾尽全国之力,在渭河南岸又修建了极庙和信宫,在周都丰镐一侧营建阿房宫,这样,一个天地对应的皇都就粗具了基本的框架。从其布局看,以极庙为中心,北为咸阳,象征天上的紫微星,作为帝居。渭水横贯都城,象征天上的银河,河上架桥使南北相连,各宫殿园囿宛若散布两岸的星辰,如牵牛、织女一般相守相望。西南建阿房宫,为新都,是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极庙是城的中心,咸阳在亥方位属水,骊山陵在卯方位属木,阿房宫在申方位属金。天地对应,五行互补。一个城城相连、规划有序、独具匠心的秦大都便清清楚楚地展现了出来。从秦始皇崇道求仙的心理背景中,我们很轻易就找到了与这种规划思路的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始皇帝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只是做个国家的统帅,他要的是天地的主宰。
水生木,咸阳可以护佑着始皇的亡灵永垂不朽,所以是否能够实现死而后生的关键就在咸阳。金生水,申方位是咸阳可期的保障,要想帝业永固,就必须从阿房入手,建一所够分量的新都,才能给予咸阳应有的支持。从中不难理解,这完全就是一个有着深刻意图的信仰设计,他要完成的是一个从永远到无疆的期愿。
天下一统后,兴建能与咸阳和始皇陵相当等级的阿房宫就成了最为急迫的问题。阿房宫原有秦惠文王时紧邻周都丰镐营建的阿城,因为当时阿城还没有完全完工惠文王就晏驾了,工程一直就搁置在了那里,始皇便以此为基础,又重新规划,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设计规模,使之与咸阳连为一体,成为一座功能齐备、技术先进、理念超前的大都会,气象更为宏伟。离宫别院从渭河北岸到南山之巅,从老都雍城到栎阳至骊山,绵延300余里,大小殿堂700多所。这些大大小小的宫宇,构成了一个由点到面、由宫到城的建筑群体,而这一建筑群体后来被集中收纳进了历代文人的眼里,成为了史和诗中记载的阿房宫的全貌。
阿房宫原本是一座城,城中新建有宫,宫便以城命名。宫是城的一个最具身份的代表,城又因此而以宫的名义流传了开来。这时我们才发现,其实宫就是城,城也就是宫。那个狭隘的具体宫殿的判断,已经不再具有多少实质的意义了。
关于阿房宫的有与无、存与废一直都争论不休,但是载入史文的历史记忆却又异常的清晰。无论它的真实样子到底怎样,在中国人的心里其实早已搭建了一个磨灭不了的肖像。即便是走进三桥南面的田埂,也一样有一处处突兀的土台高冢,不断支持着我们始终都认定的猜测。
作为具体的宫殿来说,宫殿就会有一系列的配属设置,至少都会有前殿、朝堂与后宫,而史书中就明确记载了阿房宫前殿的样子。东西700余米,南北115米,占地8万平方米,这是一个有着相当于1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建筑。四周有阁道,从殿下直抵南山,以南山之巅为门阙。一侧修复道向北渡过渭水,抵达咸阳。由于南山海拔两千多米,从山顶的门阙到山脚的宫室各自处于不同的气候带里,所以在一天之中阿房宫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这简直就是一座恢弘到了无与伦比的帝都。
其实,无论是城还是宫,也都仅仅只是一些具体的建筑,再大都有边界。而思想理念上的建设,才是始皇真正的手笔。有形的宫殿只是他借以用来对于无形的政权所作的一个具体而又真切的说明。
从阿房宫的建造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神受的思想和君权至上的理念,也可以看到天地一统,恒定永昌的期愿。同时,还有主辅有序、恪尽职守的态度和法度严谨、各司其责的意识。从咸阳到阿房,是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是从今生到来世的转移。这完全是始皇对于帝国构架的一种别致的政治表达。阿房宫是为咸阳构筑的未来彼岸,而与此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则是为后世谋划的理想家园。
宫殿不一定就是房子
秦国没有多少大族的传统,长期处于与西戎较力的前沿边陲,民风民俗粗犷剽悍,东方各国都视其等同于戎狄。正因为文化积淀不多,所以主要针对士族分封与世禄的变法才有了施行的可能。这样,秦国也就注定了要成为法家的试验田。法家思想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主张,都在秦国得到了尽情的实现。商鞅开启了秦国图强的序幕,韩非完成了帝业辉煌的总结。
法家崇尚的法的作用,一是“定分止争”,二是“兴功惧暴”。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
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强大了起来,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统一战争。在统一的过程中,士兵们获得了一次次封地晋爵的机会,始皇帝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表现尊威的理由。他把对六国的征服,用一座座新的宫殿的落成,标注为一次次胜利进程的坐标。
公元前230年灭韩,建韩国宫。公元前228年灭赵,建赵国宫。公元前225年灭魏,建魏国宫。公元前223年灭楚,建楚国宫。公元前222年灭燕,建燕国宫。公元前221年灭齐,建齐国宫。
六国宫是对旧的国家秩序的打破,也是以咸阳为主的新的帝国的重建。就是在这种打破与重建中,中国从分封走向了集权。阿房宫的诞生,其实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座简单的宫殿了,它完全就是这种新的集权力量的直观表达和外在表现。
我们知道,文明常常要靠不文明的手段才能建立,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而没有沦为野蛮,就是因为它又必然有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秦国通过变法就获得了这种力量,所以中国的文明就开始以它的形式进行了重新塑造。
通过这个王朝的建筑构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个最基本的判断:一是功利主义思想的现实体现;二是军事力量的政治表达;三是国家意识的标明与塑造。
阿房宫就是通过树立皇权至上的思想,构建了一座超现实主义的帝国大厦,是对于一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搭建。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工程有还是没有竟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而那个对应于阿房宫的帝国设计竟逐渐清晰了起来。一个工程,两座建筑。天地对应,虚实两得。这才是阿房宫原本的真相。
阿房宫展现了始皇统一六国的具体梦想,也表达了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的文化大统一理念。而大统一理念的实现,才是真正的,也是最为彻底的统一。统一六国是国家边界的废除与新建,统一货币、度量衡是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推倒和重来,而统一文字则是帝国文化的打破与再造。
十年征战,统一了疆土,同时也把国家的管理方式推行到了全国。为了便于组织和交往,就必然还要进行同文、同币、同度等等的改革,以实现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对接。摧毁六国的城池和宫殿其实只相当于决斗时留下了伤疤,只要种子在,还会有青山。但是,文字的丢失却是信心与传统的毁灭。这种毁灭,对于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要迈出崛起的第一步,就必然需要经过这种血与火的洗礼,最终才能走向统一和强大。因此,文字的统一,正是文化的大破与大立。
破就会有流血,如同经历一次山河再造。然而,文化的重塑却往往险峻万状。因为文化是民族的一种沉淀,重塑就会翻江倒海,甚至会把塑造者也卷落进去,如同商鞅或者还是秦朝。商鞅是被卷落进去的人物,秦朝是被卷落进去的时代。
透过阿房宫的房檐,我们从那些不拘一格的建筑风格能够看到,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国家,它很包容。廊腰缦回、各抱地势的建筑群落,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一切都安顿得很有想法的社会结构,它开拓并且超前。只有这种结构有条不紊的国家,才能沉淀出具有清晰脉络的群体心理,只有拥有了那些具有创新意识和进取渴望的群体意识的国家,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大气与伟岸。
阿房宫既是一种信仰设计和政治表达,更是一次集中的文化展示。所以,它绝不仅仅只是秦代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而完完全全应该是对它的概括,是对于整个秦代最有代表的归结。
阿房 阿房
中国历史上,秦文化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功利实用,满怀开拓和进取精神。他们崇拜规则和秩序,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许,这种文化传统在秦人发迹之前就决定了日后的崛起,同时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但是,这种集权统一的国家结构,从此再也没有改变。
秦国的强国之路在于“变”,以不断的变革应对六国陈腐的不变。在变中求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使秦国紧急提速,驶进了发展的快车道。一国之本在于农,变革后的秦国农业迅速走出了困境,繁荣的农业又支撑着强大的秦军在短短的十年间神速统一了全国。
但是,十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帝国却丢掉了变的传统,学得以不变应万变了,最终又遗憾的走向了瓦解。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呜呼之声,和“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的嗟夫之叹,剥掉了宫墙上的华丽砖瓦,一语道破了帝国惨遭“楚人一炬”的文化败因。
帝国的发展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从开始到终结一般都会经历崛起、承启、鼎盛、延续和衰败五个时期。在最初的征服过程中,亡国的百姓往往因屈服于胜利者的军事威慑,而形成了一种高压下的无奈遵从,也正是获得了这种遵从,胜利者才称得上是实现了真正的统治和占领。统治是一个武力胁迫的过程,百姓在长期的屈从中会逐渐变得麻木,进而也就成为一种日常习惯。习惯产生认同,认同形成自觉,自觉又自发就达到了鼎盛。盛世没有永远,就像宴席不可能不散,一切还会慢慢冷却下来,而冷却过后就又跌落到了平庸。
然而一般大一统的王朝数十代走完的路程,在秦始皇的手中竟然轻而易举的一个人给实现了,从统一到鼎盛仅仅只用了区区二十年。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王朝也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使命,延续和衰败的过程自然也会缩减,只是缩减的速度比他创建的速度快得多,瞬间就走到了终点。
高压尽管能迫使出屈服,但是在屈服中就肯定还会有反抗,只有进入了日常的生活才会在习惯中形成一些秩序,秩序是公众的认同,认同后便有了国民的国家荣誉感。荣誉感是一股聚合的国家凝聚力。
秦王朝只用了二十年就达到了鼎盛,被吞并的六国百姓在秦人的军事高压下屈服后,还没有完全融合进新建的帝国里,他们仍然携带着亡国的屈辱和复仇的怨恨,还没有完成俘虏到国民的转变,对于帝国缺少感情上的牵连,就是有也是曾经的亡国恨,当国民的感情始终与朝廷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形成一个以国家为号召的凝聚力。
国家是用边界围起来的政治实体,国家的凝聚力就是一种有向心力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能够让它的国民在内心深处怀有我是某国人的认同感。对于国家的这种认同能够产生稳固的归属感,有了归属感的国民才有国家的概念。
真正的大国是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意识形态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秦国统一后,老百姓没有分享到做大做强的成果,生活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当老百姓得不到发展的红利和强大的实惠的时候,什么样的制裁也不能杜绝对残暴统治的仇视。秦朝初建15年即土崩瓦解,虽有诸多原因可以追问,但更重要的是扩张和征服的速度太快,国家认同的意识没有及时地跟上。
在西安西郊阿房一路的西头,有一处孤独的高台土冢,当地人叫它“天台”,是阿房宫中的一个附属建筑遗址。土冢被绿化保护后用砖墙围了起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浓缩的疆土。曾经横刀立马一统天下的帝国,破败的没留下任何廊腰缦回中的丁点屋角。那种摧枯拉朽式的结构性坍台,揭示了他们突然陨灭的政治性败因。
政治的极端化促成了军事的速成,而军事的速成又导致了经济的过度膨胀和文化的早熟。国家的财政需求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高赋税对百姓正常生活造成的压力。百姓无法感受到大国的福利,承受的只是灭国的屈辱。
商鞅推崇的是“以法治国”,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刑不上大夫”意识的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尝试了一种国家管理的法制化模式。在这种模式的管理中,激发了民众的创造热情,直接催生了大秦帝国的出现。但是,后来的韩非在继承了商鞅的法制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着重强调了“以法”的方式,使之成为了一种政治谋略。“以法治国”不同于我们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是依靠,有遵从的意思,法律是高悬的明镜,是指导。“以”是凭借,有使用的意思,法律是手中的棍棒,是工具。“依法治国”指的是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治国”指的是借用法律行事,其目的是保障始皇的集权统治。他们的思想都只强调了法律的惩处作用,忽视了它的指引,尤其是保护作用,使老百姓都成了法律的对立面。加上一味的严刑峻法,老百姓体会不到国家对于黎民的关怀,对于国家的憎恨也就与日俱增。
国家的强大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了,老百姓也就没有由此而生的自豪和荣耀。在这种大而无爱的国家里,难以让人获得幸福的感受。没有了仁爱的社会,横行的是浮躁、功利与教条。秦国过度的追求严刑峻法,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十年战争以及随后的征服南方战役,北击匈奴等战事耗尽了秦国几百年的积蓄,被征发后剩余的男子努力耕种也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女子不停地纺织也不能得到足够的布匹,孤寡老弱都无法生存下去。当生存也成了问题时,为国效力的尚武精神便消失殆尽了。一统天下后,秦帝国实际上是危机四伏,在强有力的始皇帝健在时还能起到威服的作用,一旦秦国失去了始皇帝,外强中干的秦国土崩瓦解命运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秦始皇将秦帝国带到了辉煌的顶峰。但是,他超越了时代的野心也耗尽了帝国的国力。无论如何,再怎么善战的军团,它的命运也是紧紧依附在它的国家之上的。在秦军最后的日子里,帝国的秩序已经崩溃。当士兵在前方拼杀时,他们的家已经无人来养,覆灭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一旦人心动摇,荣耀与未来就将同归于尽。
西安城郊外的荒野里,一处年年聚集着70万劳役的工地上,密实的夯土层如同秦人的智慧浓度一般,曾经耸立着帝国五百多年的功业。2000年过去了,建立在它上面的阿房宫都已变成了黄土堆,帝国的军队也躲避到了东面30公里外的地下,成为了长期潜伏的陶俑。秦帝国的横空出世和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的命运,似乎是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主宰,这个深藏不露的力量轻易地就戏弄了那支曾经骁勇无比的军团。
虽然项羽推翻了秦国的政权,但却无法推翻那个时代建造的大国框架。虽然他烧毁了秦国的宫室,但却无法烧毁始皇构建的帝国大厦。当阿房宫经历了三月不灭的大火被彻底地焚毁后,那些攻取了咸阳的胜利者们却发现,他们已经没有了转身回头的路。文化的整合让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