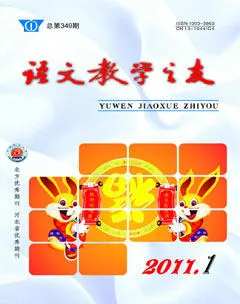误判一句 冤案无数
199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曾把下面这个句子判定为病句:
由于改编者没有很好地理解原作的精髓,任凭主观想象,加入了许多不恰当的情节,反而大大地减弱了原作的思想性。
权威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对于这例句子也持同样的主张。它们都认为最后一句不合逻辑,关联词语“反而”要改为“因而”。
笔者认为此句不是病句。从实践层面,我们不妨对该句作一些补充:“由于改编者没有很好地理解原作的精髓,任凭主观想象,加入了许多不恰当的情节,(不仅没能增强原作的思想性,)反而大大地减弱了原作的思想性。”补充后,一看便知这是一个无误的句子。
通过原句和修改句的比较,我们发现原句只是语意跳跃、不够连贯而已。从理论层面讲,即便原句有欠缺,那也只是修辞问题,属语言表达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语法问题,即语言表达对不对的问题。吕叔湘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高考试题不只具有决定性的评价和选拔功能,还具有潜伏性的导向与辐射价值。误判上述句子,那么出自曾经使用过的、正在使用着的中学课本中与之类似的许多省略句,都将视为病句。譬如下面各句(其实这些句子原本都没有语法毛病,只要补充上括号里的内容,修辞上的连贯也不成问题):
1.搞得太烦琐,(本想说清楚的,)反而不容易说清楚。(季羡林《成功》)
2.而对健康过于注意的人,又常常会造成精神上的负担,老是疑心自己有病,结果(不但不利于健康,)反而把身体搞坏了。(杨述《恰到好处》)
3.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不但不向远处逃走,)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社戏》)
4.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那时的手红活圆实,现在)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鲁迅《社戏》)
5.我实在没有勇气重新回头去找那只丢失了的鞋子,(我意识到自己终究要回家,)可我也不敢回家。(张洁《挖荠菜》)
6.我爱月夜,(因为月夜很亮;星天虽然不亮,)但我也爱星天。(巴金《繁星》)
如果从上述高考试题的评价标准看,例1至例6都是转折有误、关联词语使用不当的病句,尤其是例1和例2跟1997年高考试卷上的句子惊人地相似。
7.那时既无大队骆驼带了大量清水食品跟上来,(也无人力车送来补给,)更谈不到汽车飞机来支援。(竺可桢《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8.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即使用功了,)有时也很任性。(鲁迅《藤野先生》)
9.恒星有各种各样,(它们表面的温度也应该千差万别,)但是全都是灼热的庞大的气体球,全都是发光发热的。(郑文光《宇宙里有些什么》)
如果依据以上高考试题的尺度,例7至例9也是逻辑有误的病句。
我们以为,例1到例9即使退后一步不加补充,也不能就一定说修辞有毛病。细究这些句子之所以省略,有的是因为思维跳跃,有的是因为话语抢白,有时源于对话的双方心照不宣,有时源于说话的一方闪烁其辞……不一而足,这才是“活”的语言,实际运用中的原生态语言,而无懈可击中有太多的人为雕琢。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荒谬结论:越是那些平时对课文阅读扎实、语感出色、表达灵活、语文素养出众的考生,高考中越会远离此类高考试题的荒唐答案,越会遭遇滑铁卢。所以高考试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肩上有几乎无法承受的信度之重。
(作者单位:洪泽县高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