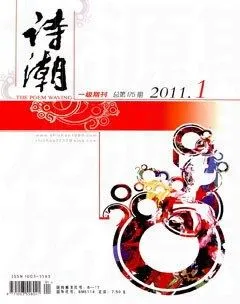爱的祭奠
爱先于生命/后于,死亡/是创造的起点/世界的原型。——(美)狄金森
普拉斯的《情书》写给情人特德·休斯,莫如说是写给自己,它厘清了自认识了休斯后感情的巨大变化,读来不能释卷。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剑桥求学时,结识了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对于她,自遭遇了这场爱情就身不由己。之前,她对于感情“像石头一样”,“像沉睡在黑岩中的一条蛇”,即使天使为她“迟钝的性格落泪”也没有用;她继续沉睡,“像一根弯曲的手指”。渐渐地有了朦胧的爱情之感,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一边是“封锁着的水滴”在“露珠中升起”,一边是内心依然是“坚实无比的石头”。但在“一眼认出了你”——见到了休斯后,蛰伏的爱情惊醒了,“我闪闪发光,一身云母的鳞片,伸展开来/然后将自己液体般倾倒”——这是情爱奇异的力量!继而写爱的进一步苏醒,沉睡如“一根弯曲的手指”,此时“渐渐透明,像玻璃”;竟“开始像三月的嫩枝一样抽芽”,“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此处的互文性,除凸显出了更为宽广的阅读语境,还给人以纯美而动人的想象;女诗人又“从石头向云彩,我就这样升起”。诗中这个前后一以贯之的“石头”,化为“云彩”般轻盈,无疑是爱情的奇迹——此刻,灵魂飞升,像天神;像方形的冰那样纯净。
《情诗》一诗写得极为细腻、委婉,“石头”“一条蛇”等意象平行、交叉的变化,既陌生而又令人莫测。
“如果我现在活着,那时我已死去”。爱情的疯狂给普拉斯带来了幸福的巅峰之感。
但在读《十月的罂粟》时,竟像一句谶语。
《十月的罂粟》写普拉斯追忆吸煤气自杀急救送往医院,濒临死亡一刹那所见的幻象与体验,极为绮丽——亦如题目所示:“十月的罂粟”。
这个死亡的意象,为她所独创。抑或她用自杀来获得缪斯一次心灵的补偿。
“云想衣裳花想容”,死亡之美,亦如十月盛开的罂粟;它的美如女人的衣裙,光彩照人,而非阳光里的云层所能制成;美的绝望也绝非红色的心盛开沁人魂魄的惊异;它是礼物,莫如是爱情的信物——芬芳、妖艳,夺人心魄;炽烈,也似地狱般让人疯狂。它是冷酷人间黎明时,迟迟张开喊叫的嘴,绝望窒息之后的一次挣扎,那是她怎样的一种痛苦?
“十月的罂粟”,其意象嬗变为衣裙、红色的心、礼物、喊叫的嘴等,一种充满动态的永远无法完成的进行时,显然普拉斯以“十月的罂粟”自诩,与之合二为一;抑或于在似与不似之间,仿佛是她想象力饕餮的盛宴。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三次自杀。她的这种极端性的行为,除了生理的因素外,还有作为诗人精神上对死亡之美体验、之匪夷所思的无休止的渴望,令世人惊异不已!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2月11日,普拉斯在她生日的那天,她打开煤气,终于如愿以偿。她的这次自杀与婚姻的破灭、丈夫特德·休斯移情别恋有关。
对一个女人来说,爱是她的一切。
《情书》与《十月的罂粟》读来,感觉是那么迥异不同,其反差于内心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而不能平静。前者渐次透明,纯净,轻盈,飞升抵达爱的殿堂时的无限憧憬;后者则色彩强烈。弥漫着死亡的幻象与绝望的痛苦——“在矢车菊催开的黎明中/迟迟张开喊叫着的嘴。”把“艺术与疯狂糅合在一起”, “自杀悲剧和作品把生活与艺术卷入妇女挑战的无可辩驳的戏剧性姿态”,普拉斯以死亡的方式向社会提出抗议和反叛,使她成为当代世界诗坛一颗最璀璨的星星之一。
这两首非凡的诗与其是她的传奇,莫若是对爱沉重的祭奠——
“如果我现在活着,那时我已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