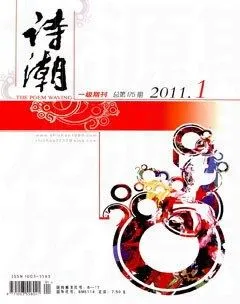谈诗片段(二章)
诗人要有自己的精神背景……
没有自己精神背景的诗人很难成为重要的诗人。
“精神背景”可以是很具体的诗人的思想和人格范型,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精神原型,总之它具有某种“源头”或“母体”的属性。寻找或拥有它,应该是所有“自觉”写作的开始,也是所有自觉写作的归宿,是它力量的源泉,也是它意义获得扩展的一个基础。当然,源头不必只有一个,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大诗人的精神背景可以说至为复杂,屈子、子建、陶潜、谢脁可以说都构成了李白的精神营养,是他诗歌源头的众多溪流。
艾略特有个“传统和个人才能”的说法。他说,“任何诗人都不能单独地具有完全的意义。”一个写作者的意义无法靠他自己独自建立,而必须是靠他和传统之间的一种关系来建立的。所有的经典作品已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谱系,一个秩序,而每一个新的文本的出现,都与原来的谱系和秩序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你所提供的和前人相比,究竟改变了多少?是重复的还是新鲜的不一样的经验?
历史上西方文学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都和过去的文学之间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互文”或重复关系。古希腊的神话和《圣经·旧约》构成了西方文学的大量“母题”。荣格正是据此提出了他的“原型”说,认为在任何创作里,都有“集体无意识”的呈现。写作者自己当然不一定“意识到”,但他会和前人的写作有一种不自觉的、深刻的“重复”,这种重复并非属于多余,因为一个写作者“文化属性”的获得,必然是在与传统理念与精神母体的“隶属”或对话的关系中实现的。中国古代的诗人,除了总有精神的传承以外,还喜欢“用典”,用典其实就是寻找个体的经验与传统的经验之间的联系,以使自己的感受汇入到古老的知识谱系之中,目前入业已成为经典的说法与经验达成一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互文”和对话的方式。
好的诗人既有自己的精神源头,同时又构成了后来者的精神传统。这正像普希金受到英国文学、特别是拜伦的影响,同时又构成了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精神源头一样,像鲁迅接受了西方19世纪“摩罗诗人”的精神营养,又构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典型的精神肖像一样。
一个人常常会意识到他个体的无力,个体作为一个c7efbc66f1faaac3c7b5fd850b9c645c抒情者,他的力量源泉从哪里来?他的某种神圣的合法性从哪儿来?很难靠一个单个和孤独的个体来建立。然而一旦他与某个关键性的精神传统或背景建立起对话关系,那就不一样了。这种例子有很多,海子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的重要,但他是引凡·高和荷尔德林为精神知己和先驱的,它称凡·高为“瘦哥哥”,这种说法在那时或许被认为是“矫情”,或是有说不出的某种别扭,但事后我们再想,就显得非常自然——那几乎就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的语言与思维方式是那样的一致,虽然一个是使用了伟大的汉语,一个则是使用了线条和色彩,但他们所表达的对世界和对生命的理解,却是殊途而同归的。还有荷尔德林,海子一生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那时这位德国诗人在中国还很少有作品被翻译,更少有知音,而海子在读了他有限的作品之后,便“永远地爱上了”他的人和诗。“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说得多好啊,这场烈火最终也将他吞噬,并且将他永恒地照耀。
“有两类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凡·高和荷尔德林就是后一类诗人……”海子也是这样的诗人,凡·高和荷尔德林的人生与艺术,强化了他对存在、世界与生命的理解,使他“超出了第一类狭窄的抒情诗人的队伍”。
也还有更靠近的例子,王家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写作了大量的诗歌,但直到90年代初期他才真正产生出广泛的影响,为什么?是这个年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使他凸显出了意义,当他写出了《瓦雷金诺叙事曲》之后,他就不再是一个“狭窄的抒情诗人”,而是通过一位苏俄诗人的命运遭际,照见了一个中国诗人的精神处境。“蜡烛在燃烧,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这冬天和蜡烛,隐喻了他自己精神上的寒冷与忧愤。“整个俄罗斯疲倦了,又一场暴风雪止息于它的笔尖下,静静的夜,谁会在此时醒着,谁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他是在说俄罗斯,是在说帕斯捷尔纳克,但没有一句不是在说中国的现实,是在说他自己。“也许你是幸福的,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松木桌子留了下来,这就够了。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这样富有时代感的书写,富有悲剧力量的书写,因为一面遥远的镜子而变得清晰和容易起来,也变得坚硬和艰难起来。
“你省下的粮食还在发酵,这是我必须喝下的酒,你省下的灯油还在叹息。这是我必须熬过的夜……”这是另一位中国诗人的诗句,寒烟的《遗产——给茨维塔耶娃》中的句子。某个时期生活的困顿,以及精神的某种艰难处境,使她想到了这位早期苏联时代备受磨难的诗人,并且建立起她们之间精神与命运的相似性:“你测量过的深渊我还在测量,你乌云的里程又在等待我的喘息,苦难,一笔继承不完的遗产,引我走向你……”一个诗人也许会有自己的小苦难,一个当代中国的诗人,你可以设想她所承受的一切并无惊世骇俗的地方,但是她们之间仍然可以有人格的纽带与感人的桥梁:“看着你的照片,我哭了,我与我的老年在镜中相逢”。她已下决心要拥有一个那样的人生,一直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她要用一生去关怀那巨大的精神和伦理,并决心成为和她一样被后人追思和赞美的诗人——
“莫非你某个眼神的暗示,白发像一场火灾在我的头上蔓延……”
这就是可以称得上不朽的句子了,两个灵魂之间不只发生了精神的对话,甚至肉体也发生了一种完美的融合,她全身心地扑向那伟大灵魂的能力和冲动,让我赞佩不已。
中国诗人的身份与写作
一个敏感的问题。有太多关于身份的角度可供思考。
有时候,身份会奇怪地缠绕在诗歌中,屈原的诗中显然有一个试图拯救国家而不能的“上大夫”的身份,但归根结底,这个身份又转换成了诗人,一个“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全身披满鲜花和香草的、失意的男人,一个近似于精神失常的、对周同的人都不信任的自恋自艾的人。李白和杜甫也都曾有小得意的时候,拂面的春风溢于言表,但最终他们都确立了自己在诗歌中的角色:一个边缘的、潦倒和喜欢自由的人,或者一个在失意中仍然顾念家国、心怀天下的人,一个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这样说看起来有点矛盾,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智慧,他们建造了一个“儒道互补”进退有据的文化结构,这个结构赋予了他们两种权利自由往来转换的便利。
中国现代诗人的身份就面临了许多难解的问题:当他还是自由之身的时候,他的叫喊或者抒情都是有依据的,像《女神》时期的郭沫若,那时他几乎是一个创造的精灵。但稍后当他进入了体制,成为一个身份奇怪的人之后,他的写作也便失去了自由,创造力变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低迷。上世纪40年代初曾创造和抵达了新诗诞生以来的某个高度的冯至,在1949年以后,也只能写《韩波砍柴》那样的顺口溜了;艾青也一样,只能写《藏枪记》那样的快板书。从30年代的《太阳》《我爱这土地》到《国旗》和《春姑娘》之类,艾青的变化也令人难以理喻。至于到1980年朦胧诗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也以“叫人读不懂的诗起码不是好事”为逻辑给予了批评和否定。可是当我们略加比较便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一首所谓的“朦胧诗”在阅读的难度上能够达到艾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写作水准,但为什么艾青会声称它们是让人“读不懂”的诗呢?
身份问题还在持续地起作用。1987年之后,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们,除了舒婷以外大都远走他乡,但我们有一个疑问:北岛和杨炼,他们成为了何种身份的诗人?是“好的诗人”呢,还是只是“流亡诗人”?如果去掉身份政治的符号,他们还剩下多少诗歌的分量?顾城为什么会自杀?除了自身的性格与精神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个身份的困顿?我认为是有的。他在国内时曾产生过由虚构的外部压力和读者事实上的万千宠爱所带来的巨大幻觉,这种幻觉在他出国很久以后还在起作用。因此,他一直还过着一种延续下来的“精神撒娇”的日子,这种精神撒娇所凭据的很大程度上是原先国内的身份和语境。当他一直不肯更改自己的角色和心境的时候,只能变得越来越失衡、虚浮和暴躁。他的悲剧从总体上看,应该不无这层关系。
还有,一直备受读者爱戴和喜欢的舒婷,1987年之后也差不多终止了诗歌写作,渐渐变身为一个“散文作家”。这也甚为奇怪,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的意志得以回复之后,在冰消雪融和特定象征的“秘密话语”失效之后,还能否保持写作的心境,这是个问题。事实上,舒婷正是在这样一个检验面前发生了迟疑和犹豫,如果不能使用原来的一套由“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组成的话语,那么写作的激情和必要性是否还能够持续存在?表面上看,舒婷是把“童话诗人”这个身份赠与了顾城,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她和顾城所使用的象征语码,乃是同一种系统。很显然,选择和调整话语方式就是重新选择写作的身份,由一个反抗者的角色到一个常态的言说角色,也意味着必须由隐秘话语的持有者,转化为常态话语的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诗意的存续面临着考验,舒婷终于在危机面前停下了脚步。
比较幸运的也许是所谓“第三代”。他们大多数出道时所喊的口号就是比较“低调”的,是声称“破坏”和相对粗鄙的一群,所以,他们一直不存在身份的落差。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压力下,他们又像其所“Pass”的前辈一样,成为了体验意义上的坚守者和道德精神的化身,成为了“劈木柴准备过冬的人” (王家新诗句)。尽管这个短暂的冬天也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压力,但却在长远帮助了他们,让他们的文本和诗人身份意外地很快通过“出口转内销”的通道而经典化了,他们的形象忽然变得高大和神秘起来。不过在这之后,在社会环境再次发生转换——渐渐由一元政治社会过渡到二元的市场时代——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眷恋于自己90年代初期的异端身份呢,还是要在网络时代的象乱中适时予以更替,完成日常生活的过渡,恐怕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盘峰论争”事件的发生背景,正是这样一个身份困境的反映,一个身份分化和转型的信号。
2007年的一次汉学会议上,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无意中流露了一个说法:当他在否定和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小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现场的几位中国诗人,他改口说,不过中国的诗歌是好的。“但是”,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已经是‘外国文学’了——不,是‘国际文学’的一部分了”。他意识到自己也许说的不够得体,把“外国文学”改成了“国际文学”,因为“国际文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学”的同义语。但这个话语中不经意间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当代诗人的国际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被标定和改换身份为代价的,尽管这种情况在前苏联也有过,但不会像顾彬教授说的这样过分。因为他的话逻辑上也可以反过来:正因为中国的诗人是“国际化”了的,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好的”。这当然也没有错,中国的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国际化呢?但前提是,如果他单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能不能说是一个好的诗人呢?如果只是因为“中国的诗人”已经成为了“国际的诗人”而得到比较好的评价,那么我认为这个评价仍然有着不够真实的成分。因为说到底,西方的人民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文学,而中国的人民也不太需要自己的诗人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他们需要的是言说当下的自己,他们需要用汉语书写自己的现实经验的诗人。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诗人必须首先真正甘于做本色的“本土诗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