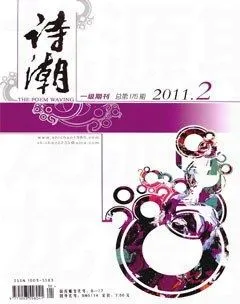乡愁时代
出生地
生我的那个小县城
叫合水县从来就没有什么水
坐落在一个驴脊梁窄的黄土残塬上
远远望去 一县之长
好像和满县城的老少男女
骑着一头瘦毛驴
生我的那个老镇子叫西华池镇
就在县城内 所谓的华池
其实只是几个常年底朝天的旱涝坝
积一点水都让涝坝自己喝完啦
坝底只剩下几只渴死的麻雀
和一些口干舌燥的青蛙
生我的那个穷村子叫闫家坬
一个没水的坬字不吉利
连年大旱以后
就改成带三点水的洼字
即使地上落下三个铜钱大的雨点
也是归十几户姓闫的人所有
生我的那个破院子
有三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黄土越干旱越坚硬 那年大地震
一孔窑洞顶上咔嚓一声闪开条口子
给窑里的人看了看天上的一颗星星
又马上合住窑洞还是那个窑洞
生我的那个苦女人
叫贾秀琴 已是八个孩子的小脚母亲
一生守在甘肃省合水县西华池镇上
像一盏灯 照亮闫家堀村的一孔窑洞
于1963年2月2日的后半夜 将我
从她苦难的身体里放生
在黑暗里
我 打火机 蜡烛
三个重逢在停电之后的黑暗里
我打开打火机的记忆
打火机打开蜡烛的记忆
而且 在自己打开的光明里
我又想起那些简朴的火柴
想起那些如豆的煤油灯
甚至想起远古钻木取火的石头
和木头 以及那些取火的先人
被火光照亮的面孔
我甚至想起那些天外的星星
为人间一直守候在苍茫的夜空
我还想起大地上的那些萤火虫
始终自己为自己带着光明
我总是在失去光明之后
想起那些火的种子存放在哪里
我不能在光明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却能在黑暗中掌握自己的光明
而且 那些深藏在黑暗里的光明
只有在黑暗里才会被彻底想起
然后被豁然打开
明月一轮
对面一栋正在拔高的楼上
升起了一轮月亮 它宁静
但却勾魂
虽然那只是大楼为自己
点亮的一盏巨大的照明灯
但它出现在没有月亮的夜里
充分照亮了我的夜空
一盏明灯
有一个月亮的颜容
还有一颗月亮的心
它不但占居了月亮在天空的位置
还占居了月亮在我心里的天空
一轮不移动的月亮
一轮不残缺的月亮
在一轮移动的月亮离开之后
在一轮残缺的月亮回来之前
升起在该自己升起的时候
升起在该自己升起的地方
一生一世的幸福源于一轮明月
更源于一盏明灯被当作明月一轮
美满当空
城里的鸡叫
一只鸡突然叫了
黎明时分 从来没有鸡叫的城里
几声嘹亮的鸡叫
把我从睡梦里唤醒
在一个很压抑的城里
不要说是一只鸡 即使是一个人
平时也是很难放开嗓子
吼叫一声的
而且 城里人不相信
一只鸡会天天为别人操心
城里人每天的时间
都是由一种叫钟表的时光机器
一分一秒制造的
一只久居城里的鸡
可能错把城市当成了乡村
突然看见天边的鱼肚白之后
就情不自禁喊出了声
不过 这只雄鸡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里
可能只叫醒了我一个人
几声酷似乡下的鸡叫
在一个让我失魂落魄的地方
没叫我的名字 就把我的魂儿
从身外叫了回来
想起老鼠兄弟
那时 我的一点儿灯光
总是忘不了把墙角的一个老鼠洞照亮
我住在一孔窑洞里
老鼠住在我的窑洞里的一孔窑洞里
大窑洞护着小窑洞
老鼠夜夜翻我的柜子
夜夜拿我的玉米和麦子
和我好像是一家人
而我 年年过年
都要给窗口贴一张老鼠嫁女的红剪纸
巴结老鼠兄弟
那时 闲来无事
我会躬下身子朝老鼠洞问一声——
里面有人吗
现在家里因没有老鼠而清静了许多
但心里却好像缺了点什么
月光下的雪地
雪花盖下来
月光也盖下来
里面厚厚的一层雪花
外面薄薄的一层月光
莫非是在谁的梦里
谁拥着雪花和月光进入梦乡
今夜 一个我来了
没想到我的黑影也在身后跟来了
我的脚踩坏了谁的许多雪花不说
我的黑影还遮黑了谁的许多月光
一个我的贸然到来
破坏了谁个在这里营造的一切
我给一块没有一丝儿尘埃的天地
带来了人世间一些不纯的动机
今夜 我只能和那些树一样
原地不动 把自己身后的黑影
从谁的月光上 从谁的雪花上
一寸一寸给人家移走
而且 在这里
这一个我还必须独自把自己
干干净净忘记
在家里拾到一根针
一根针
与我针锋相对
一个针尖大的线索
让我想到许多我过去的事情
这根针 曾给我缝过几个补丁
几次挑亮过一盏快灭的煤油灯
这根针 还曾多次故意把我刺疼
一针见血
在生活的大海里捞针
有时也只是让我弯一弯腰的过程
犹如在家里偶拾
遗失在苍茫里的一首小诗
月光像剑一样进来
门缝迈进来一把剑
那是一束月光
一把剑环视了一遍四壁
看见了一把裸露的刀子
其实 刀子一直在期待
月光像剑一样进来
一束月光在刀子里找到了月光
而锋芒等来了锋芒
怀旧
一个人 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会像我这样蓦然回首往后看
走到尽头 一个人
依依不舍的都是舍去的那些时间
一个人 终了最想去的地方
其实就在自己美好的从前
只有即将腐朽 一个人
生命里才会像我这样出现闪电
我听见了一条大河
一条大河深夜穿城而过
把我惊醒
我听见的是一条大河沉重的脚步声
在干涸的荒原上
一条大河为什么远远奔来又擦肩而去
被我听见的大河也许只是偶然经过
天下的河都是要走到一个地方去的
一条大河一路寻着河的足迹
猫吃糖瓜子儿的声音
夜深人静
楼上 我的头顶
经常会传来一阵一阵的咯吱声
小时大人们对我们说
成为大人后我们又对孩子们说
那是猫吃糖瓜子儿的声音
其实 那是床的呻吟
或者是灵与肉在床上的动静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当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而作为一个正常的独身男人
我当然要屏住呼吸
倾听它咯吱的过程
一只蹑手蹑脚的猫
好像捉住了一粒很大的糖瓜子儿
声音急促地咯吱着
我住一楼 咯吱好像就在二楼
但咯吱了一会儿就走了
好像不在本单元的二楼
而是在另一个单元的三楼
而且一会儿在四楼一会儿在五楼
一会儿又在本单元的六楼
或者七楼或者八楼或者九楼
其实整个楼上不只是一个咯吱
而是有许多个咯吱
是许多只饥饿的夜猫子
在咯吱咯吱吃糖瓜子儿
此刻 最底层的我
意外地成了一个有滋有味的人
遭受着数层幸福的压迫
浑身被别人的爱滋润
幸福满心
今夜 我的夜空
又传来猫吃糖瓜子儿的声音
忘情的呻吟 犹如天籁
那是怎样的一些馋猫呢
嘴里叼着怎样甜的糖瓜子儿
让我也情不自禁
孩子似的兴奋
回家
上路之后
我先是幸福地想起那头小猪
那头丢失了三天的可爱的小猪
自己是怎样哼哼着拱开了家门
欢天喜地和一大家子人重逢
接着我又慢慢幸福地想起
那头丢失了整整三个月的毛驴
又是怎样风尘仆仆自己寻到家的
三个月 给一个人要走多少里路啊
三个月 给一个人要经多少件事啊
但一头倔犟的毛驴
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回家了
那头毛驴好像受了很多的委屈
那头饥肠辘辘的毛驴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当院里耍脾气
使劲踩下一个蹄印子
好像是说 到死我都是这个家里
一头吃苦受累的驴子最后
那头毛驴自己到槽里大吃了一顿
卧倒一觉睡了七天七夜 我当然
还记得那只被送到远方的大黑狗
又是怎样在三年之中跋山涉水
独自流浪着奇迹般回家 那天黄昏
那只忠实的大黑狗先是汪的一声
突然把一大家子人吓了一大跳
然后就不停地摇着尾巴低声呜咽着
把一大家子人一个一个感动
而让我羞愧的是 一个人离家三十年
居然一直不知道回家
连个畜牲都不如
大厦的出身
我了解那座摩天大厦的身世
可以说 我是看着那座大厦出生
和一天一天长大的 那个地方
原来什么东西也没有一片荒凉
先是一台埋头苦干的挖土机
不停地从那个地方往外挖黄土
当那里挖出一个大大的深坑
又出现一台脚踏实地的打夯机
跟着挖土机往深坑里填黄土
直到无数钢筋水泥在黄土里扎根
那里又出现一架壮志凌云的吊车
一层一层使劲把大厦吊上了天空
其实大家都看见了
就是挖土机打夯机和吊车
这三个吃苦力的铁家伙
合伙扶起了那座大厦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挖土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打夯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吊车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而挖土机特像进城打工的三叔
打夯机特像进城打工的二叔
吊车特像进城打工的父亲
三个亲兄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所以 那座漂亮的摩天大厦
是农民出身 即使在城里拔地而起
归根结底是一个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