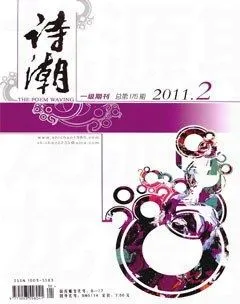关于现代诗韵律问题之思考
新诗已经走过将近一个世纪。不可否认,新诗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新途径,留下许多可圈可点的好作品。不过,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华民族诗歌史长河中,新诗显然不如唐诗、宋词、元曲那样奇峰崛起,引人瞩目,还需进行不懈的开拓。其中,如何建构新诗的韵律问题,是当下诗歌创作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由此使新诗在不断探索诗意内涵的同时,也注重诗性本体的坚守、审美情致的提升、艺术表现力的拓展。
回望五四新诗运动初期,许多有识之士在推崇白话文、坚持“诗体解放”进程中,并没有放弃从传统诗歌中汲取营养,为创造现代诗歌开辟了既有广阔自由空间又有深厚基础的路子。今天,我们重温那一代开拓者的作品时,仍可从中读出他们在开创新诗事业时对诗性本体的坚持和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胡适作于1916年的《蝴蝶》,是第一首以白话文写就的诗歌,由于采用五言八句诗体,读起来朗朗上口。他的《鸽子》:“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虽是白话语言,也蕴含着厚重的古文化浸润。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抒情诗,都有非常明显的节奏感而富有内在张力。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以回旋往复的内在韵律,营造出一种徘徊、彷徨的意境。即使以自由体著称的郭沫若先生,他的《凤凰涅槃》也不乏韵律,如“昂头我问天,/天徒矜高,莫有点知识。/低头我问地,/地已死了,莫有点呼吸。”
在新诗发展史中,一代又一代诗人始终坚持诗性本体写作。上世纪“新月派”诗人,就非常注重诗歌的韵律性。许多追求意象、象征主义的现代派诗人,也没有放弃诗歌的本体意义。张扬现实主义创作的诗人,坚守着诗歌艺术的特质。一直到“朦胧诗”诗人,仍然坚持“纯诗”立场。台湾的现代派诗人,也在对诗歌的本体性进行不倦的探索。
近年来的诗歌创作,虽然好诗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存在着不押韵脚、不讲韵律的现象。这造成了许多诗只能阅读,不能朗读,更谈不上吟咏,随之出现了诗歌欣赏群体越来越少的倾向。有作者说,自己只是写一些分行的文字。这种说法固然有自谦成分,但是,如果真的不讲押韵,甚至连韵律也不考虑,那些“分行的文字”即使含有诗意,最多也只能称为散文诗,或者干脆说是分行的散文。
什么是诗、什么是散文?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界定。先秦时,由于当时文体较少,古人把文分为诗与散文两类。公元六世纪刘勰撰写的著名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逐一研究,把当时的二十种文体归纳为韵文与无韵文两大类别。属于韵文的有诗、乐府、赋、颂赞、铭等,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内在韵律;属于无韵文的有史传、诸子、论说、诏策等,其基本特征是没有韵律。这种分类方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看赋体,赋体属韵文,即便唐人的骈文也有内在韵律,这里摘取王勃《滕王阁序》的一些句子:“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读起来有极强的韵律感,与今天一些诗相比,《滕王阁序》反倒更具诗的特性。
新诗是比较注重向外国诗歌学习的,那么,会不会因为这种学习导致了一些诗歌“失韵”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表面看,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押韵较少,也缺乏明显韵律。然而,这是翻译的原因,并非原诗没有韵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用母语写作的诗歌,几乎都有自己的韵式。传统西洋诗歌就非常重视韵律、韵式,传统英语诗歌的韵律(Metre),或者依据每一音步所包含的音节,或者依据轻重读音而形成。现代外国诗歌也在进行探索,有些诗的韵脚不甚明显,但仍具有内在韵律。这一点与汉语诗歌情况相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汉语韵部较许多外语更为宽泛,可供押韵的词汇更多一些,并且汉语语音具有声、韵、调的特点,便于依托汉语语汇建立起音韵感。诗歌是建立在不同语言、语音之上的文学形式,从严格意义说,诗歌是不可能被准确地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能失去原有的韵律、韵味。尽管如此,我们翻阅上世纪老一代诗歌翻译家介绍过来的外国作品,由于那些翻译家大多是诗人,又具较高的外文素养,那一时期翻译的外国诗歌大都有较为明显的韵律,许多作品还以汉语语音配上了韵。这些翻译家自己创作的诗歌,带有向外国诗歌学习的痕迹,也不失韵脚、韵律这些基本特征。比如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的《大车》,就采用了西洋的商籁体,这里引用前四句作分析:
拖着|一大车|夕阳的|黄金,
骡子|摇摆着|踉跄的|脚步,
穿过|无数的|疏落的|荒林,
无声的|扬起|一大阵|黄土,
从韵律看,以明显节奏的音步强化韵律,而且还有变化;从韵脚看,其第一句、第三句押相同韵,第二句、第四句又押另外的韵,属典型的西洋“双交韵”。其实,类似“双交韵”这种交替押韵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存在。
或许有人说,自由体诗就是要破除一切框框,讲究韵律会过于刻意。不错,自由体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但它毕竟是诗,仍需保持诗体的特质,而且一些好的自由体诗,甚至在韵律方面也在探索。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第一首《忆秦娥》据传为李白所作,这里不去考证作者,着重分析其上阙的韵律:“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种长短句与格律诗绝不相同,在当时就是一种自由体,只是后来模仿者多了才形成固定词牌。这首词有着极强的韵律,从句式看,前三句各有一个三字句,节奏型鲜明,后两句又变成了四字句节奏型,且与第二句中“秦娥梦断”四字句相呼应;从韵脚看,五句四韵,律动感极强,其中第三句“秦楼月”是叠用,形成了音节、韵脚的复沓。现代诗创作也有这样的事例,比如戴望舒的《雨巷》。正因为自由体诗没有模式,才可能探索出新的韵律、韵式。
诗歌审美是建立在诗意内涵与诗性本体结合之上的艺术欣赏。诗歌的本来意义,是蕴含着诗意的有韵的文学形式。今天的诗歌创作应该坚持“加法”而不是“减法”,中国几千年的诗歌传统、世界各国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积累了许许多多艺术精华,可供我们学习、借鉴。前些时候流行的解构主义,把比兴、意境、意象、象征等要素一一从诗歌中消解,甚至连韵律也予抛弃。我们尊重现代诗创作对诗歌形式的突破,可以不那么注重韵脚,但起码也需具有内在的韵律。韵律,是构成诗歌本体的底线,或者说是人们认识诗体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连韵律也解构了,就会模糊诗与散文的区别。或许我们顾及一些主观因素,不便对那些没有韵律的所谓诗歌进行评价;但我们的后人是会作出客观评价的,他们不会再把分行的散文说成是诗。这因为,诗学的本体属性是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