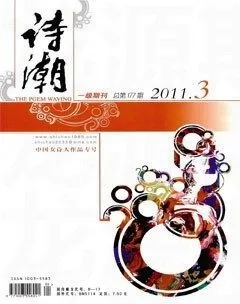前往与返回(组诗)
蓝蓝:
原名胡兰兰,1967年生于山东烟台。做过工人、编辑,现供职于河南省文学院。出版诗集七部,散文集五部,长篇童话和短篇童话集五部。
创作谈:诗歌是语言的意外,但不超出心灵。
复杂的壳里包裹着最单纯的内核。
——我准备好了。……但结果往往不是我预想的那样。
有时,诗人最害怕的是阐释者对诗的解释。
诗歌在诸如“立正、稍息、齐步走”的口令面前,永远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在说“不”。
它所要求的秩序是艺术和美的秩序,而不是别的。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人,他的工作是唤醒在那个时代昏昏欲睡的事物。
事物还是原来的那些事物,但是背景变了,——把它们写出来,原来的事物也不似从前。
不要在作品中说教、讲道理,那样只会使“道理”变得孤立。塞尚的画中几乎很少用轮廓线,他以色彩说话——它的明暗、体积、对比……由色彩构成了事物的重量感、相互的联系,然而它是人对事物综合感觉能力的艺术表达。
面对某些不易理解的诗句,愿我们生着一双清亮的眼睛吧。因为诗人在说:“他们说我晦暗,可我停留于光辉之中。”
阿瓦提
阿瓦提,清澈的水!
在未遇到你之前,我仍不知道
我的双脚常停留在书本的干旱里
那里的犁沟紧闭,头顶没有雨云。
在沙漠和胡杨树之前,我仍不知道
歌声在四壁的纸页里回旋
没有风,也没有落叶的飘动
似乎是一场可怕的诅咒。
阿瓦提不是一个例子,写作的长夜里
一直都有悄悄的叩门声
弦在寻找琴弓,而死在寻找生
笔倘若不知道那么心里的哭声就知道
阿瓦提,对于一个汉族人
你知道。
库布鲁克大峡谷
木卡姆放进汉语的水里就变成了一块玉。
时间秘密的宫殿就在托木尔腋下的峡谷深处。
是丹霞山蹿升的火苗,被冰凉的手
在一瞬间握住。
更远处,最细的一股泉水
仿佛春天的巴扎
卡龙琴格子的暗房洗出了
葱绿的棉花田。
被洪水熄灭的篝火在昨晚曾经燃烧,如陨星
飞坠在美人的怀抱。夏天的温宿!
你烈焰的群山前
站着一个女诗人。
她用笔歌颂自己的同类——
山口两棵胡杨树喂养从沙漠
走过来的旅人,在被干旱烧焦的正午
她们低头亲吻了你的嘴唇。
八瓣梅
裙子褪色,头巾洗白
卷进风的漩涡的引力
一场浓雾里隐匿的灯
在牧歌里开始发电的身体
是外乡人带来了寒冷。她的嘴唇:灰的。
三天,塔尔寺的墙可以下雪了。
高原隆起
揪紧她渐渐弯曲的旋转。
格桑花
八个瓣的石头,会飞的石头
我秘密的爱认出了你
啊,红色的炭块,白色的火焰
燃烧在八月的高原
你是穷人的前额,风的情人
你是一个人的童年深藏在他泪水的晶莹中
我从你对高原的忠诚里
分得了幸福的允诺和低垂的羞赧
恍惚间我记起另一个八月
是谁曾用指着你的手把我点燃
格桑花,你用最小的闪电把我抓住
——由于一个人
那往昔一刻不停地走到今天……
哥特兰岛的黄昏
“啊!一切都完美无缺!”
我在草地坐下,辛酸如脚下的潮水
涌进眼眶。
远处是年迈的波浪,近处是年轻的波浪。
海鸥站在礁石上就像脚下是教堂的尖顶。
当它们在暮色里消失,星星便出现在
我们的头顶。
什么都不缺:
微风,草地,夕阳和大海。
什么都不缺:
和平与富足,宁静和教堂的晚钟。
“完美”即是拒绝。当我震惊于
没有父母、孩子和亲人
没有往常我家楼下杂乱的街道
在身边——这样不洁的幸福
扩大了我视力的阴影……
仿佛是无意的羞辱——
对于你,波罗的海圆满而坚硬的落日
我是个外人,一个来自中国
内心阴郁的陌生人。
哥特兰的黄昏把一切都变成噩梦。
是的,没有比这更寒冷的风景。
在东大寺
东大寺的一角,头戴白帽的
年轻穆斯林在诵经。
他们低沉的声音里,清真寺的圆顶在升起
朝着弯月和星星
他们平静的面容宛如树叶
他们的嗓音宛如西风和北风。
一个有信仰的心灵可以如此安宁
令旅游者的脚步变得胆怯、沉重
就像今天,我坐在电脑前
耳边忽然响起缓慢的诵经声:
东大寺依然在遥远的西宁
下午的阳光照在长廊的圆柱上
并推着一阵风从千里之外赶来
吹凉我发烫的额头……
在台湾东华图书馆楼顶
电梯把他们送到半空,沉甸甸的云
向下按住他们的头顶。
为什么你眩晕,难道被砖瓦下
甘蔗林在风中的起伏颠簸着?
还是你的脚踝踩到多年前芒草白花花的摇曳?
远处是东海岸的山脉,楼房密集
宛如巨大的墓地。你听到野豌豆丛中
黑蛇的窸窸窣窣,更远处有望不见的
外婆那长满瓦松的屋顶。
“总有人试图从这里跳下去。”
俯瞰脚下蝼蚁般的人群
神色忧郁的诗人啊,折断四肢的细碎声响
砸在你视野地平线的尖石上。
大海宛如一道深渊,隔开了人们脸庞上的悲伤
就像你被高高吊起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