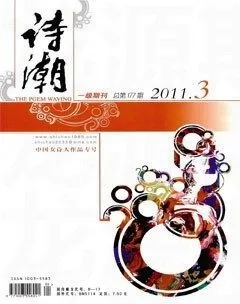奔向远方的铁轨(组诗)
阿毛:
1967年出生。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著有诗集《为水所伤》《至上的星星》《我的时光俪歌》《变奏》,长篇小说集《谁带我回家》,散文集《影像的火车》《石头的激情》,诗文选《旋转的镜面》等。
创作谈:我的生活是被思考、阅读与写作充满的生活。具体到每天,思考占最多时间,一种是因为阅读与写作而产生的思考,另一种就是乱想,无边际的想,诗歌往往就是在这种乱想、无边际的想中产生。一天中,如果我没有写诗,我也必定思考过诗,或者阅读过诗。
诗歌对他人可能是无用的,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很难想象自己没有诗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那一定是物质生活没有情趣,而精神生活萎靡不振,活得没有方向没有指望,现在和未来都暗淡无光。
这是不容置疑的:生命太脆弱而敏感,时间强大而无情。我认为所有个体生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时间。我对时间相当敏感——我对滚滚向前的、强大的东西,总是很敏感——而对脆弱的、善于怀旧的生命,总是心生悲悯。所以,我会有这样的感叹:“让我们受伤的不是彼此,是时间。”会有这样的努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时光中,感受它的流逝。它是如此的强大,而个体的生命却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在时光的河流中跳出好看的浪花。”“跳出好看的浪花”具体到我自己这里,其实就是用写作来保护和拯救脆弱生命的一种努力、对抗时间的一种手段。
流水账记录群像
我把笔下的稿纸
当书桌上的老版日历,
写一页撕一页。
树叶堆积的流水账,
我不公开也罢。
只是我的人生
固执地要以书页
制成的胶片放映。
“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了自己。”
“它不是我的自画像,
而是我们的、你们的——
以模糊的字迹或失真的声音
留痕:
“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幸福或更痛苦,
我们一样的庸常或高贵。”
我首先是个体,
其次才是群体,
最后才是一代人的近处和远方。
在丽岛紫园
光斑在她的脸上闪烁,
她按下快门。
妹妹的天才构图,
稳不住姐姐双手的帕金森。
木芙蓉多么好看啊!
“可怜的人,
一边享受,一边颤抖……”
小桥心疼细高跟
叮当的节奏。
无能为力的光线和花荫,
无可奈何的健忘症!
被典藏的颂诗,被保真的吟咏,
爱杀死了时间!
原谅那用词句
去安慰镜头的人!
我们的紫色
呼应了紫藤园。
改诗
一座被字词镶嵌的宝塔;
一条裹挟时间和石子的河流
和它的两岸。
像风在行进中,使草木起伏,
像步行者做几个欢快的跳跃,
在中途,那顺畅的句子要跳几下。
再或者,剔去多余的比喻,
删除华丽的段落。
运用——,运用……
再或者,这一切都不要,
只要一阵闪电的战栗与滴血的孤独。
因为,风不需要看起来总在吹,
它要一堵围墙使自己转向
或隐藏。
境遇
上午在擦玻璃,购物,安居。
下午在女性主义栖居地。
她们优雅,她们叽叽喳喳。
那个抱膝的女人,
抱着太深的伤口,一言不发。
她望天,
蓝玻璃被白云划裂……
像一把剪刀
像一把剪刀被掰开,
两个人生离。
从相爱的灵魂中间抬起头来,
看孔雀东南飞。
她五里一句,是为了再次
比兴、对韵。
她的徘徊伫望和他的孤单飞行,
像一把剪刀被掰开的上下齿。
除了去绞灵魂这根柔肠,
再无法啮合,去剪生活这块软铁。
她,或者他,
所幸被再婚这个铁匠回收,
回炉,增加或减少铁质,
重新打磨,与另外的上齿或下齿配对。
陌路上的又一把好剪刀,
咬着牙,一路地“咔嚓,咔嚓……”
白领丽人
她从门外进来,
风暴遗留在她的发上、肩上
眼睛和唇上。
后工业时代的
写字楼,人影重叠。
她走过,
一阵带香的轻盈的穿堂风,
有风暴的末梢和书卷味。
她把闹市和琳琅满目的商品
关在门外,面向有待
翻阅的文案。
她坐下时,座椅代替
高跟鞋旋转起来……
这样或那样的支点,
以她们的身份,
来告诫我的文字。
从芦苇丛到咖啡馆
江边的芦苇在学者那里是诗人,
在诗人那里是学者。
此刻它们既思想又诗意:熄掉烟,
不放野火!——多么优雅!
风不吹,它们都相爱:
手牵着手,脑袋偎着脑袋。
波浪般起伏的怀抱,
等同于诗歌的美学。
咖啡馆里,一双感性之手
打开一本理性之书。
火花噼啪起舞,
令坚硬的思想钻石般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