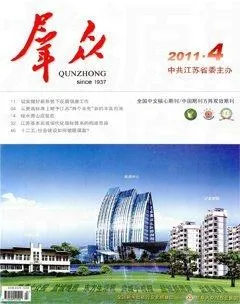企业家的道德信念与精神境界
江苏近代许多企业家为地区性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尤以南通、无锡、常州为典型。
甲午战前,南通与邻地扬州相比,属于江苏比较落后的地区。20世纪20年代,南通已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和江苏省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这种巨大的变化主要归功于张謇的悉心经营和建设的结果。
张謇(1853—1926),字季直,1894年,考中状元。张謇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他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身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
甲午战败,张謇提出了系统的立国自强方案,建议“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在“设厂自救”的社会思潮激励下,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张謇创办的第一个工业企业是大生纱厂。创办大生的目的,据其所述:“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曰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寸心不死,稍有知觉,不忍并蹈于沦胥。”
大生纱厂是张謇进行“实业救国”的物质基础,是江苏近代工业化的嚆矢,是南通近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此后数十年,大生纱厂的命运始终与南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生经营成功后,张謇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和投资活动。’他在通海创办企业,一般说来,具有四个目的:
首先,为了填补南通经济结构中的空白。大生纱厂、大达轮步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南通汽车公司等在南通皆属首创,这些企业的创办,既体现了张謇利不外溢的思想,也有利于南通人民的生计,逐步完善了南通的经济结构。
其次,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一个方面是将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使用同一台传动机可以带动数量较多的机器。张謇在筹创各企业时,充分考虑了各企业之间在原料、火力、产品等方面的相互协作。如广生油厂的原料,就是大生纱厂的下脚料棉子;大隆皂厂的原料又是来自广生油厂的下脚料棉油及废渣;大兴面厂的传动火力是大生纱厂的过剩部分;颐生酿造公司的原料主要是自垦牧公司为改良盐碱地而种植的大麦、高梁,等等。
再次,有利于通海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张謇设立盐恳公司,完全运用绿色手段进行盐碱地改良。他先指导农民在碱地上种植芦苇,待土壤盐分略降后,再种植苜蓿;然后依次种植高梁、番薯等。通过绿色农业,最终把盐碱地改造成高产的棉田,极大地改善了通海乃至苏北的生态。
最后,企业的创办,奠定了南通工业的基本结构。百年来,南通作为苏北一个门类较为齐全、以纺织为龙头的轻工业基地,其基本构架是由张謇一手定立的。可以说,在江苏以至中国,没有哪个城市能像南通那样,一个人的抱负决定了一个城市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命运。
抗战前,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的茂新和福新两大面粉系统及申新棉纺系统为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系统。
荣德生认为发展经济就是为了造福社会。据荣德生自述,他经营的企业,“宛如一家庭”,他写道:“故余以为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慈善机关周恤贫困,尚是消极救济,不如积极办厂兴业。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兴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本人是以事业作为救济。”抗日战争胜利后,荣氏企业复工时,一些无锡人真诚地说:“德生先生又回来了,他的大烟囱冒烟了,我们的小烟囱也可以冒烟了。”
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说:“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贡献。”
常州近代工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刘国钧经营的大成纱厂。大成纱厂系1930年刘国钧接盘大纶久记纱厂更名,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8年中,大成由1个厂扩展到4个,纱机由1万台增加到8万台;资本从50万元增加到400万元。马寅初说:“像大成这样八年增加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刘国钧认为要办好工厂,“必须以工人以主体,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他重视工人的思想动态,经常深入车间找工人和管理人员谈话。他常说:“工厂工厂,乃工人的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工厂。”大成专门花费巨资开办职工食堂、建职工宿舍,举办大成小学、保健站、商店;并造了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工死了可立碑入堂,老年职工死了要开追悼会。另外,大成纱厂还置办大成公墓,等等。
王国维把诗人分为两个境界,“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在企业活动中,我们也把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境界“入乎其内”,就是在企业事务中登堂入室,包括具有向近代工业投资的目光,在日常的操作中精打细算、锱铢必得,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其表现就是处处用金钱来衡量。这一层境界的企业家如同恒河沙数。他们不乏精明,不乏“从人身上赚钱”的观念和手段,而他们也确实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货币资金,但他们仅是为赚钱而赚钱,一味沉缅于金钱物欲中,无法看到更伟大的目标、因而没有更有意义的追求,他们只能“入乎‘金钱’之内”,而不能走出“金钱”的苑囿,不可能到达更高的境界。
第二层境界的企业家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人生情感、道德义务、社会使命的深刻领悟,不是为了单纯的赚钱而赚钱,为了盈利而不择手段。这层境界是一般唯利是图者无法企及的,它是人生气量、道德、涵养、悟性、智慧、知识、经验、信念等量的积累,甚至还有常人不曾经历过的人生磨难的锤炼与催化,从而实现人格的超越,是企业家获得的不逊于物质成就的精神成就。这类人可称为张謇式的企业家。
张謇式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张謇指出:“策中国者,首日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凡天子之忧勤,大臣之所计划,天下士之所攘腕而争,大抵划一矣。……謇不自量,辄亦毅然自任以必成。”张謇式企业家对金钱物欲、对个人利益具有超然精神。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自议创至开机,历时44个月,其间为了筹集股金,往来于上海、南通、海门等地,常常“旅费乏,鬻字”,前后数年的生活费仅靠书院薪俸维持,未挪用厂中一文钱。他半生经营实业,应得酬金何啻百万银元,但他把这些钱全部用于办学等公益事业,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荣德生,常年布衣布鞋,不沾烟酒,一张白纸也舍不得浪费,甚至用香烟壳写便笺。他写道:“国人大多无远大目光,以为余饱暖坐食,终生尽可足用,何必再需若许钱财,不知余别有远见,另图大规模之事业也。”
张謇式的企业家身上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张謇指出:“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他的一些家书再三强调:“当悟人生信用,作事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亦随之矣。”荣德生认为:“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则虽有王阳明,亦复何补哉?”
江苏张謇式的企业巨擘,在企业活动中,既带来了金钱利润等物质上的成就,又获得了人生修养、个性成熟、道德完善等精神方面的成就。这种泱泱气度,赢得人们的普遍敬重。如1922年,-,上海、北京先后举办成功名人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结果以张謇所得票数最高。这种优良的形象、高尚的人格、完美的精神境界,仅就企业需要而言,比物质设备、经营知识更重要,因为物质设备可以购买,知识人才可聘请,而企业家积累的精神成就则是花费巨资也无从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