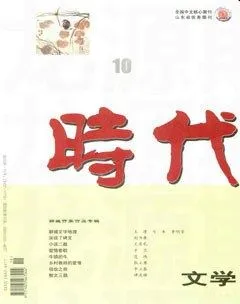浅谈绘画创作中的无意识倾向
任何艺术创作中都有无意识的参与。有的艺术家充分发挥无意识的作用,凭借无意识进行创作,“灵感”所至“即兴”而出。无意识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奇喜使我们深醉其中,对于关注甚少、了解甚微的艺术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领域是否盲从,已是艺术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审美主体来说,绘画中的无意识元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使观者不能直解其意,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怎肯不视。因此,更明确的了解无意识心理学在绘画中乃至艺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极其必要的。也正因为无意识在深度意识领域的重要参与和突出表现,才使得我们不能对其无动于衷。
意识和无意识属心理方面,清楚地说是人脑左右脑客观存在的原因。意识指人在思维清晰能动的行为反应。无意识属右脑,是人潜意识部分,是人思维模糊,无自我状态下本能的行为反应,能够产生特异现象。意识表现绘画比较约束拘谨,是控制的去表现对象,较为理性;而无意识相对意识来说,则比较自由和感性。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因此,也就有如此丰富的绘画作品。针对人心理的意识和无意识来联系绘画,去认识心理绘画。
“当代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实验证明,生物体内特别是人体内在一定的刺激下,能够本能地无意识地分泌出大量的情感激素。”[1]对于绘画工作者来说,它是创作的激情和其它各种情感所以产生的生理基础和条件。实验证明为我们提出意识绘画中存在无意识倾向提供生理依据。在绘画思维过程中,生理机能调动起无意识的积极活动,表现出或喜悦,或悲伤,或激愤等情感。绘画者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在各种艺术认识的激发下产生创作灵感。绘画者受外界的种种刺激,过分喜悦,过分愤怒,过分紧张都会引起神经元过分膨胀和情感激素过量,容易影响对事物的刻画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无意识激发下所出现的情感激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感,是绘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别林斯基说:“如果一个诗人决心从事创作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一股伟大的力量,一股不可克服的情欲在推动着他,驱策着他去做这件事。”[2]这是在意识控制下的强烈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忠实可信的指南,首先是他的本能,朦胧的,不自觉的感觉,那是常常构成天才本能的全部力量,这种构成天才本性的“本能”和“朦胧的不自觉的感觉”实际上指的就是长期创作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无意识,可见在创作任何绘画作品的过程中,没有无意识的参与与倾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触景生情,随情成章”,这是经过长期训练的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共有的即兴应变的能力,在即兴创作中,能随机之巧,意境之妙,应变之奇,令欣赏者称奇、钦佩并得到足够审美享受。绘画最核心的奥秘是生动地表现作者某种独特的情致的境地,一个画家的创作才能和技巧只有发展到无意识的表现其独特的情致的,才能创作出韵味无穷,别具一格的艺术佳作。
在绘画创作中无意识倾向显得格外自由,在一般情况下,有意识的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本来就可以获得自由。而绘画者有意识的把握绘画思维和绘画创作的规律,发展到无意识的把握规律,即达到随心所欲,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无意识境地,当然就进入了很自由的境界了。不仅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到轻松自由,观看者亦能从他的作品中品读出这种轻松与自由。“一旦我进人绘画,我意识不到我在画什么。只有在完成以后,我才明白我做了什么。我不担心产生变化、毁坏形象等等。因为绘画有其自身的生命。我试图让它自然呈现。只有当我和绘画分离时,结果才会很混乱。相反,一切都会变得很协调,轻松地涂抹、刮掉,绘画就这样自然地诞生了。”[3]
在艺术阐释中,精神分析理论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利用了有意识的生活经验和无意识的内驱力之间那潜在的宣示性关系,来揭示内驱力对这一关系的决定作用,并因此而进一步揭示了艺术的隐秘目的。借用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通过弗洛伊德那种释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绘画作品中理性的作者意向,还可能在这意向中看到某种游离的东西,这东西看似毫无逻辑可言,但却正是隐藏在绘画无意识创作动机中的伪装的暗含意向。
在绘画创作中“创造者对现实关系的把握,不是有意识的把握,而是能动地和本能地把握。……剥夺创造中的无意识活动就等于完全取消创造……当形成的内在形象与大作家的偏见或神圣的信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偏见和信条抛弃,而去描绘他真实看到的东西”。[4]
审美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含义,但不同时代艺术家都为试图建立相应的审美规范而努力。在审美过程中毫无疑问人是作为审美主体出现的,如何评判客体是由主体决定的,那么我们说是艺术的必定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而我们作为审美主体面对艺术作品时却有着不同的审美体验,而且审美的程度,侧重点也各不相同。造成这些不同并非由客体而来,课题本身承载的审美是不变的,其具有的审美多少是由主体而定的,主体有 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地域,文化,时期,阶层是造成审美主体不同审美感受的根源。审美主体不同的经历,生理,心理变化都会使审美主体有不同的审美能力,这是造成不同审美感受的本质。不同的主体还有它不同的反差。如历史学家自然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欣赏或鉴定作品的优劣,看它是在社会哪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当时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理学家便会从作品的结构性去入手,即作品的比例、透视、黄金分割点、光和线等逻辑性去讨论。当然,美学家会从他们的审美学角度出发,是优美的,是崇高的,是喜剧性的,是悲剧性的,还是丑和荒诞的。
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是可以改变的。通过过审美知识有意识的收集与无意识的积淀来提高审美主体的艺术修养。作为审美主体能力的改变,有意识的收集是有效的快速的途径,如了解艺术的相关知识和分析大量的不同艺术作品。我们通过长期接受的信息和在平时的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它会不知不觉的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活动,并直接影响我们的审美能力。在分析艺术品时优秀的东西就会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沉淀下来,形成无意识,这也是审美主体经由大脑的选择处理储藏到无意识细胞之中的人在无意识状态中之所以选择了某些方面而舍弃了另一些方面,乃是理性进行了长期了解、深刻静思的结果,是知识与理性溶合其中以至变成知觉本能和自动想象的结果。这就是说,这种神秘莫测的无意识活动,并不是天生具有的,也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深层结构与有意识的经验多次相互作用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自动推理活动,并不是仅仅靠天赋得来的,而是知识变成了本能之后与情感结合起来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效果,只有经过了有意识的点滴积累,才会出现无意识的闪光。意识与无意识在审美主体中交融更替,同时“在我们意识的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经常的,时刻不停的,活跃的联系。无意识的东西影响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痕迹和表现才学会认识无意识的东西,以及它的主导规律” 。[5]
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审美主体的意识收集再通过逻辑思维评判是远远不能完成我们各种审美复杂任务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审美过程中,是审美主体和外界物质同意识的不断交流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中逐渐的储存积淀了一定数量的无意识信息,这些无意识信息不断积累和优化并在受到外界某些东西的触动时就会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对于绘画的作品而言,要追究每一细节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就连画家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例如达利,他曾对他的某些画面上的细节作过某些解释,然而,这些解释仍然是模棱两可。更有赵无极不知道画的‘是什么’让人颇费寻思。但是,这并不说明其整个画面都没有意义,相反却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首先,无意识中的意识仍然是有意义的,一种象征的、隐喻的意义。其次,超现实主义画家在作画时其实都是在“企图”表达其无意识——他的白日梦或者夜晚美梦、恶梦等等这些曾被“超我”(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生活的集体法则)压抑过的无边无涯的本能欲望。在画家而言就表现为一种绘画的方式和技巧。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表现方式和技巧,就是用一种近乎完美的、精确写实的绘画能力和油画技巧——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形象、结构以及非常漂亮的色彩,以最具刺激性和挑逗性的、非现实的怪异形式,描绘出那些本能欲望——以被传统现实主义画家所推崇的极其写实的绘画手法,表现非现实即非写实的、荒诞不经的形象和景物。这些通过画面形象进行“化妆表演的本能欲望”(弗洛伊德语),是个人的,也是人类共有的。唯其是人类共有的,才使人们普遍感受诱惑和对破解其怪异后面的谜底兴致盎然。再有对波洛克艺术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带来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波洛克曾经回忆说,“是他们关于艺术源自无意识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胜过这些特殊画家的创作。”[7] (他一开始先是热衷于描绘那种所谓“生物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