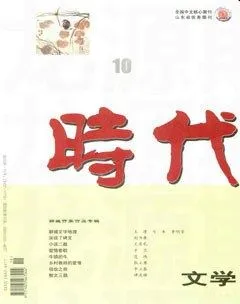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摘要: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是伴随着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转型而产生的,所以,要真正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必须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上着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作为重建的重要方式,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尚待深入探究的领域,文章初步展开了论述,认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是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文化产业
中国文论“失语症”并不是一个纯然停留在文论领域的问题,它与整体文化的转型息息相关,来源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病态式清理。所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必须置身于整个文化语境当中来进行详细考察,从文化思维的高度上来深化重建路径的探究,根本旨归就是“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①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从话语建设上来讲,文论话语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文化话语的演变,否则独自的超拔,始终只能更新乏力,因此从文化的高度上来思考文论话语的建设也是重要的课题,可以呼应问题产生的原因。对文化语境给予关注,原因还在于当前文学理论学科边界的扩展,文本逐渐泛化,进而表现为文化研究的正位。种种现象表明,文化建制的深化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实现与否至关重要。在重建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话语的主体性价值需要显明,依托于文化的主流建制,文论话语的生存空间日渐被正视。
一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要明晰,必须首先增强其本身的内涵,从而展现出超凡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以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曾一度受到诸多质疑,打倒“孔家店”式的活动不断冲击着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虽然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一直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但是急切的变革情绪时时泛滥,使精华与糟粕之间的分野逐渐模糊,批判标准失衡,日积月累,这种状况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生存语境的恶化。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模糊与失落严重制约着当前中国文化体系的构建,缺乏深度历史传承的文化很容易被他国文化理念侵入,因为文化根基的薄弱使我们缺少稳定的话语,面对现实难以展开自己的言说,更不用说去影响他国文化的言说方式。反而是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被他国文化的话语规则所规范,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被严重遮蔽。要改变现状,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应该调整,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锻造文化“内功”。当前世界的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话语权显得异常重要,这在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得甚为明显。
为了更有效地提炼中国文化的价值,“文化软实力”的视域被打开,日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并且还在体制上得到政策性的确立,这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制定了根本目标——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它与“硬实力”组成了现在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维度,大意指向: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感染力、影响力等表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军事、经济,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达成深度影响,不像硬实力那么激烈。约瑟夫·奈是政治学家,他的划分主要从政治领域着手:“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主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纲领计划和吸引其它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他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这种力量——能使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②此后,约瑟夫·奈多次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说明,使软实力的界定愈发充实、明确,但是作为一个新的视域,对其展开论述的角度甚多,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众声喧哗。从软实力被提出的语境来看,就可以发现它与当前国际关系新趋势紧密相关,是国家竞争的新形式,因此软实力必然关涉权力的争夺,尤其是话语权的竞争。
软实力作用的凸显,逐渐获得世界诸国的重视,中国也不例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全新的理念得到确立,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制定了战略。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概念的针对性更强,可是两者之间的层次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文化”的边界具有多义性,一旦我们将“文化”概念泛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界限似乎就不明确了。当然,把文化的概念凸显出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以往文化传承思维缺失的状况起到了反拨作用,政策的制定更表明文化意识的重新觉醒,是对此前偏重工业经济发展的补充,也是对当前中国文化格局的调整。中国文化经过5000年的演化,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曾经广泛地展现出吸引力,但在近代社会结构调整中,却逐渐进入了西化的轨道,于现代性的范式中愈行愈远。这导致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乏力,在价值认同上偏离了传统理念,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二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大家,比如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先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贯中西,在西方话语的优势下,不偏废中国传统文化,能于中西交流中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并建构起中西话语交织的学术体系。而当代以来,我们却缺少一批这样的学术大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术培养机制的问题。曹顺庆先生在反思这一现象时,这样指出:“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包括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问题。我们在整个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严重失误。”③因此,要改变现状,在教育上有所作为是重要的方式。在我们看来,重新面对传统文化,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进阶,而教育的调整和实施则是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重塑传统文化的当代形象和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文化被严重妖魔化,被视作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然而片面的批判,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外来文化趁虚而入,确立起话语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入恶性循环。要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传统文化不能只是停留在研究的层面,或者说是少数人的专业“游戏”,而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传播出去。教育中应该增加一些传统文化的素材或课程,除了学校教育的革新,大众传媒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毕竟它在广度和速度上都具有其他媒介缺少的优势。
另外,能够迅速扩大传统文化影响,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前必须要采用的方式。以往,文化价值常常固守为历史传承,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价值的丰富性得以彰显,文化交流的方式也更加多样。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从口耳相传、印刷保存走到了画面呈现的时代,在形象性和传播的广度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大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大众阅读文化的主要通道。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携手的形态,它改变了此前文化事业的一些运行规则,将文化价值的开发置放于经济规则之下,增强了社会开发文化价值的主动性,并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多层次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存在空间。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文化产业的意义也呈现出多个维度,它以产品的形式化合了文化理念,所以它一方面具有产品的特性,能够创造相应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它更是一种文化形式,潜藏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话语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话语要确立主流地位,文化产业需要将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树立起来。并且,在国际交流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播可以更加有效地避免当代意识形态的强烈冲突,而采取一种历史叙事来实施潜在的影响。其实,人们在使用经济产品时,除了享受物质价值,还要获取产品上的附加值,亦即它的符号意义,比如Adidas背后的Nothing is impossible,Nike内含的Just do it,一定的产品都彰显出某种价值理念,广告宣传则凭借大众传媒的力量不断重复了产品与理念的符号建构关系。相比之下,文化产业就是以文化理念本身作为素材的,它对价值观念的构建和生存感念的书写具有先天的优势。文化产业以创意作为发展基点,创新能力往往决定着它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它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也是绿色产业,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正是由于它的特殊属性,传统文化的价值必须被发掘出来,中国文化产业要提高世界竞争力,它的主要吸引力往往不是我们的现当代文化,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多在学习西方,当西方的学生,作为产业形式,现当代文化的独特性并不鲜明。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优势,四大发明的光环,享有世界的声誉,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渲染的中国文化,就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价值,而是要在当前的语境之下,重塑被遮蔽的传统文化价值,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文论和文学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无体系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关系,文化洞见与文论话语常常熔铸一体,难以如西方科学范式所愿,进行清晰的分割。其实,无论是文学书写,还是文论构建,其主体都是生存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人,他的文学(文论)智慧需要置于该文化氛围中才能充分彰显。因此,“发现东方”、“发现中国”对中国文化、文论的发展都是势在必行的。发现不同于发明,它主要指向揭示、去蔽,是针对传统长期被遮蔽、被遗忘、被边缘化、被悬置而言的,发现中国,就是要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传统,为当代文化的建设积累素材,在此基础上还要坚持文化输出。作为发现东方的积极倡导者,王岳川先生指出:“我们现在再也不可以等着人家来发现你,‘发现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象’也不再是那些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东西,而是经过现代化的欧风美雨洗刷后,中国文化的整合形式。我们在发现过程中,书画、音乐等是最好的文化输出途径,然后是思想文化,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化。”④具体的文学艺术形式,规避了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能够更有利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同时也扩大了蕴含在其中的中国世界观、价值观。所以,现在的电影、电视等文化工业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各国之间对他国的文化工业都比较谨慎。因为它一方面会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会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中国青年一度的“哈日”、“哈韩”就是一种表现,经过美化和包装的他国文化,往往成为受众模仿和向往的对象,在潜移默化中成了他国文化的“跟班”。以此观之,文化产业的发展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战略,要让中国文化(文论)在当代呈现主体性,获得国际的认同,必须坚守我们自身的文化理念,在产业发展上有所作为,增强以产业的形式去言说中国文化的力度,而不纯然诉诸理论的宣传。当然,在国际上去锻炼中国文论的言说能力,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国际研讨会等方式,与国外理论家展开对话、交流,碰撞新的理论火花。通过这种方式,让世界逐渐听到中国理论家的声音,使中国文论话语可以在学术前沿中去磨合,为参与今后世界文论话语的建构制造良机。这一切都可视作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解决“失语症”问题。
注释: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②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第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③ 曹顺庆:《“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④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重释中国》,《长江文艺》2004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