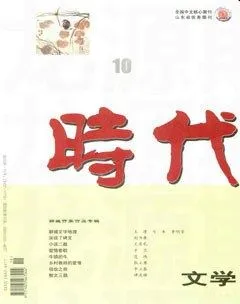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围城》中的名利场与《名利场》中的围城
摘要:《围城》和《名利场》分别是中英文学著作中著名的讽喻小说。两本小说虽然相隔百年,但是在诸多方面相互映射,犹如两位作者跨越时空的交流,揭露了中西方社会不同时代人类的共同特点。本文通过分析“围城”和“名利场”这两个概念在原著中的体现,揭示了《围城》中的名利场的众生相与《名利场》中的围城内外的众生,进而总结出“围城”和“名利场”在古今中外的普遍性。
关键词:围城;名利场;普遍性
世界名著《围城》和《名利场》的作者钱钟书和萨克雷虽然处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国家,但他们好像是心有灵犀,用智慧、幽默、讽刺的语言共同揭露了人性丑陋的一面,都称得上是讽世明镜、警世宝典。《围城》通过串线人物方鸿渐在恋爱、职业、婚姻等城堡里冲进或逃出的沉浮际遇,展现出病态的现代文明所造就的病态人群,描绘了围城内外名利场的众生相。《名利场》通过串线人物爱米丽亚·赛特笠与蓓基·夏泼这两位出身不同、个性相异的女孩离开平克顿女校,步入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名利场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没有道义,没有情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现实世界,而名利场这个现实世界无疑是座巨大的围城。
一、“围城”在原著中的体现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原著中对“围城”的意义有所扩展,是指包括婚恋在内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围城。小说通过对中高等阶层知识分子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四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时,在船上就与苏文纨和鲍小姐纠缠不清,“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回到上海后,借看苏文纨为名去看唐晓芙,并暗中与唐晓芙恋爱。由于苏文纨的挑拨离间,唐晓芙与方鸿渐分手时,他“感到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后来离开银行,到三闾大学去任教,期间与孙柔嘉建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后双双离开三闾大学,回上海之前去了香港并在那儿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之间就总是为各种事情争吵不断,最后方鸿渐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当他决定回家与柔嘉和好时,发现柔嘉已经走了。
小说通过串线人物方鸿渐的亲身经历,描述他如何不断地从求学、恋爱、婚姻、工作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当她最后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时,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
“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二、“名利场” 在原著中的体现
“名利场”取自班扬的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人们对名、利、权位和各种享乐趋之若鹜,傻瓜和混蛋都在市场上欺骗争夺”。原著中通过讲述爱米丽亚·赛特笠与蓓基·夏泼这两位出身不同、个性相异的女孩的生活经历,揭露了上流社会贵族、资本家们自私、冷酷、虚伪的真面目,证实了“名利场”是一个惟利是图、尔虞我诈、买卖良心和荣誉的世界。
已故穷画师的女儿蓓基在离开平克顿女子寄宿学校后,暂住在富家小姐爱米丽亚家中,企图勾引爱米丽亚的哥哥以进入上流社会。为了猎取财富和挤进上流社会,她寡廉鲜耻,卖弄姿色,勾引达官贵人、纨绔子弟。她口是心非uAvnGzfWzFVoz7SeBiT6qg==,冷酷自私,明明不爱丈夫,甚至为了跟情人寻欢作乐而设计把丈夫关进监狱,但在公开场合却又装出体贴入微的姿态。她招摇撞骗,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却喜欢有良家妇女的名声”。为此,她努力学着上层社会妇女的一套风度和动作,还通过勾搭大伯,在嫂子引见下觐见了国王,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丑行。而纯洁的姑娘爱米丽亚钟情于轻浮空虚的军官乔治·奥斯本,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和他结婚。但丈夫很快就厌弃她,另寻新欢。爱米丽亚一味痴情,即使在丈夫死后仍不肯改嫁。最后,蓓基道出乔治生前曾约自己私奔的事实,爱米丽亚才另结了婚。蓓基后来又与年老丑陋的斯丹恩勋爵私通,因私情为丈夫窥破而遭抛弃。而斯丹恩则误以为罗登夫妇设局诈骗,也与蓓基一刀两段,蓓基就此潦倒。她晚年从另一情夫约瑟夫手中得到一笔遗产,开始热心于慈善事业。
从这两个女孩的坎坷生活,尤其从她们的恋爱和婚姻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英国中上层社会各类人物,都忙着争权夺位,争名求利,在“名利场”中,“有满身铜臭的大老板,投机发财而又破产的股票商,吸食殖民地膏血二长得肥肥胖胖的寄生虫;他们或是骄横自满,或是贪纵懒惰,都趋炎附势,利之所在就翻脸无情,忘恩负义。至于小贵族地主,他们为了家产,勾心斗角、倾轧争夺。败落的世家子往往把富商家的纨绔子弟作为财源,从他们身上想花样骗钱。小有资产的房东、店主等往往由侵蚀贵族或富商起家,而往往被他们剥削得倾家荡产”。真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名利、权势、利禄,原是相连相通的。
三、《围城》中的名利场
读完《名利场》之后再读《围城》,就会发现“围城”内外皆是“名利场”,小说中提到的人物无一不是在“追求浮名浮利”,众生百态,跃然纸上:方鸿渐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遭遇失恋与失业的夹击,失意彷徨;在湖南偏僻山乡的三闾大学那座充满着“政治暗斗”的“名利场”的“围城”里,受欺骗、被排挤。而在上海洋场发迹、升官、发财的政务院参事苏鸿业,银行经理周后卿,崇洋媚外的洋奴张吉民之流却春风得意。在三闾大学里,那些投机政客、伪君子们自立门派、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却生活得有滋有味。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才女型人物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高松年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他撒谎老练,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等等,举不胜举。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充分揭露了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以及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现象。
四、《名利场》中的围城
读完《围城》之后再读《名利场》,就会发现“名利场”其实就是一座“围城”,小说通过爱米丽亚·赛特笠与蓓基·夏泼的人生际遇与沉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
蓓基·夏泼刚离开平克顿女子寄宿学校时,犹如身处“名利场”这座“围城”之外的人,觊觎城内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奢华生活,因而诸如姿色,才智,亲情,友情等都成为其实现如此最终目标的工具。而当一切的资源都被其利用透彻之后,回头过来,才知道所谓的名利不过是刹那烟花。名与利,固然可求,但那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人如果过分追求名利,名利就会成为心头最大的诱惑,人也因此变得贪婪、虚伪,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一颗纯洁的心。但身处“围城”之内,她却不能自已,深感窒息又不能自拔,“她不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而当她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一颗永恒炽热的心依然在等候着她,她终于重新体认到了善良、宽容、谦和、淳朴、友爱、和平与宁静,寻找到了身体和心的归宿,让时光从自己的心内慢慢地流逝如水,从中领略生命的全部意义。她的经历构成了一部完成而简练的名利场历险记,是冲进“围城”后又逃脱“围城”的生活历程。
爱米利亚·赛特笠出身名门,虽然善良和纯情,但却懦弱、无能、心地狭隘。她对生活的苦难和不幸缺乏勇敢的斗争精神,而只是无为地屈从、忍受。作者称她为一条寄生藤,只有在结实的老橡树上才能抽芽。爱米利娅傻傻的爱着乔治,曾一度在乔治的“围城”外苦苦等待,终于和他步入了婚姻的城堡,却不料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但她自己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冲出使她窒息的“围城”。而深爱着自己的都宾,却曾被拒之于“围城”之外,直到真正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不忠时,才如梦初醒,终于和一向热恋她的都宾结婚。
两个姑娘殊途同归的真实人生体验揭示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五、小结
《围城》和《名利场》虽然是中西方不同时代的文学名著,但都描绘出了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其中的人物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和周围人的影子。两本小说都涉及到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他们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在“情场”和“名利场”的角逐中,《围城》中的方鸿渐和《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都是失败者。若把结婚恋爱比作“围城”,那么他们俩就是陷入这座“围城”里最久的困兵。这两本小说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名著,就在于它们所揭示的并不单单是著作出世当时的社会现象,而反映的是超越了国度,超越了时代的社会普遍现象。时代变了又变,但“围城”和“名利场”依然是不变的。《名利场》最后萨克雷不无叹息的说道,哎,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这正呼应了钱钟书的“围城”理念: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因此,我们要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走平实的人生之路,即使这条路崎岖而充满荆棘,但是这条路的风景更多,更加真实,更加惬意。
参考文献:
[1]陈彪.《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5):99-101.
[2]何苏平.浅谈《围城》的讽刺与幽默 [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16-17.
[3]黄翠兰.《名利场》与《围城》之比较 [J].茂名学院学报,2008(5):72-75.
[4]李慧莉.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72-74.
[5]钱钟书.围城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孙慧芬.名利场浅论. 世界文学名著选评(3)[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7]杨绛.名利场·译本序[J].文学评论,1959(3):36-38.
[8]朱虹.论萨克雷的创作 [J].文学评论,1963(5):28-31.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