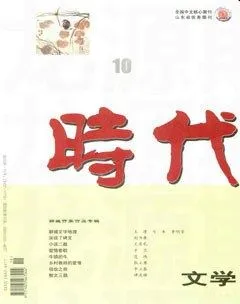新感觉派小说中都市与女性的悖离
摘要:现代都市虽然以其多样性、丰富性、开放性、多元性等特征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宽松的生存环境,但并不意味着都市是女性的天堂,城市与女性的关系中悖离的一面仍占主导地位。在新感觉派文本中,一些都市女性的角色仍被定位在色相市场的商品之上。即使尽情享受性爱狂欢,张扬自己主体性的都市摩登女郎仍逃不出性别的藩篱。另都市的物质化特性又使都市女性在物质面前迷失了自我。都市的物质理性,实用性,机械性等原则的建立则使都市两性关系走入工具性原则的误区。
关键词:都市;女性;陷落
在现代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都市直到新感觉派作家笔下才第一次获得独立,真正成为审美对象。在新感觉派文本中,作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上海这一大都市时,都市女性也被推上文学叙事的前台,成为新感觉派小说叙述的焦点,很大程度上女性与都市两元素构成了新感觉派的创作景观。与分散、单一、封闭、静止的农业文明相比,现代都市以其多样性、丰富性、开放性、多元性等特征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宽松的生存环境。都市文化特征影响了都市女性的价值观,在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女性对“贞操”的漠视、对自身身体欲望的肯定、在男女两性关系中,都市女性打破“男强女弱”模式,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等等,这一切具显示出都市某种程度上与女性的亲和性。但是,城市在大多时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仍是异己的。城市与女性的关系中悖离的一面仍占主导地位。“城市是属于男性的。城市挺拔耸立在地平线上,本身就被认为是雄性勃起的象征。而女性,始终被淹没在地平线下的洞穴里,她们甚至被认为本身即是意指洞穴,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城市所具有的符号特征。”[1]
城市是属于男性的,男性创造了城市文明其实早就隐喻在中国神话故事“廪君与盐水女神”的描述中。神话中,部落首领廪君带领部落到远方建立城市,在艰难的路途中,廪君疲累病倒,后来在盐水女神的悉心照料下,他恢复了健康。当他想要继续前行时,女神为了不让心爱的人离开,她化身为飞虫,遮天蔽日,阻挠廪君上路。僵持之中,廪君假装赠爱之信物与女神,其实是用信物作射杀她的记号,然后射杀了女神,他率领部落继续前进,终于完成了建立城市的功业。
这个神话故事一方面显示了一个“有史以来描述两性关系文本的原型”。[2]女性生来是为男人服务的,“廪君”受伤时,“盐水女神”作为女性的使命就是要柔情万种、周到地呵护、抚慰“廪君”的身体和精神。当她强行阻止廪君时,就违反了“男主女从”两性关系原则,就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则更隐含了一种既定叙事:在城市建立之初,女性就与城市产生了不和谐之音,而男性与城市在建造与被建中已合二为一,在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父权制体系在工商业文明的城市仍在延续。因而,城市的兴起,虽然在客观上出现了一些令男性无法预测,无法把握的有利于女性生存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乡村到城市对女性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天堂。相反,都市女性在享用比宗法制农村多一点自由的生存环境时,同时要承受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双重压力。
一、走不出性别的藩篱
在商业化的三、四十年代上海大都市里,城市一方面带来的是秩序、速度、物质财富、科学精神等;但另一方面当时的都市上海,文化形态远未达到现代阶段。在当时的上海都市,仍沿袭着传统的男权中心观念,女性的就业并没有达到广泛社会化的程度,都市畸形的就业结构与文化意识使城市中只有少数知识女性与下层无产者女性才进入工商、教育、卫生等低收入的狭窄行业范围,大多数女性无法在社会上挣钱养生,在依然属于男性的都市里,女性根本不能机会均等地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搏杀。这正如凯特。米利特所说“男权统治者最有效的方面是对他的女性臣民所实施的经济上的控制”,[3]由于女性在社会上仍然不能取得同男子平等的谋生机会,她们的生存就不得不以依赖男性为前提。在物质化、商业化的都市中、金钱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这使一些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为了谋生而靠拢金钱文化,成为色相商品。她们分布在与都市金钱文化有关的某些区域:交际场、舞厅、妓院等等。她们在脱离家庭,摆脱传统的男性玩偶及欲望对象的卑贱地位后却更进一步沦为商品。都市的商品化无情地将她们推到市场之中,进入商品流通的环节。在赤裸裸的商品化交换中,这些女性只不过是男性购买者泄欲的工具,她被视为物,被剥夺了一切主体感受,不得不忍受来自男性的性掠夺。如穆时英的《GravenA》中的舞女余慧娴“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在男人的眼里,她“巴黎风的小方脸”、富有诱惑性的“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还有性感的身姿是值得“暂时玩玩”的,但是在男人的心目中,她又是“cheap”的,她只不过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当她年老色衰的时候,当她成为“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时候,“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没有人为她的太息而太息!”“青色的寂寞从她脸上浮过”。《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黄黛茜,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意识到青春将逝时,“猛的觉得有条蛇咬住了她的心”。她拼命的买化妆品以掩饰眼角的皱纹,对于舞女来说,没有青春就失去了生存的依靠。这些女性,她们获得生存的资金时,所要付出的是比男性双倍甚至多倍的代价——收起个人的人格与自尊,出卖自己的容貌与肉体,当她们利用身体容貌来换取物质利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被使用被折旧的过程。当易逝的容颜衰老之时,被遗弃的悲惨命运便也在所难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虽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农业社会以性别差异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但是,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见证,自建立以来就由男性统治,城市史是一部男性文明史。男性的城市并没有为女性的进驻提供真正的方便。虽然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动摇了父权统治制序,但是都市女性的角色仍被定位在家庭主妇与色相市场的商品之上。
即使新感觉派文本中一些妖治的、性感的、不羁的都市摩登女郎,虽然她们一改传统的“女为男用”的地位而变为“男为女用”,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已走出性别的樊篱。这些都市摩登女郎之所以能消费男性,她们凭籍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性感的外貌和肉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男性消费的圈套之中。作为三十年代上海都会的现代女性,在都市的铸造下,她们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而西化化,她们大胆和挑衅,“肌肉的弹力”代替了“弱不禁风”、“胸前和腰边处丰腻的曲线”代替了“杨柳细腰”、“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代替了“樱桃小口”……这些都市摩登女郎以掌握性的肉体资源的强势,游忍有余地穿梭于受诱惑的男性之间。而男性人物在男女纯肉欲的游戏中,他们之所以处于被动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充满性魅力、性诱惑的有别于传统女性的都市摩登女郎让当时的男性感到新奇、陌生,由此而产生不适的焦虑、恐惧感。但是,这种男性人物的弱势状态,不是由于怯弱——茫然无知地被蛊惑和控制,而是男性人物心甘情愿地屈从于女性“肉”的魅力,他们在两性游戏过程中却保持着“玩味”的清醒姿态,他们对这些都市女性既崇拜着又轻视着,这些都市摩登女郎在不知不觉中也将自己置于男性竞相“猎取”的尤物的位置。新感觉派文本中的男主人公们,他们始终做为看的承担者,女人的妖治、性感是他们观赏中的美景和奇观,如刘呐欧的《游戏》中,男主人公以品物的心态对女主人公的玩赏:
“他直起身子玩看着她,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
穆时英的《Crave A》中,男主人公在歌舞厅对一个摩登女郎充满欲望的打量。在他的眼里,女郎的身体变成了一张国家地图,他从女郎的头发(黑松林地带)看起,到眼睛(湖泊)到胸脯(两座孪生的小山),一直望下看到南方“更丰腴的土地”(下体)……
在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摩登女郎的脸和身体常常被男性不怀“好意”的窥探、剥离。其实,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历史——当男权中心秩序被确立以后,女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男人追逐富贵和享乐的一部分。《良友》1934年85期上登载了这样一个照片镶拼图,上有中英文标题:“Into Xicated shang hai”和“都会的刺激”,图上有爵士乐队,一幢新的22层摩天大楼,赛马和赛狗场景、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穿着时髦的开叉很高的旗袍,坐姿性感诱人。图画中,都市摩登女郎和都市的现代设施、娱乐园地并置一起,这种意象已非常明显的表明女性已成为都市消费品的一部分,她们已成为都市可供欣赏、品味的欲望释放对象了。
在充满商业和消费气息的上海都市,女性本身已成为都市的“商品化”或“物化”象征。无论是新感觉派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亦或是作为男性的新感觉派作家,在他们眼里,都市摩登女郎作为欲望的对象,被不断地强化着。即使对性采取开放态度,享受性爱狂欢的都市摩登女郎,她们虽然在两性关系中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凸显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及女性的性别意识。但是,她们用性征服男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迎合男性的欲望眼光,把自己打扮的更美丽、时髦、更性感,甚至要象好莱坞明星一样富有热力。女性是男性欲望的承载者,女性的欲望必须通过满足男性的欲望才能得以实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二、物质化对女性意识的弱化
20、30年代的上海商业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度繁华,现代化的物质和消费成为都市高度发展和极度繁荣的象征,而对物质的疯狂占有和追逐也成为现代都市人有别于生活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人们的显著特征。刘呐鸥曾在《都市风景线》中这样描述物质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这饿鬼似的都会吞了进去了。“被大百货的建筑的怪物吐出在门口”刘呐鸥所谓的“饿鬼似的都会”其实是极度渲染了现代都会的物质的魔力,都会物质化对人的吞噬,对人性摧毁性地扭曲。但人性的贪欲,都市人对感官享乐的放纵则又使他们不由自主的依附于物。的确,随着都市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他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4]穆时英小说《黑牡丹》中的主人公黑牡丹曾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物质的狂热和迷恋:“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人对物质的占有欲抽空了人的灵魂,物质以惊人的吸附力和巨大的破坏力改变着人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追求,物质成为现代人生活的焦点,对物的消费成为现代都市人一切行为的起点和目标。生活在五光十色、充斥着消费和享乐的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她们一反传统女性那种受压抑的形象,都市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滋生的个性化环境使都市女性同样有权利表达对物的迷恋和渴望。新感觉派的都市文本对女性消费欲望的展示和关注似乎远远超过了对男性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都市消费文化对女性传统生存价值观的瓦解深深地震慑着习惯于传统宗法制体系中温良、贤淑女性形象的都市男性,所以他们以怪异,厌恶的而又深表忧虑的眼光打量着现代都市女性。另一方面都市女性对物质的狂热追逐、甚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换取物质的行为方式也给都市男性以巨大的震动。刘呐鸥,穆时英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她们经常活跃在跳舞厅、跑马场、咖啡馆和高级电影院这些代表现代性物质,能给人以消遣、娱乐的地方。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这些女郎不惜把情、爱作为换取物质的筹码,正如穆时英作品中所说:“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和蔚蓝的心脏原来只是一种商标,为了生活获得的方便的商标。”[5]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笔下活跃于公共社交空间的都市摩登女郎,她们并非职业妓女,她们类似于影星、舞女、咖啡馆女招待等等,她们与男人保持着有“性”无“情”的暧昧关系,把自己作为商品交换男人的金钱。金钱成为这些女性生活中一切行为的目的,这本身对女人个体意味着最深重的剥夺,它抵消了女性的个体人格,在男人为性事支付金钱,女人为此接受金钱时,它满足着她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它又泯灭了她作为人应具有的情感和精神追求。在都市化进程中,女性在物欲面前主体性的迷失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她们的女性意识。因为没有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就无从谈起女性意识本身。人的主体性、自主性、个体性以及人的独立的品格都应是女性性别意识的前提。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女性,他们在更加个性化、多元性的都市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展示自我、张扬自我的自由空间,但都市的物质化特性却又使她们在物质面前迷失了自我,也从而使她们在与男性的抗衡中走入另一歧途。
三、都市两性关系工具性原则的误区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由于商业化的渗透性影响,五四时期男女两性追求个性独立、个性解放、追求灵肉结合的、相对积极的、健康的两性关系已经被彻底的颠覆了。都市的发展,都市的物质理性、实用性、机械性等原则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包括男女两性关系也被理性的、冰冷的实用关系所代替。已被高度商业化所包围和渗透的都市男女,不再相信地老天荒的爱情神话,也不再遵循爱情的“唯一”性规则。他们在情爱和婚姻的选择上首当其冲的考虑是对方的实用性,他们把两性关系建立在“暂时和方便”之上,两性间不再要求独一无二的个性和忠贞不变的感情,而是从不同的异性方面求得不同的满足。《游戏》中那位“鳗鱼式”的女子从具有“卓别林式的胡子,广阔的肩膀”的步青身上获取“肉”的满足,为了获取“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等物质享受的欲望,她选择嫁给了一位工厂主。刘呐鸥的《方程式》中,男主人公密斯脱丫是“都会产的、致密、明晰而适于处理一切琐碎的事情的数学的脑筋所有者”,在两性关系上,妻子只要具备他需要的功能就可以。他的前妻对他来说,因为具备做诱他食欲、他离不开的“新鲜的青菜salade”的功能,他便会像他爱着她的青菜叶一般地爱着她。他对续弦的要求是“无论哪一个,能够在两天之内给我结婚的我就娶她”,他认为只要是“teen”内的女儿都可以胜任做妻子的功能,因为“teen”内的女儿是没有一个不可爱的,谁不愿意在新洗的床巾上睡觉。这种不考虑情感的都市社会男女双方实用性择偶标准实际上意味着把人简化为一种功能,在功能价值观中,人被分割、以人的功能取代人本身,人不再是一个丰富完整的个体。如同具有各种功能的机械一般。《幻洲》“灵肉号”、“灵肉续号”上曾有文章记述这样的都市两性关系:
“社会进化到了今日,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分工的认识。人们已经明白:一个体(个体或团体)只应求其能够满足人的一种需要。能够替“我”制成合体的衣服的便是‘好裁缝’,不必又要能够做精美的食品;要精美的食品时应当另求‘大师父’去。反过来,“我”有经济上的需要,“我”就去做经济方面某种组织的一员,同时“我”又有学术上的需要,“我”又可以去做学术方面某种组织的一员:一个人不妨同时为多少组织的一员以求各种不同需要的满足。爱情实在也不只一种,有因肉的生活而生的,有因灵的生活而生的,……这两性爱情,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要求其满足不宜执在一个异体上营求。一个异体的只能满足“我”的一种爱情,是人们进化到认识了分工原理之后所宜坦然处之的。[6]
这种流行于现代都市的功能性的恋爱观,揭示了现代都市中机械原理对于人类的思想、情感和现代日常生活的渗透。它把主体性的人降低为从属性的功能或者说是工具,以功能的价值取代了个性的价值。都市男女两性建立在实用性和功能性原则的婚恋关系,它不以承认和尊重对方独立的个体人性为基础和前提,这样男女双方很难取得精神的沟通与和谐、这势必导致男女双方更加疏离和对抗,男女双方的互相异化也在所难免。
结束语
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熟的都市文学创作范例,他们的作品塑造了有别于传统女性形象的都市摩登女郎。将这些摩登女郎与都市意蕴相联系,有助于探讨商业化市场化时代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都市传统意识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使都市女性面临着突围/陷落的现状。都市女性所处的历史、文化处境展现了女性要走出传统男权文化的樊篱、穿透都市异化的迷宫,达到透彻的自我认识,任务会是多么艰巨。
参考文献:
[1]丹娅:《女性景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页。
[2]丹娅:女人与城市——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J],当代文学研究资息,1998,(2)。
[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0页。
[4]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98页。
[5]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上海书店,1988年,221页-222页。
[6]任厂:《如是我解的灵肉问题》,1927年1月《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7号。
(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