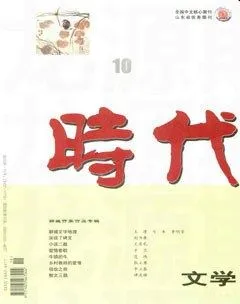当基督徒变成了野蛮人:《奥赛罗》中的种族与文化冲突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创作的历史背景,讨论剧作家如何通过巧妙的地点选取、角色编排包括台词创作一步步地在剧本中展开了十六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初欧洲的文化与种族的冲突, 并探究造成剧中悲剧的真正原因正是当时欧洲社会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关键词: 《奥赛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冲突;他者
《奥赛罗》 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尤其是英国社会所浮现的种族冲突,以及剧作家对此的深思。该剧的全名是《奥赛罗的悲剧:威尼斯的摩尔人》 ,表面上看来此剧是一部因奸人作祟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其本质其实是对“他者”歧视及不同地域文化差异的悲剧。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就重点讨论莎士比亚如何通过巧妙的地点选取、角色编排包括台词创作一步步地在《奥赛罗》中展开了十六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初欧洲的文化与种族的冲突,从而成就了这场悲剧。
1. 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
《奥赛罗》中较为突出并贯穿了全剧的一个主体与客体(西方与东方)的矛盾即体现在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的矛盾中。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就洞察到,在该剧中“东方世界和伊斯兰教徒总是表现为在欧洲内部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外来者”(71)。尽管剧中没有直接出现土耳其人角色,但是这个来自东方的“他者”的威胁化身成为一场军事威胁,从戏剧的开始就被威尼斯人提到。 追溯历史,奥特曼帝国在整个16世纪中都被看作为欧洲世界的军事及宗教威胁体。Faith Nostbakken 指出:“奥特曼帝国不仅仅是16世纪的第一大国,同时也是与基督教相冲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心。土耳其人在十五及十六世纪从基督徒手中成功的拓展自己在陆地及海上的领土,并让被征服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这样的政治与宗教侵略在整个西欧埋入了很大的焦虑与恐慌。”[1]尽管在1571年的Lepanto战役中,土耳其人被重重击溃 ,但他们仍占领着塞浦路斯(1570-1573),奥特曼帝国控制着东欧的大部分土地。这种对土耳其的焦虑也带来了当时欧洲文学作品中土耳其人的形象诋毁。
Walter Lim在《帝国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不光是伊雅各,奥赛罗也把土耳其人处理成“基督教相反的价值观的他者的比喻”[2]p119。例如,剧中在塞浦路斯,当奥赛罗得知凯西奥与洛特力戈打起来之后,他教训道:“为什么闹起来的?难道我们都变成野蛮人了吗?上天不许土耳其人来打我们,我们倒自相残杀起来了吗?为了基督徒的面子,停止这场粗暴的这个争吵;谁要是一味怄气,……他就是看轻自己的灵魂,”(第二幕第三场)。显而易见的是 , 奥赛罗这里的“我们”包括了剧中他身边的所有基督徒角色,其中大多为威尼斯人。 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多是“理性的,文明的”, 如第一幕第三场中的公爵,他在外敌入侵的危机时刻临危不乱,在辨别民众是非上公正不阿。然而,与有着诸多优点的基督徒相反,土耳其人,或是异域的“他者”则被西方看作是文明的对立方,他们被威尼斯人定义成残忍、野蛮、具有攻击性的;而土耳其对欧洲的威胁则被看做是伊斯兰教的野蛮粗鄙相对于基督教的文明理性。至于短语“变成野蛮人”,根据学者Norman Daniel的考证,源自于十四世纪,意指“变成穆斯林”,或“成为野蛮、严酷而独裁的人;行为举止如野蛮人或原始人一般的人”。[3]剧中威尼斯人与 土耳其人的战争,其实更是莎翁的一个暗喻——一场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文化争斗;虽然剧中来自土耳其舰队的威胁被一场狂风暴雨化解了,但这场文化种族的冲突却仍然潜伏在剧中人物内心的世界中,自第一幕的暗潮汹涌一直到最后一幕的勃然喷发。
2. 伊雅各与奥赛罗
人与他人的矛盾作为戏剧的三大矛盾冲突之一,一向是戏剧的描绘重点。《奥》剧中最突出的人物矛盾就是黑摩尔人奥赛罗与白人伊雅各 :肤色的鲜明对比把他们放在一个黑与白的强冲突之下。莎士比亚中让伊雅各担当起《奥》剧中这个满腹阴谋的大奸角,这个威尼斯白人自登场就反复申明自己对奥赛罗赤裸裸的憎恶:“……一次一次反复告诉你,我恨那摩尔人;我的怨毒蓄积在心头,……”(第一幕,第三场)。至于伊雅各要毁灭奥赛罗的原因,他也在第一幕中明示了两点:其一是奥赛罗没有提拔他,仅让他屈居低职;其二是因为他怀疑奥赛罗和他的妻子私通, 他在独白中阐明:“有人说他和我的妻子私通,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可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不过是嫌疑,我也要把它当作实有其事对待” (第一幕,第三场)。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他没有挑明,但读者却可轻易发现,它其实根源于伊雅各的种族偏见以及对“他者”的敌意。伊雅各从出场起就甚少用正式姓名称呼奥赛罗,相反,他使用了各色诋毁性的称呼词:“黑将军”、“摩尔人”、“厚嘴唇的家伙”、“老黑羊”、“魔鬼”、“一头黑马”,等等,其中,“摩尔人”即是出现次数较多的一个。而这样一个称呼则鲜明地体现了种族性和他者性,它意味着“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们”,且以肤色不同为标志。尽管奥赛罗一直表现得高尚且有能力,但是受到当日欧洲社会对于黑皮肤的“他者”普遍存有的偏见及文化定势的影响,伊雅各依旧无法接受一个来自非洲蛮邦的黑人在白人社会中位居高职、发号施令,。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敌意驱使着他去摧毁奥赛罗——这个渗入到本土文化中的“他者”。伊雅各的行为不单代表着种族主义不理性行为的普遍传达渠道,更是莎翁给出的维多利亚时期对于黑人“他者”的殖民话语的特定比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看似阅历广博,历经沙场的黑将军还是被伊雅各牵着鼻子耍得团团转,不由得让人深思,什么才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
3. 奥赛罗与奥赛罗
整部戏剧的高潮在奥赛罗提剑自刎的那段到来,然而究竟是谁要为英雄奥赛罗的倒下负责?用该剧中的对白回答即是:“是我,我自己”(第五幕,第二场)。细读全剧,笔者认为这场悲剧根源于奥赛罗本人,或是源于在当时欧洲对他者的话语下其身份认同的矛盾。
从剧初伊雅各与洛特力戈的对话中,读者得到了奥赛罗的最初讯息:他是 “摩尔人”、 “黑将军” 、一个“厚嘴唇的家伙”,即一个外貌特殊并在威尼斯任重职的异邦人。他既是威尼斯人,又是摩尔人。一方面,因为他的工作职责、他基督徒的信仰,以及他对欧洲文化的认同,奥赛罗把自己当作威尼斯人,认为土耳其人是其价值观的他者;另一方面, 因为他出生在北非,他无法真正属于威尼斯,且不可避免的成为威尼斯人思维下的“他者”。当他和苔丝德梦娜叙述自己那些丰富并充满异域色彩的经历时,以及当伊雅各挑拨他与苔丝德梦娜感情、并使他相信他与苔在国族、肤色和阶级上的差异最终会使苔变心时,奥赛罗下意识的又把自己归属于他者的文化。然而十六世纪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又使得奥赛罗时常否定自己的文化,并试图抹煞它。 两个自我在奥赛罗身上混存并折磨着他,因此才有了他在自刎前的遗言:“在阿勒坡地方,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诽谤我们的国家,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咽喉,就这样把他杀了”(第五幕,第三场)。在这段话中,奥塞罗既把自己看作“行使正义”的执法者又把自己看做有罪的被杀者,究竟自己是“文明正义”的威尼斯人,还是“卑劣”的野蛮人,奥赛罗至此依旧无法分清,但他显然认同欧洲文化是更理性优越的一方。而这样的纠结却恰恰是其所生活的欧洲社会对来自文化及价值的“他者”所怀有的歧视造成的。
剧作家或多或少的要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话语的影响,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莎士比亚展现了早期近代英国社会上的文化及种族冲突,并让他自己及《奥赛罗》站在当时霸权性种族意识形态下的一个争论性立场。
参考文献:
[1] Nostb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