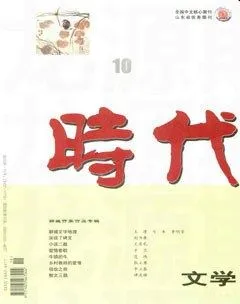荒诞的手法真切的等待
摘要: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一剧本中,虽然作者从戏剧情节、语言、舞台形象等各个方面都使用了荒诞的描写手法,但是他为我们揭示出的这个孤独无助的、只有近似绝望地等待才能生存下去的群体,却是感人至深、真实可信的。
关键词:《等待戈多》;荒诞;真实
1969年,瑞典文学院,一位精神矍铄、年逾六旬的老者走上领奖台。他因“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以及“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而领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塞缪尔·贝克特——荒诞派戏剧的奠基人。
塞缪尔·贝克特是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1906年生于都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青少年时期去巴黎郊游时,他结识了同样出生于爱尔兰的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贝克特的小说创作深受乔伊斯的影响,故有“小乔伊斯”之称。真正使他名震世界文坛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
这是一个两幕剧。出场人物共五人:除主要人物、两个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外,还有奴隶主波卓和他的奴隶“幸运儿”,以及一个小男孩。时间是先后两天的黄昏时分。地点是荒凉的乡间路旁。
第一幕。两个衣衫褴褛、浑身发臭的流浪汉戈戈和狄狄,焦燥不安地站在乡间路旁,等待戈多的到来。他们并不认识戈多,也说不清到底为何要等待戈多,但却又如此急切地盼着戈多的到来。时间难熬,他们的谈话也是梦呓般的胡言乱语。后来他们竞想玩玩上吊的游戏。不久奴隶主波卓拿着鞭子,牵狗般地牵着他的奴隶“幸运儿”路过这里,他打算将“幸运儿”在市场上卖掉。他们将波卓误作戈多。这主仆二人走后,小男孩上场了,他是戈多的信使。他说道:“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可是明天晚上准来。”孩子退场,夜幕突然降临。“咱们走不走?”“好,咱们走吧。”但他们仍坐着不动,幕落。
第二幕。次日黄昏,相同的地点。但原来的枯树上现在却长出了四、五片叶子。两个流浪汉戈戈和狄狄不知在哪里稀里糊涂地过了一夜,又来到这里焦急不安地等待戈多。漫长的等待中,他们时而拥抱,又时而互相谩骂。这时。波卓主仆二人再次经过这里,但戈戈和狄狄竟认不出他们了,这两人又误将波卓看作戈多。一夜之间,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两人一上场就烂泥般瘫倒在地。他们走后,戈多的使者、那小男孩又上场了。他也不认识戈戈和狄狄了,他报告说:“戈多先生今天不来了yf9nRuIAvIcD0DFNPA1Snw==,明天准来。”他们绝望了,决定去上吊,可是没带绳子,他们竞想起了用裤带。但裤带太短了,一拉就拉断了。他们决定明天再上吊,除非戈多来了。“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了。”“好的,咱们走吧。”但嘴里喊走,脚却一动不动。幕落下,剧终。
在西方剧坛轰动一时的《等待戈多》就是这样一部戏剧。它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
该剧情节是荒诞的。在这两幕剧中。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这与以往的传统戏剧是大不相同的。整个剧本情节杂乱无章,时像幻觉,时像恶梦。剧情也没有矛盾、冲突,都发生在黄昏,都是在乡村的路旁。两个主人公戈戈和狄狄的谈话也是语无伦次,毫无逻辑可言。枯树在一夜之间就长出四、五片叶子;而奴隶主波卓竟象牵着狗那样牵着奴隶“幸运儿”登场,并且他们莫明其妙地在一夜之间分别变成了瞎子和哑巴。尽管他们头一天见过面,但再次相遇时,竞互相不认识了。整个剧本的中心似乎都围着两个字“等待”,但他们除了知道要等的是戈多外,别的竟一无所知。
戏剧中的语言、人物是荒诞的。整个剧本,逻辑正确、因果分明的句子廖廖无几;大多数句子都颠三倒四、不断重复、文不对题、胡言乱语。这与作者意欲刻画的人物是紧密相连的。该剧中的五个人物,没有一个是英雄式的正面人物,且神智都不能算正常。这五个人物,是被扭曲的当时西方社会的人们的缩影。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变得喜怒无常,恍恍惚惚,整日如梦游一般。这样,作者就刻画出了一个非理性化、非人性化的世界,人既不能称之为正常的人,其语言也必定似胡言呓语。这样,通过语言与人物的贴切结合,作者有力地揭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荒诞性。
舞台形象是荒诞的。荒凉凄惨的景象下映衬出的黄昏,灰蒙蒙、无精打采、令人心情备感压抑。波卓竟用绳子拴着“幸运儿”,而套在他脖子上的那个沉重的箱子,里面装的是沙土。两位主人公上吊用起了一扯即断的裤带。而一夜之间枯树上就结出了的这四、五片叶子,使人觉得连最公正无私的时间老人也变得荒诞起来。
多少年以来,对《等待戈多》的评论一直在争论不休。有的戏剧家认为贝克特在戏剧和文学语言上掀起了一场革命,有的则认为他把文学变成了类语叠用的文字游戏。但不管怎么说,贝克特用荒诞的描写手法,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真切的等待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等待就是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热恋中的情人等待幽会,囚犯等待自由,贫穷者等待发家致富,投稿者等待作品发表……只要等待就有希望。等待也是一种努力,而为生存、亲情、友情、事业所作出的真诚等待,还能产生催人泪下、令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明知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不可能再有人出来买火柴,但她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一心想卖掉火柴,硬是坚持着,等待着,直至冻死在那里。有一位孤苦伶仃、年逾六旬的老太太,深知自己参军的儿子喜爱自己做的布鞋,每个月都要为他赶做一双新鞋子。当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她几乎痛死过去。但后来,她擦干眼泪,以顽强的毅力活下来,她把对儿子无限的爱,投入到做制鞋子的针线活中。针不知磨断了多少根,线不知用完了多少团,手上不知磨起了多少泡,老人仍是那样一如既往地做着、等着,等着她那已不可能回来的儿子试穿新鞋子……等待儿子不可能的归来,成了老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老人死后,人们在她屋里发现了山丘似的鞋子!
人人都有难言的等待,正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一样。最隐秘、最痛苦的等待,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在球迷阵阵呐喊助威声中,有人却在等待自己的主队惨败——他已为此投进巨资赌博竞猜。为所欲为的贪官倒台前,总是期待着,梦想着神圣的法律压不过他手中滥用的权力!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戈戈和狄狄为什么要苦苦地等待?剧中有这样的对白:“等待戈多干什么?……向他祈祷,向他乞求”,“咱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了,要拴在戈多身上。”还有“咱们要是不理会呢?”“他会惩罚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全都死啦,除了这棵树。”“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啦。”由此可见,该剧揭示的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琐碎的生活问题,而是有关是等待还是死去的重大问题!
总之,在《等待戈多》这一剧本中,贝克特通过荒诞的描写手法,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莫大的灾难——人情冷漠,贫富分化加剧。一些入,如戈戈和狄狄这两个流浪汉,只有乞食祈求,靠虚无缥缈的希望等待着,才能赖以生存下去。在作者给我们刨设的这个冷漠、离奇而混乱的荒诞世界里,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些人不得不孤单地、无助地、痛苦地生活着。他们的身心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永无休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只有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苦苦地寻觅着,绝望地等待着……
参考文献:
[1] 段汉武.等待戈多:荒诞中的真实无意义的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6.03。
[2] 焦敏.《等待戈多》与存在主义哲学.【J】《文学教育》
2008.17。
[3]中外文学名著描写词典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