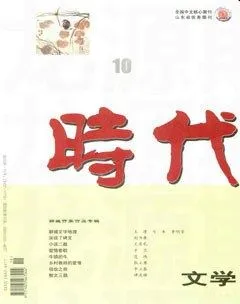淼淼散文二题
淼淼,原名赵洪杰,女,山东省作协会员。先后在《诗刊》、《人民日报》、《青春诗歌》等省级、国家级报纸刊物发表诗、散文作品百余篇,在《时代文学》2005年2期发表中篇小说一篇,作品入选《当代散文诗人16家》、《绿风诗刊十年作品精选》、《华夏散文精典》等,出版诗集、散文集各一部。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农联社工作。
音乐的魔力
总是感叹音乐对心灵的震撼力,虽然我不懂音乐,不知道什么是音律和章节,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识,但这都不能成为我倾听它的障碍。当我忙碌或行走的时候,可能无暇顾及音乐,但当我心灵疲惫或停下来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音乐,因为这时候我需要它,就像一个跋涉在沙漠中的人,因身体的饥渴和劳累而需要泉水一样。音乐响起,心中一片绿荫,一片温柔,清亮的水漫过沙样的心,眼前尽是诗情与画意。
原来,一根琴弦是深藏在你心底的,平时你找不到它,只有音乐的手轻轻一触,它就会响起。
而音乐是什么?那根深藏在心底的琴弦是什么?我却回答不好。
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到物欲横流的今天,音乐的历史已经远远跨越五千年。最早的石器乐出现在什么时候?我说不清,但是,我却知道,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不能没有音乐,人类那种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情一直传递到了今天,世界的各个角落,哪里有爱,哪里有美,她就会出现在哪里。音乐时刻都在用她独特的魅力唤醒人间沉睡的一切。那漫天飞舞的音符,动听的歌曲,把有关自然、美、爱的气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永远不至干枯和荒芜。
我猜想,音乐一定跟自然、记忆、爱情有关,与心灵的渴望和寄托有关,与心中苦苦追求的梦想有关,而心底那根不轻易触碰的弦,应该是那种深埋的情感。
音乐是自然。你听,当音乐响起,那禁锢你的坚硬的四壁就会消失,你会看到大海,海浪轻轻拍打着海滩;你会看到壮阔的草原,绵延起伏的群山;你会看到严冬悄然消失,春雨滋润着大地;你会看到花草拂动,阳光灿烂;你会看到茂密的丛林,曲折的幽径,跳跃的山泉。那纯净、恢弘的音乐,那天籁般的声音,使我们的胸襟一下子开阔起来,思绪也飞到了遥远的天地之间,感受着千奇万变的壮美景色。《平湖秋月》、《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彩云追月》、《蓝色多瑙河》、《莫扎特小夜曲》等,这些经典名曲仿佛一册巨大的画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你面前……
音乐是记忆。我不知道曲作者会带着怎样的心情和记忆去创作,但我知道,音乐会徐徐打开尘封的一切,让你走进生命的记忆。也许是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只是一曲简单的旋律,却能让你毫无防备地卸下坚强的武装,于一瞬间唤醒那些沉睡的往事。也只有音乐,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的记忆。它记载了往事,也承载了悲欢。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无限地接近了最原本的自我,接近了最简单、最精神化的幸福与快乐!在这样的音乐世界里,可以遇见你想要遇见的一切,可以沉浸在岁月的深处,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只有原来那段旋律还守在原地,等着你不经意间的靠近,去捡拾童年和青春消逝的一切,去揭开你不轻易触碰的隐痛和已忘怀的欢娱……
音乐是爱情。有多少音乐取材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恐怕无法计数。《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音乐史上异曲同工的经典之作,那种爱情故事的悲壮、曲调的优美抒情和深沉婉转的韵律,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令它们走向艺术的顶峰。无需任何语言,随一段曼妙的音乐,故事中的爱情之花,就那样悄然开放了。还有一首我喜爱的《神秘园之歌》,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哀伤的女子,迟暮的容颜已饱含沧桑,她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星空下,那交错闪烁的星子,多像一个人的梦,在生命的天空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触手可及,却又无法碰触……然而,如此美丽浪漫的时间,却是如此孤独寂寞的世界。又好像独自一人迷失在神秘的丛林里,那婉转哀伤的曲调令人窒息,爱情就仿佛是这样一片一望无边的蓊郁森林,当你走入其中,就会迷失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四周是一片迷雾,向前走或向后退,都找不到出路,没有尽头,而你却不停地走下去……迷茫着、痛苦着、诱惑着、徘徊着,一直走下去。在这样的音乐中,你不清楚人是在爱情中永生,还是在爱情中灭亡。
音乐,是心灵的寄托。我不知道别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会怎样调解自己的心情,而我调节心情的秘方就是音乐。听一首与自己心境相似抑或相反的音乐或歌曲都可以改变心情。音乐既可以让高涨的情绪得到舒缓,也可以让伤了的心得到抚慰;音乐既可以听我们诉说,又能陪自己轻轻的叹息。寂寞了,可以陪伴;伤感了,可以慰藉;疲倦了,可以放松;压抑了,可以宣泄;高兴了,也可以助兴。无论是开心还是伤心都可以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心灵所需要的一切。这世间,还有什么比得过音乐的包容、抚慰和宽阔?更多时候,音乐里有一种温暖的音色,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像一个温婉的情人悉心地陪伴着你,度过一段浪漫的時光。邂逅音乐一如邂逅情人一般动人心魄。
音乐,是梦想。不敢想象,没有音乐,生命会是怎样的枯燥与乏味。如果眼前总是现实的一切,而没有音乐带给你的梦想,心是否很快就会像深秋的落叶一样枯萎?甚至,在你几近绝望的时候,音乐纤柔的小手会牵引着你一直走向美妙的境地、梦中的天堂。即使在看书的时候,也需要音乐的陪伴。行走在古诗文里,感动于天地间那些浩然正气,感动于地老天荒的痴情,聆听古人心灵发出的声音,与那些圣人先贤们相遇,与文学大师们交流,与你梦想中的一个人倾心相诉,灵魂随高山流水般的雅韵轻轻飞扬……这些,都弥补了现实世界里的不足,似乎找到你前世今生的梦。也只有它们,才能够承载心灵的一切,才能承载悠远的梦境。
所以,因了音乐的存在,我们的心还在跳动,还在奔跑;因了音乐的存在,我们的心还能够感动,还能够回忆,还能够悲伤,还能够拥有希望和梦想……
蝉声如雨
蝉们隐身在茂密的枝叶间,声嘶力竭地齐声叫着,那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强迫性地占据了人的耳朵和大脑。慵懒而燥热的星期天,蝉的鸣叫成了唯一能够欣赏的音乐。
看完书中的一个章节,蝉的叫声又不失时机地挤了进来,一种让人无处躲藏的热也紧跟而来。然而,这样的天气,却是蝉的好时光,它们似乎在如火的骄阳中快乐得发狂,因为它们正以庞大的气势演唱着交响曲,那叫声密集如雨。听着听着,忽然就听出了一种悲哀,想到,蝉们正在用歌唱完成它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相对它多年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来说是多么短暂,但为了这嘹亮而短暂的时光,它们进行了一场多么艰难的生命蜕变啊。
小时候是极爱捉蝉的。我们把蝉的幼虫叫做“知了蟪”,把蜕变后的蝉叫做“知了”,你听“知了——知了——”,真像什么都彻悟、一切都明白似的。小时候并没想这么多,只觉得捉蝉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夏天闷热的傍晚,于树下干硬的地面上寻找一个个小孔,挑开一层薄薄的地皮,一个黑洞洞的地穴露了出来,试探着伸进食指,立刻被锐利的小爪子攀住,然后,一捏就揪出一个鬼头鬼脑的小虫来。哈哈,立刻向同伴报告战功。有时去徒骇河边去捉,一个晚上收获甚丰,第二天,可有一盘炸得金黄的美味。偶尔捉到一两只,就挂在蚊帐里看它变。先是等到半夜,看它一下裂开脊背上的中线,慢慢地,一只淡绿色的昆虫拱着腰往外挣扎,终于拱出头部来,露出两只凸出来的黑亮的眼。后来知道,蝉不止两只眼,中间还有几个红晶体状的小眼,小时候并未注意到,也不知道什么是它的单眼或复眼。当蝉大部分躯体挣脱出来的时候,它会先把躯体倒挂下来,然后再反转上去,才能将尾部抽出虫壳。刚出壳的蝉整个是淡绿色的,两片绵软透明的蝉翼让人不忍触摸,当蝉的身体变黑变硬时,我才敢摸一摸什么叫“薄如蝉翼”。紧接着,看看它胸下是否有两个大盖片,如果有,就轻轻挤压一下,看它是否能叫出声来,这时,你如果捉不牢,蝉会飞掉。
后来从书本上知道,蝉的一生太不容易了。一般我们见到的蝉,要在地下潜伏四年,在地面上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当蝉的卵虫从树枝掉到地上,它会急切地寻找适合它的土壤,钻入地下,找到靠近树根的地方,然后就凭着吸食树根里的汁水慢慢生长,并自己动手为自己建造一个大小、湿度相宜的小房子,冬天到来时,它大概会冬眠。四年的时间,不知这些小小的昆虫是怎么在地下度过的。下大雨会不会冲毁它们的房子?青蛙和蛇会不会吃掉它们?它们为了打洞挖掘出来的土是怎么处理掉的?它是如何感知外面的世界,并准确地预测出来的适宜时间?出来后它的视力是否足以令它找到一棵树攀上去而免遭各种危险?飞到高枝上后会不会遇到捕蝉的螳螂和紧随其后的黄雀?这些问题曾在我成长的岁月中萦绕多年。
蝉的智力肯定不发达,记得小时候调皮的哥哥们在夜晚的柳树下燃一团火,然后使劲摇晃树身,这时,蝉们就会鸣叫着扑啦啦地飞下来落在火堆上或火堆旁边,于是,被那些玩童们信手拈来。玩童们的绝技也是多样的,他们自做一种很黏的面筋,粘在竹竿头上,然后举着竿子在Ny/PNVDklJ0mokCv1gwJeA==树上粘蝉。这方面我也很在行。记得粘蝉要选择合适的角度,就是要选择它大大的复眼看不到的位置将竹竿慢慢靠近,蝉似乎听觉不好感觉也不好,只要让它看不到就能粘住它。这些捉蝉的趣事很深地留在记忆里,以致在成年后的梦境中多次出现。
农作物杀虫剂的应用使很多鸟类和昆虫灭绝,但蝉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可能跟它不食人间烟火有关。一到夏天,河边的柳树上或榆树上蝉的乐队就会齐声高奏。有一次走在茂密的马颊河林海中,炽热的阳光下,蝉声密集如雨。在一片低矮的柳林里,我们几个朋友一边走一边拨开眼前的垂柳枝,随着我们迈动的脚步,不断有成群的蝉在我们的头顶一哄而起,就这样一路走过,不知惊飞了几千几万只蝉,真是有趣得很。那时,蝉的叫声是那样悦耳,坐在林海下的树荫里听蝉鸣,竟听出了无限闲适和千古诗意。
蝉在中国古代象征复活和永生,这个象征意义来自于它的生命周期和生命形式:它最初是幼虫,后来成为地上的蝉蛹,最后变成飞虫展翅飞去。蝉的幼虫形象始见于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青铜器上,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人们总把一个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庇护和永生。另外,古人以为蝉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来比喻清洁的人品,或以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行的高洁。人们还制作出青白玉的蝉的吊坠,成为古今女性的所爱。曾经在一次旅游途中的玉器店里被一只玉蝉所吸引,那完美的造型、晶莹剔透的玉质、圆润的手感令我爱不释手,把玩多时,终因价格的昂贵使我放弃。
在一般人那里,蝉鸣被称做聒噪,因为它没有婉转的鸟鸣动听,没有袅袅的音乐优美,更没歌女的歌喉甜蜜。也的确,蝉的叫声有时听起来更像一条撕裂长空的横线,并且高分贝地撞击着人的听觉神经,尽管这样,我依然喜欢蝉鸣,那种来自自然界强大生命的声音令我着迷,而蝉们也依然自顾自地叫着,不受任何干扰地、无所忧惧地歌唱着,成为夏季里最高亢嘹亮的音符。
可以说,蝉是我见到的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它从早上七八点钟开始,一直叫到傍晚八点钟光景,好像中间有声音低落的时候,有稍许停顿的时候,又好像从不停止似的,除非下雨或天气恶劣。它们这样拼命的、不知疲倦的、与时间赛跑似地鸣叫,是一种什么道理和现象呢?我说不明白。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想,这叫声是在召唤同伴吗?是在呼唤爱情吗?是在歌唱自己卑微的生命吗?是在歌唱生命的解放和自由吗?是它们生命终结之前的一种能量的集中释放吗?还是它们不失时机地借以表达生存乐趣的一种方式?
记得我以前曾写过一首诗,名为《蝉·禅》——披一件金色的袈裟/禅悟/打坐,脱一层金色的外壳/知了/飞了。想一想蝉的多年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多像人生的炼狱,多像一位高僧的十年面壁和禅悟打坐,而最终那种对一切的“知了”和参透,那种顿悟般的飞翔,简直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尽管,金蝉的鸣叫和飞翔更接近生命的终点,但毕竟,那深秋的寒蝉,曾在盛夏时节留下一段美妙的歌声,曾在亮丽的天空划出一条美丽的生命的弧线。